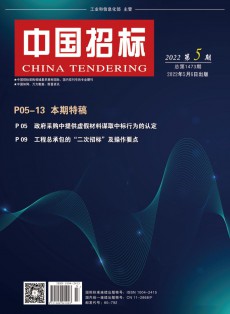民法典应用案例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4:4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民法典应用案例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DF5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1
历史上创制和使用民法典比较成功的是法国,它不仅使用了所有权原则、自由和平等原则等,同时它的制定契合了人民的思想和意愿。相较于法国,我国的社会性质和其截然不同,所以创制一套成熟的民法典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民法学者的努力方向。我国已经对民法典进行了三次创制,这三次创制都以失败告终,当前再次启动民法典的编纂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本文中,根据先前创制民法典的经验及专业人士的探讨,分析和阐述了民法典创制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和总体结果,以期能给予一定的参考建议。
一、民法方法论
我国前三次的民法典创制工作均因各种原因以失败告终,所以我国的民法学者在研究国外民法典理论和制度的同时,更着重于研究民法本身的性质,并根据我国的国家特征对其进行改革,确保其能达到我国的要求。民法方法论对民法典来说很重要,它详细分析和研究了民法的配置和规范。我国的民法学者可以根据民法典创制的基本要求,借鉴各种法律的特点,在研究了不同国家的民法条款、传统法律概念特点、民事习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革新和改变并应用到我国的民法典中。对于民法方法论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随着我国民法学者的深入研究,对民法自身的特点和规范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因为我国当前还没有成文的民法典,所以还需要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方法论问题。[1]
二、民法总论
1.民法总则的结构
民法法典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民法总则,它不仅包括民法自身的一些内容,同时还包括与之相关的一些法律。从某些方面来说,民法总则是民法法典的总纲。研究民法总则从多年前就开始了,我国的很多学者研究民法总则花费的时间要比研究民法典内容的时间多得多。因为民法法典自身的性质不一,所以民法总则对其的影响和分布也不相同。
2.民事主体
民法典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民事主体,因为各国的民法典自身性质不同,所以其民事主体也不同。我国的民法典还处于创制中,但是民事主体已经确定好了,那就是自然人。对于自然人来说,它包括的分类较多,不仅包括已经死亡和失踪的人,同时还包括未成年人和婴幼儿等。这些类型和形式各异的自然人就是谈论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同时事业单位的法人和营利法人等也是民事主体的研究对象。
3.法律行为
法律行为理论对于我国的法学来说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因为它自身的性质和我国的深入研究层析不成正比。这就导致了我国对法律行为的分析和论述主要通过借鉴国外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来完成,这会出现各种的不协调问题,同时我国在对法律行为进行判断时也缺乏准确的概念。所以研究法律行为,既要研究相关的定义和理论,同时也需要详细论述和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内容。
三、人格权法
1.人格权法总论
在民法典中人格法是很重要的部分,在民法中它的編纂形式一直存在争议,但是它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格权的商品化形式研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研究方式,对于人格权的赔偿和侵害等已经被高度重视起来,并且有许多学者详细对其进行研究和分析,以期能获得相应的结果。
2.人格权分论
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身体权和隐私权等,这些权利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民法学者一般都是从各组成部分对人格权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其中的身体权和隐私权是近年来被逐渐认识到的重要权利。对每个人来说,隐私权都是很重要的,它甚至会危及到人们的生命安全。身体权在近年来主要是涉及到器官移植等方面的问题,先前主要是研究供体,当前很多学者已经转变思考方式考虑从分析受体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这样就发现很多先前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为人格权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物权法
1.物权法总则
对于物权法来说,它的性质性相对特殊,在民法典中列入需要经历比一般法律多得多的分析和研究,民法学者及时在经过深入研究后将其列入,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一直都是争议的焦点问题。对于物权法来说,它需要遵循最基本的平等保护原则,这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体现,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宪法的要求。学者们所提出的物权法观点有许多是很有用的,因为物权法理论一直是我国民法典中的争议焦点,所以它在现实中的意义,需要结合实际进行分析,通过实际的应用来获得正确结果。[2]
2.所有权
所有权是物权法的核心问题,也是物权法制定的根本原因。物权法所有权主要是针对所有权的类型而规定的。我国当前的所有权形式中私人所有权是当前争议的焦点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所有权问题发生了变化比如房屋的所有权,就有了权形态的变化。
五、侵权责任法[3]
1.一般侵权行为
因为侵权行为中包含着违法性理论,所以很多的民法学者认为应该在民法中独立对待违法性。一般情况下,在我国侵权行为会被当作违法性案件来处理,这是因为它自身的功能和涵义与传统的理论不一致。对于侵权行为来说,它包含着较为广泛的案件,还包括死亡赔偿和安全保障义务等理论,因为理论观点的不同而影响到了对侵权行为的判定。民法典的创制,需要综合分析各方面的分歧,从而得到好的选择方向。
2.特殊侵权行为
特殊侵权行为包括专家责任、环境侵权和专利侵权等侵权行为,如果侵权行为如果被当作是人过世责任,那就属于新型的侵权行为,因为该侵权行为形式较新,且没有更多可供参考的案例,在进行阐述的过程中会缺乏认识。特殊侵权行为从整体来看其类型的分化问题是我国侵权立法的核心,只有详细对每个侵权行为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对类型进行分化,从而为民法典的创制铺平道路。
六、合同法
1.合同法的生效和成立
合同法主要用于约束合同的执行,它对合同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合同法中合同的生效和成立是最关键的问题,成立合同需要合同双方具备规范的合同形式和意向书并进行规范的签署。合同法的信赖问题一直都是讨论的热点,对于信赖保护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研究,并将国外的一些理论应用其中,但是只构成了信赖保护的大体框架,并未形成具有明显意义的关系分析。
2.合同的转移、变更和解除
建立好合同后,合同就会具备相应的效益,如果合同双方有意愿的改变,就会出现所谓的合同转移、变更和解除问题。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很少有人会去研究第三人利益合同。在这其中,债券的让与分析问题成为了研究的关键,依照我国当前的法律将让与债券归属的不同之处指出来,并将抵消问题在此基础上融入,对民法典的创制意义重大。
七、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法学研究也受到了影响,我国的民法学者应努力克服不利因素的影响,加快对民法学的研究步伐,确保民法典创制的实现。此外,我国的民法学者还应认清我国当前的民法典创制现状,及时发现民法学中存在的问题,为我国民法典创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刘颖
参考文献:
篇2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4—0042—05
违法性是一个从其术语就存在争议的问题。关於违法性有很多不同的称谓,例如:“违法行为”、“行为的违法性”、“加害行为的违法性”,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行为的违法性”、“违法行为”等都是来源於拉丁语“Injuria”一词,而“Injuria”则主要是指一种行为,并且指出了“违法行为”是个比较妥当的术语。因采用术语的不同,不同学者探讨违法性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例如,采用“违法行为”的术语,更多地集中於“行为”的阐释,“违法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违反法定义务、违反法律所禁止而实施的作为或不作为。”
本文采用“违法性”这一术语,并不否认违法性中的行为因素,而是侧重於“违法性”本身的研究。本文从违法性的由来着手,简单概括了“结果违法说”和“行为违法说”两种学说,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违法性”的概念,并分析中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权益侵害”,进而明确了违法性的价值。
一、违法性的由来
一般地讲,过错和违法性的区分是由德国学者耶林提出的。“耶林在《罗马私法中的责任要素》一书中,提出了‘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概念,他认为,只有存在过错的不法才能够产生损害赔偿的义务,而一个客观不法仅仅产生返还原物的义务。善意占有人是客观的违法,而恶意占有人是主观的违法。善意占有他人之物处於客观的违法状态,然而,如果占有人是恶意的,例如窃贼,则属於主观的违法,即具有可非难性。”耶林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德国学者的支持,并且违法性也得到了立法的支持。《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负有向他人赔偿因此所生损害的义务。”这里的“不法”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违法性。自此之后,在德国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中都将违法性与过错区别开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违法性的产生直接与法国和德国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对於罗马法中过错概念的不同继承方式有关。在罗马法中,过错包涵了违法行为的概念。《法学阶梯》记载的一些案例也表明,违法行为意味着过失(culpa),而过失(culpa)的含义比违法行为(jnjuria)的概念更加广泛。例如:《法学阶梯》第三篇第211条:“当某人故意或过失杀死他人时,被认为是非法杀人。不属於非法损害的情况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谴责;因此,那些在无过失或故意的情况下偶然地造成损害的人,不受处罚。”在这一条关於故意或过失杀人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杀人,就意味着非法。但是在罗马法中过错概念的继承问题上,法国和德国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在所有的欧洲民法典中,《法国民法典》给法院的指示最少。其作者只是对表达‘永恒的真理’感兴趣。”《法国民法典》有关侵权行为的规定仅仅是从第1382条至第1386条五条而已。“《法国民法典》的制订者给予法院的指导原则没有超出第1382条与1383条所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这三个构成要件是: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可见,在《法国民法典》中所确立的侵权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并无违法性的存在。“法国学者普兰尼奥尔和萨瓦安蒂等人就提出:过错是一种行为的错误和疏忽,它是指行为人未能象‘良家父’那样行为,从而形成了过错内涵的双重性,即过错不仅包括行为人主观上的应受非难性,也包括了客观行为的非法性。”所以说,对於《法国民法典》中的过错,是完全继承了罗马法的做法,本身就是一个包括违法性的范畴。这样一种立法模式在给法官带来确认侵权责任便利性的同时,由於没有确定什么才是行为的非法性,需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也带来了可能过於宽泛的过错责任的危险,从而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
在《德国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首先是耶林在理论上提出“客观违法与主观违法”的区别为此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其次,“《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认为《法国民法典》的起点都是不可接受的:‘将解决应当由立法解决的问题之职能交给法院,既不符合草案的本意,而且从德国人民对法官的职能之一般观点来看,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等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一一列举,将对这些权利的侵犯规定为“不法”,从而在立法上实现了过错与违法性的分离。同时,《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对“违反保护性规定”和第826条“违反善良风俗”的规定使得违法性这一概念更加周延。这样以来,就将确定什么是违法的权力收归了立法者,而不是像法国那样需要法官在司法实践的每个案件之中去确定。
二、违法性的概念
《德国民法典》虽然第一次用“不法”在立法上确定了违法性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地位,但是在具体怎么界定违法性这个问题上,却始终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从整体上讲,存在有两种不同的学说,即结果违法说和行为违法说。
(一)结果违法说
传统的违法性理论采取的是结果违法说。按照中国台湾学者的观点,结果违法说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除非存在违法阻却事由,不然只要行为造成了权利侵害,就具备违法性。“民法的‘权利侵害’要件是基於保证个人自由活动的个人主义民法的思想,在只要不侵害他人的权利就不负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制度下,个人的自由活动只受最小限度的制约,这样,就明确了作为‘权利侵害’要件根据的法律思想背景。”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法,乃为违反法律之强行(强制禁止)规定之谓,然此系就狭义之不法言,若就广义而言。则违背善良风俗,亦属不法。”但是,“所谓强制禁止规定之范围如何,显然有欠明确。”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欠缺,违法性的界定应该包括以上两种观点。
(二)行为违法说
行为违法说建立在对结果违法说批判的基础上。这主要是由於结果违法说对於远因加害行为违法性的解释上的无力造成的。“在德国学说上争论最热烈的是下列案例:甲制造汽车(剪草机、爆竹或其他家电用品)而使之流入市场,乙使用此等物品遭受伤害或侵害他人的权利时,如何认定甲之侵权行为的违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甲所制造的汽车没有缺陷,按照结果违法说,认定甲行为的违法性则存在很大的困难。行为违法说认为,仅仅是行为造成了他人合法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后果还不能认定该行为具有违法性,还应该考察该行为有没有尽到社会生活上所要求的一般注意义务。如果行为没有违反注意义务,那么即使它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也不具备违法性。
(三)一个纯粹的违法性概念
本文认为,结果违法说比行为违法说更具合理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从理论上讲,行为违法说将本来清晰的概念变成了复杂的和过错日趋相同的概念。结果违法说对於违法性的判断是基於民事权益受到侵害,而行为违法说则是基於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以及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缺失。可以看出,无论对於哪种学说,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存在是判断违法性必不可少的条件。至於行为违法说中对於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判断,则属於过错的判断标准。行为违法说将本属於过错判断的标准引入到违法性的判断之中来,导致两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出现重合,从而使得违法性的独立性受到损害,“这种理论实际上否定了客观违法的概念,而在违法的概念中包括了过失的概念”,行为违法说成为很多学者对於违法性独立价值产生质疑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从实践中看,虽然结果违法说和行为违法说在理论上的差别比较大,但是最终在绝大多数具体案件的判决上并没有导致不同的结果。“德国学者所以对此争议倾注了洪流般的墨水,系由於其善於争辩及问题本身所具高度理论上的魅力。行为不法说虽为学者的通说,但德国联邦法院仍然采取结果不法说,解释适用上并无疑义或困难。”
综上所述,违法性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结果违法说恰恰符合了这个标准。就目前来看,《德国民法典》对於违法性的规定是相对完备的。所以,违法性应该包括了三种情形:
第一,侵害他人权利。这里所谓“侵害他人权利”,就《德国民法典》而言,应该是其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各种法定权利,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该条文虽然列举了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等五种权利,但是“其他权利”的规定,使得全部民事权利都应受到保护。
第二,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中所谓“法律”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解释。所谓广义的“法律”,是指包括民事法律在内的,所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保护的法律。所谓狭义的“法律”,仅仅是指刑法、赔偿义务法等。本文认为,此处“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解释,其理由在於:只有采用广义的解释,才能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全面的保护。
第三,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法加害於他人。此种情形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所谓善良风俗,是指“社会之存在及其发展所必要的一般道德。”此处所谓一般道德,不应混同於一般的道德,而是具有法律意义的道德。故意违反此处一般道德,具备违法性。“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的规定在於补充法律规定的不足。众所周知,成文法的特点决定了其滞后性,仅依靠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已存在的保护他人之法律,并不能全面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善良风俗作为一个弹性条款的存在,不仅弥补了法律规定的不足,也为全面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益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权益侵害的实质
《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国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应当是权益侵害、过错、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从法律条文本身来看,并没有规定违法性,而是规定了权益侵害。在此,需要深入分析权益侵害的实质。
(一)权益的内涵
何谓“权”?“权”指的是民事权利。《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尽管《侵权责任法》采取了如此广泛列举的方式,规范了权利的范围,涵盖了民法和商法的领域,体现了我们“民商合一”的立法倾向,从而实现以侵权责任法来解决民商事领域的一切侵权案件。但是,这种列举方法并不能穷尽现有或将有的民事权利类型,例如夫妻之间的身份权,即配偶权。所以,在理解《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权利范围时,不能仅仅局限於《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明文规定的权利,应该包括所有的民事权利。
何谓“益”?“益”指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亦称为“法益”。对於法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广义的法益,认为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包括权利在内,都是法益;另一种是狭义的法益,认为法益是指不包括法定权利在内的,法律应当保护的利益。第一种观点对法益的认定似失之宽泛,不能完全体现权利与法益的区别。狭义的法益的界定更为合理。具体到《侵权责任法》中,法益应当是指除民事权利之外的,应当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身或财产利益。
通过上述对“权益”的分析,可以确定《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同时也能认定权益侵害的内涵,即侵害民事权利以及民事权利之外的应受到法律保护的人身或财产利益。
如果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仅仅限於民事权利,就会导致法律上的“权利侵害”与现实的“利益保护”之间的失调。“我妻荣博士批判道,由於在这种思想下,能够被认定为权利的对象狭窄,所以即使是加害行为违反道义,扰乱社会秩序的场合,也会被以未发生权利侵害为理由否定侵权行为的成立,这就阻碍了社会的提高和发展。”日本侵权法的发展过程中,“权利侵害”要件向“违法性”要件的发展证明将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局限於民事权利是不足取的。
(二)从权利侵害到违法性
《日本民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时,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这与中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非常类似。《日本民法典》本身并没有规定将违法性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是规定了“权利侵害”这一要件。
自《日本民法典》颁布后,日本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东京控诉法院在1912年判决中指出的:“这里所谓的权利……应该广义地解释为依照法律受到保护的利益,而不应解释为仅指例如所有权、质权、著作权那样特定的权利。”二是出现了严格运用立法者宗旨的判决,如1914年日本大审院的“云右卫门浪曲唱片案”中坚持了侵权法保护的对象仅限於权利的理论。1925年,在著名的“大学汤”案,大审院抛弃了过去的态度,作出了即使不能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但只要有“法律上应该予以保护的利益”受到侵害,也成立侵权行为的解释。这一判决被学说评价为代替权利侵害要件建立违法性要件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从云右卫门到大学汤’这一判例的动向,被学界视为司法机关对‘权利侵害’要件由僵直的狭义理解改作柔软而弹性的广义解释的划时代变更。受到这种流向的刺激,学说上也开始一个转变,即由‘权利侵害论’走向‘违法性论’;由‘权利侵害’要件移向‘违法性’要件。”
从日本侵权法中“权利侵害”要件的发展过程来看,中国《侵权责任法》中的“权益侵害”要件的优势是明显的。但是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现今日本的学界更多的主张“违法性”要件,并不单单止步於司法机关对“权利侵害”要件的广义解释。此中缘由值得深思。
(三)权益侵害的实质
权益侵害的实质是违法性的表现形式,之所以能构成侵权行为,还是在於违法性的存在,在於权益侵害破坏了现行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生活。正如同末川博博士在《权利侵害论》一书中所阐述的:“在比较了自罗马法以来包括罗马法在内的各种侵权行为制度后他发现,所有这些法律制度中均未将权利侵害作为侵权行为责任成立的绝对条件,在进一步研究后他指出,法律之所以规定权利不得侵害,乃因为侵害权利是破坏法律秩序的违法行为,权利侵害只不过是违法行为的表微。”尽管与权利侵害要件相比,权益侵害要件更能适应侵权责任法和社会的发展。但是,脱离了违法性,单纯的权益侵害并不必然成立侵权行为,权益侵害不适合作为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四、违法性的价值
违法性在以下三个方面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不能为权益侵害所替代。
第一,违法性为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自助和受害人同意的合理存在提供理论基础。
权益侵害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行为违法,无违法性的存在自然不会成立侵权行为,更谈不上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存在对於违法阻却事由的探讨。违法阻却事由主要包括:依法执行职务、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受害人同意和自助。《侵权责任法》第三章规定了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只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两种,如果严格依照《侵权责任法》,那么依法执行职务、受害人同意和自助既符合权益侵害的要件,又不属於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应当构成侵权行为,然而这三种情形不构成侵权行为已为中国司法实践广泛认可。
上述五种情形都是通过对一种民事权益的侵害达到保护法律所认可的另一种利益的目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情形为法律所允许,甚至是鼓励呢?正是因为本质上,这五种情形并非不属於权益侵害,而是不具备违法性,更对现行法律秩序的保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违法性为其合理存在提供了理论基础,尤其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的规定还有待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是权益侵害所不具备的功能。
第二,权益侵害范围过於宽泛、不易确定,容易导致司法任意,违法性的存在使得“法益”保护成为一个可控制的范围。
仅仅笼统规定应当保护民事权益,不能很好地解决《日本民法典》起草时的困惑,“侵权行为法是保护已经存在的权利的法律,而不是由此创设新的权利。社会生活中损害涉及他人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如果没有‘权利侵害’要件的限定,得以认定的侵权行为责任的范围就会没有边际,过於宽泛。”尽管后来的发展证明单纯的“权利侵害”并不足取,但是,对於侵权行为责任范围会没有边际的顾虑仍然是值得肯定的。“法益往往依赖於法官对法律理念或概括性法律原则的领悟得以实现。不同的法官基於不同的价值观念会做出不同的判断。”法益是否保护、如何保护完全依赖於法官的自由裁量,尽管有适用便捷之利,却也为司法任意开了方便之门。
《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权利侵害,其对法益的保护则是通过第823条第2款和第826条来共同完成,这使得“法益”的范围不至於过分宽泛:首先,第823条第2款,所谓“以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将法益限定在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范畴;其次,虽然第826条中善良风俗的规定,为“法益”的保护提供了更广泛的范围,但是,“故意”要件对此类民事利益的保护加上了较为严格的限定。换言之,只有在行为人故意的情形下,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他人才有可能成立侵权行为。《德国民法典》正是通过这样两条规定,既弥补了单纯规定“权利侵害”的弊端,又将“法益”保护限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同时,《德国民法典》中这三个条文,也确立了违法性作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地位,这种做法值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三,《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前,违法性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得到承认和应用。
篇3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而依法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要谈保护胎儿的民事权利,就必须首先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说起。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从而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只有在具备了民事权利能力的情况下,才被真正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才真正开始享有民事权利。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起始的时间是“始于出生”。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胎儿是否就是民事权利的当然否定主体?
一、我国胎儿民事权利立法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只体现在《继承法》第28条,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法律保护的范围还仅仅局限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保护就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的精神了呢?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栏目中曾有这样一个案例: 2001年的7月27日傍晚,当时已经怀有6个多月身孕的裴红霞在散步时被后面驶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到了肚子。她看清骑摩托车的是自己楼下的邻居钱明伟。于是,两人发生了争吵。由于没有太多的医学知识,吵完之后,裴红霞没有多想,仍旧继续散步,可到了当天晚上,下身便开始有少量的水流出。7月29日凌晨5点,裴红霞被紧急送往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后,被诊断为胎膜早破先兆早产,并进行抗炎保胎。8月8日,裴红霞被迫提前两个月早产了女儿吴佩颖。在出生医学证明书上,孩子的健康状况被评为差,体重只有2公斤。作为早产儿的小佩颖的身体将来能否发育正常,就必须需要家里人长年的精心护理,补充营养来预防早产儿的各种并发症,度过一段成长发育期,直到孩子完全发育成熟并一切正常为止。这不仅仅给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负担,而且也带来了经济上的负担。在医院住了十多天后,由于经济困难,孩子只好出院回家。裴红霞一家人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完全是因为那天被撞造成的,而当初撞人的钱明伟却再也没有露面。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刚出生33天的小佩颖当上了原告,和其父母一起要求赔偿孩子的生命健康权伤害费、医药费、护理费及其父母的精神损失费共计6. 3万元。庭审过程中,由于在事件发生时,吴佩颖尚在母体中,能否成为诉讼主体成为本案争论的焦点问题。最终,法院认为当时孩子未出生,在目前法律框架下,不具有法律的人的身份,她的利益只能通过母亲的名义得到保护,判决被告赔付裴红霞医药费等经济损失5455元,其余诉讼请求予以驳回。
从以上案例中不难发现,法律的不完善,不仅给法庭审理案件带来了困难,而且使胎儿的合法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胎儿是自然人发育的必经阶段,对胎儿的民事权利置之不理,这显然有悖于整个社会人权的进步,也有悖于民法以人为本的法律传统。
二、其他国家对胎儿民事权利的立法保护
早在罗马法时期,著名法学家保罗就提出:“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这对他毫无裨益。”这种法律的精神一直被一些国家和地区传承至今,但立法的方式不尽相同。
(一)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溯及取得民事权利能力
《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出生之前的胎儿,以活着出生为条件,有权利能力。《匈牙利民法典》规定:人如果活着出生,其权利能力从受孕时起算。这种立法的方法可以对胎儿的民事权利进行全方位的保护,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因为总括的给予权利能力,在保护的同时,也使胎儿可能成为民事义务的主体,在现实的法律应用过程中很可能会改变立法的初衷,将胎儿置于不利的境地。
(二)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在某些事项中有民事权利
《德国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1923条)、抚养人被杀时(第844条)视为已经出生,可以享有民事权利。《法国民法典》规定了胎儿在接受赠予方面的民事权利。《日本民法典》规定胎儿在继承(第886条)、认领(第783条)、损害赔偿(第721条)方面视为出生。我国《继承法》第28条的规定也是如此。这种立法方式针对性很强,容易操作,当同时具体的列举胎儿民事权力范围容易遗漏,难以给予胎儿严密的保护。
(三)胎儿出生时为活体的,对其利益的保护上视为已出生
这是一种附条件的保护立法方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条规定:“胎儿以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已出生。”这种保护方式,明确了在关于胎儿个人利益保护时,才视为出生,排除了胎儿作为义务主体的可能。同时,又可在胎儿民事权利保护需要的情况下,给予胎儿必要的民事权利,为胎儿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立法保护。无疑,这样的立法保护方式,是我国民法所需要借鉴的。
三、胎儿民事权利的范围
笔者并不主张对胎儿的民事权利保护完全等同于活着的自然人,而应该就保护的范围进行一下探讨,以避免我国立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一)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但由于胎儿的精神状态很难评估,因此,笔者认为胎儿的健康权是指在母体中时所享有的生理机能正常发育的权利。
胎儿在母体之中,仍会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外界侵害,而使健康权受损,如环境污染、劣质食品药品、机械性损伤等等。健康权作为胎儿的一种可期待权利,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有观点认为,胎儿必然依赖于母体的存在,当健康受损时,母亲有权以侵害人身权为由要求损害赔偿,因此再规定胎儿的健康权保护是画蛇添足。但不能忽略的是,胎儿尚在母体,健康的受损状况无法确定,只有在其出生后才能确定。
由此可见,对胎儿的健康权保护很有现实意义。许多国家的民法和判例也都认为在胎儿的健康权受到损害时,应当视胎儿为自然人。英国有一个判例法,阐明一母亲怀孕时服用某种药物,由于该种药物可直接导致胎儿成长后患乳腺癌,该胎儿出生成人患病后,起诉制药厂索赔,获得胜诉。
篇4
表见本质上属于无权,表见的行为人实际上并未取得权,仅仅是具有已获授权的外形或者表征。所谓外表授权,指具有授权行为的外表或假象,而事实上并无实际授权。表见与狭义无权共同构成广义的无权,我国多数学者持这种观点。表见本为一种无权,但由于权表象的存在,并引起了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就涉及到了交易安全的问题。
表见适用范围扩大化在外国法上的体现
表见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各种新法律关系的出现以及民法对交易安全的着重,应当将其适用范围不断扩张。
(一)《日本民法典》第109条规定,对第三人表示授予他人以权意旨者,于范围内,就该他人与第三人之间实施的行为,负其责任。第110条规定,人实施其权限外的行为,如第三人有正当理由相信其有此权限时,准用前条规定。
案例1:第一个判例是最高裁判所昭和44年12月19日判决。案情是本人甲授予人乙以不动产为担保借入金钱的权限,而人乙自称自己即甲本人,将该不动产出卖与第三人丙。而丙亦误信乙为甲,并与之订立购买契约。法院认为,人假称本人为权限外的行为场合,对方相信该行为为本人自身的行为时,并非相信人有权;但就该信赖值得交易上的保护之点来看,与信赖人有权的场合并无二致。因此,以信其为本人自身的行为并有正当理由为限,应类推适用民法第110条的规定,使本人对该行为结果负责。
案例2:东京地方裁判所于平成3年11月26日判决。案情是人乙超越权,订立金钱消费借贷契约及以本人不动产设定抵押权的契约,因金额巨大,对方当事人要求本人确认,人以第三人冒称本人在契约书上签名盖印。法院认为,本案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人有基本权;其二,对方相信该第三人为“本人”有正当理由。因此,应类推适用民法第110条,使契约效力及于本人。
这两则判例虽名为采类推适用方法,实际上属于以目的性的扩张方法,补充法律对人冒充本人及以他人假冒本人案型未设规定的法律漏洞。人冒充本人及人以他人冒充本人的案型,与第三人相信人有权的表见案型之间,并不存在类似性关系。对于上述案型适用法律关于表现的规定,其法理依据,不存在类似性,而在民法110条之规范意旨,即对交易上的信赖应予保护。
(二)表见适用范围扩大化在我国法律实践中比较典型的体现
1、表见制度在行政法领域的应用
在行政法上,所有的表见行为都无效,责任归由被机关承担,相对人应该以被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表见制度被行政法所移植和采用,不仅从概念与理论框架上分析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在行政法领域具有重大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行政实践中,委托行政大量存在并被广泛适用,较好地解决行政之不足,以缓解现实压力。但不应被忽视的是,被委托人与委托人一样也有滥用或者超越委托权限,行使委托权之可能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行政法上仅有关于委托的规定,据此规范,引进表见制度能解决委托人与被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而最重要的相对人与委托人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被委托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属于机关内部调整范畴,游离于法律的调整之外,虽然行政诉讼法对此有所规定,但其确定的也仅仅为被告资格,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性问题,并不能在实体上解决权利义务的归属。
表见源于私法,一直为行政法学界所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众多现象与问题,非仅处理内部关系的委托所能解决。与委托相伴而生,唇齿相依。制度,特别将表见制度引入行政法,既从理论上补充行政委托之不足,亦在实践中解决行政管理领域无权、越权情况下行政责任的承担问题,进而决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可化解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现实困难。
2、表见在职务行为中的适用
职务行为,即从事与其职务有关的行为。本文所讲的职务行为,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的,包括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各种性质的公司以及个体业主的雇员,只要为其雇主利益从事与其工作有关的行为,均称为职务行为。一般而言,要判断一个人是否从事职务行为,往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判断:第一、行为的时间和地点。通常情况下,雇员在其规定的工作时间内在工作岗位上实施的行为大多数属于职务行为。第二、以谁的名义和利益实施行为。一般而言,雇员在从事职务行为时都是以雇主的名义为雇主的利益而实施,;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则当然要自己承担行为的后果;第三、与其从事的职务有内在联系,并应该是为了雇主的利益。所谓有内在联系,是指与其从事职务行为有关,并排除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行为。雇员为其雇主利益并以雇主名义从事与其职务有关的行为,符合民法上的要件,本质上为一种行为,即雇员其雇主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可将这种行为称为职务,将雇员具有的这种权利称为职务权,与普通一样,职务当然也需授权,也就是说,雇员从事职务行为时,应得到相应的从事该行为的授权。
篇5
随着 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财产损害[1]的法律保护日趋完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均强化了对人的非财产利益的救济,从而彰显人的主体价值和尊严,体现人这一法律主体的特殊地位。通常而言,非财产利益的私法救济主要存在于侵权行为法领域,通过对人身权的法律保护加以实现;而伴随着的法律的演进,在合同法领域也逐步出现了非财产损害的救济渠道,即将非财产利益纳入违约责任的保护范畴之中。就中国民事立法和司法现状而言,非财产损害的侵权法救济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程度,而违约责任的非财产利益保护则似乎仍旧停滞不前,尤其在思维意识方面,尚未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因而,以比较法为视角,从认识外国法律制度着手,或许能为完善我国相关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本文以德国法上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变革为实例,通过对德国法上相关制度变迁的考察,旨在为我国民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Www..COM
一、德国民法对非财产损害的传统保护模式
传统的《德国民法典》对非财产损害的法律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条文之中。首先,依《德国民法典》原第253条的规定:损害为非物质上的损害时,仅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形下,始得要求以金钱赔偿损害。[2]这里所指的金钱赔偿,即抚慰金请求权。根据原第253条的规定,抚慰金仅得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才可被赋予。其次,依照《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第1款的规定:在侵害身体、健康以及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损害即使不是财产上的损失,亦可以因受损害而要求合理的金钱赔偿。然而,依原第847条在法典中所处位置,其列于侵权行为的相关规定中,即此处所谓侵害身体、健康以及剥夺自由均应建立在侵权行为的基础上。又因为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在归责原则、赔偿范围、消灭时效等方面存在相当的差别,以侵权行为为基础保护受害方的身体、健康及自由等非财产利益的重要前提是侵害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依侵权行为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如果严格依照《德国民法典》上的这种传统的保护非财产利益的模式,将会严重妨害非财产利益的保护。因为原第253条所设置的最主要的法定例外情形即是原第847条之规定,而后者所指乃侵权行为,因而非财产利益的保护主要放置于侵权行为法之下,合同法上几乎不提供任何有效的保护。
显然,这样一种过于狭隘的立法模式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长期的困扰。法院在实践操作中无法完全遵守《德国民法典》之原有规定,特殊案件中它们往往规避原第253条的规定,发展出一些规则,以符合强化非财产权益保护的趋势。在对既有规定进行规避时,德国法院主要采取两种方向的努力:一方面,以《德国基本法》上保护基本人权的第2条、第3条为基础,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一般人格权”的概念,从而突破了原第253条法明文规定之限制,而“一般人格权”最大的特点是其内涵的广泛性及不确定性。[3]当然,以“一般人格权”的方式强化对非财产权益的保护仍然是在侵权行为法的框架内进行的,它以侵权责任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基础;另一方面,将一些非财产权益“商业化”,即将某些实质上为非财产性质的损害视作“商业化”后的财产来看待。[4]原第253条调整的范围仅限于非财产损害,而非财产利益被“商业化”后即不再受原第253条的限制,从而实质上扩大了非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并且,这种“商业化”的方法并非仅以侵权责任为基础,还包括了其他责任基础如合同责任,因为财产损害是整个民法主要保护的对象。尽管法院在实践中作出了种种努力,立法者也在局部进行了一定的变革,但尚不足以实现对非财产损害的充分保护,由此产生了对相关法律进行改革的现实需求。
这项变革需求最终在2002年4月18日德国议会颁布的于2002年8月1日生效的《关于修改损害赔偿法规定的第二法案》[5] (以下简称《第二法案》)中得以实现,该法案对《德国民法典》原第253条及第847条作出了重大调整。原第253条的内容仍得以保留,但在此后增加了一款,即现第253条第2款:因侵害身体(body)、健康(health)、自由(liberty)或性的自我决定(right of sexual self-determination)而须赔偿损害的,也可以因非财产损害而请求公平的金钱赔偿。[6]《第二法案》同时取消了原第847条,即关于非财产损害金钱赔偿法定性要求的抚慰金条款。这样,在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方面,非财产权益的保护不再以侵权责任为唯一基础,包括合同责任在内的其他责任同样可以为非财产权益的保护提供依据,这被称为《德国民法典》上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一次“划时代变革”。 [7]下文以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为研究对象,以合同责任为主要分析基础,来探讨德国法变革前后合同责任在非财产损害方面的地位和功能演变。
二、《德国民法典》传统的突破:以 旅游 合同、雇佣合同为例
依《德国民法典》最初的规定,非财产损害的保护须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前提,而相关规定主要集中于侵权法领域。在合同法领域,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没有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因而是完全被禁止的。然而,这样一种过于僵硬的保护模式,导致了相当的非财产损害不能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
(一)旅游合同
具有代表性的非财产权益遭受损害的例子是旅游合同项下的假期利益。原则上,旅游合同中的假期利益(因旅游而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属于非财产权益,但《德国民法典》上最初并不保护此类利益。若死守此种思维定式,势必会导致相关当事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适当保护。事实上,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的实践中,逐渐发展出一套规避原第253条规定的方法,即通过假期商业化,使旅游合同下的假期利益具有财产性质,因而不再受到第253条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的特殊限制。[8]所谓非财产损害的商业化,是指凡是交易上可以支付金钱方式“购得”的利益(如享受娱乐、舒适、方便),依据交易观念,此种财产即具有财产价值,从而对其侵害而造成的损害,属于财产上的损害,被害人得请求金钱赔偿。[9]
旅游合同项下以违约责任为基础的案件,系追究违反旅游合同者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包括对“商业化”假期的赔偿责任。显然,将假期商业化是规避第253条规定限制的有效方法,但其在理论构成上(即方法论上)却过于勉强。将事实上属于非财产损害性质的假期视作具有财产性质,人为拟制的色彩过于浓重,实为应对法律之举。同时,假期过分商业化也会引起法律上保护利益的失衡。前已指出,假期商业化的后果使得此种非财产损害可以获得赔偿,其所依据的基础并不限于合同责任,理论上并不必然排除侵权责任。但倘若在侵权责任之下,使假期过分“商业化”,可能会引起侵权责任不适当地扩张,反过来,打破了法律上的均衡,有矫枉过正之嫌。事实上,法院对以侵权责任为基础,使假期过分商业化的做法表示了反对,拒绝以假期商业化作为承担侵权责任的依据。由此可见,尽管假期商业化为旅游合同上的非财产利益提供了强化保护,符合社会发展之需要,但该理论本身在构成上具有相当的缺陷,受到了学者的强烈批评。
1979年《德国民法典》修正时,增列了旅游合同,并在第651 f条第1项规定:游客在不影响其减少费用或者预先解约权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因不履行的损害赔偿,但旅游瑕疵是基于不可归责于旅游举办人的事由的除外;第2项规定:旅游无法进行或者明显受损害时,游客也可以因无益地使用休假时间而要求以金钱作为适当赔偿。通说认为,此种立法规定已不采取商业化的理论,将假期视为一种财产价值;此条文乃第253条所谓“虽非财产上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金额”之特别规定,[10]即遭受损害的旅游合同当事人可仅因符合该第253条之特殊规定,而得到假期这种非财产损害的赔偿,无需再以假期商业化理论为基础,请求赔偿商业化的假期。一般认为,第651f条第2项规定了第253条第1款的其他法定例外情形,即对于非财产损害的金钱赔偿不以身体或健康损害(修订后第253条第2款)为要件。基于这样的认识,衡量金钱赔偿额度时不应只考虑劳动收入这一尺度,相反还应考虑其他情形,特别是应当考虑瑕疵造成侵害的程度。此时,个人的抵抗能力(如抵抗噪音的能力)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另外,对于无劳动收入的人,也要考虑其损害赔偿请求权。[11]德国立法上的这种转变值得关注。
(二)雇佣合同
除了旅游合同之外,雇佣合同也是明确可以请求赔偿非财产损害的合同法领域,它主要体现在1998年《德国民法典》修订时增加的第611a条第2款和第3款,即因雇主性别歧视而请求适当的金钱赔偿这一特殊的赔偿问题。[12]2006年8月18日,德国《平等待遇法》(allgemeines gleichbehandlungsgesetz)在长期讨论后终于生效,该法是一部专门反歧视的立法,涉及劳动法、一般合同法及公法领域,其影响深远。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反歧视立法体例,并对现有的相关立法作出了一定的调整。该法生效的同时,《德国民法典》原第611a条、第611b条被废除。《平等待遇法》对非财产损害赔偿给予了更为一般性的规定。[13]该法第15条主要规定了雇佣关系下的歧视性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及非财产损害的赔偿;第21条规定了该法所涉及的其他私法关系(如针对一般大众提供的货物及服务的私法合同、 教育 、医疗治理)情形下的歧视性损害赔偿,其中同样包括非财产损害。[14]
(三)其他情形尽管如此,在旅游合同及雇佣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中,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仍然受到第253条的严格限制,几无取得赔偿之可能。这表明,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突破仅限于旅游合同等极为特殊的合同领域,在其他合同中,即便也涉及合同当事人重大的非财产损害,这些损害仍然无法获得赔偿。以下这则发生于1998年的案件可以清楚说明德国法传统上对违约非财产损害排斥之态度。
在预订婚礼房间案[15]中,原告寻求在其针对被告提起的关于精神痛苦和折磨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得到法律支持。本案中,原告新娘与被告宾馆缔结了一份合同,约定被告在1997年6月27日晚上(也就是新娘结婚当天)为原告提供一个带壁炉的能容纳12人的房间。由于被告的过失,该房间在那天晚上已经被其他人提前预订并使用了。由于未能获得适当的替代房间,原告晚上计划的婚礼庆祝仪式未能举行。因为这场“灾难”,原告连续数日以泪洗面,她的精神压力达到了极限,并且遭受了心理上的打击(psychologicalshock)。原告于是对其遭受的痛苦及折磨请求赔偿3,000马克。初审法院拒绝了原告的请求,理由是由于原告未遭受物质上的损失且不能对违约引起的痛苦、折磨给予赔偿,原告的诉求不会得到支持。高等法院对此表示赞同。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论述道:“本案中,原告针对被告提起的赔偿精神痛苦的诉讼请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47条不会被考虑,除非被告在违反合同未能保留房间之外,同样给原告造成了符合823(1)条形式的身体上的或健康上的损害。然而,原告提起的诉讼并不构成此种诉求。
在此,我们不应考虑因违约引起的合同当事人精神状态的干涉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包含在823条的保护性目的范围内。即便该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初审法院对此并不认同),原告仍然未能对痛苦及苦难造成的损害赔偿提供足够的事实基础。
首先,原告未能提起正确的诉讼,即原告以被告的违约行为造成了原告身体上或健康上的伤害为由提起诉讼欠准确。的确,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当事人必须对其应负责的行为所造成的精神状态的损害承担责任,但需该行为引起的受害方精神上的损害足以构成身体上或健康上的损害。然而,诸如本案的一类案件中,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给受害方造成的精神上的损害如果能够成为可以请求对方承担责任的损害形式,该精神损害的种类、强度及持续期间必须明显超过日常生活中不欲事件的正常反应,至少可以将其与疾病的效果相比较。本案中,原告声称她因为‘这场灾难终日以泪洗面’且‘数周未能正常与人谈论此事’,原告认为其承受的精神压力达到了极限值并遭受了精神上的折磨(该观点在没有进一步事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不能被支持)的事实,未能显示被告违反合同的结果达到了上述要求。
无论如何,即便根据原告的主张,该精神上的挫折达到了相应的严重性要求的程度,原告的请求仍不能成立,因为被告并不存在过错。这里必须清楚的是,被告的过错不仅应包括被告未能保留房间的违约行为的过错,还必须包括该违约行为造成精神上损害结果的过错,而这正是承担责任的基础。当然,在应用适当程度的注意时,酒店店主必须认识到由于其过错未能为新娘的婚礼庆祝仪式保留预订的房间会给新娘造成消极的心理反应,甚至是严重的伤害。然而,在没有相反表示的情况下,被告不能预见的是在通常情形下,原告反应的种类、强度以及持续期间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可以构成身体上或健康上的损害。”
其实,在其他国家的合同法上,与婚礼相关的合同纠纷案件往往较为可能获得非财产损害赔偿,因为与婚礼合同紧密相连的是重大的非财产利益,法律如果对这些重要的精神利益完全漠视,势必会造成合同正义的落空,无法为合同当事人提供足够的保护。而《德国民法典》原有的规定恰恰体现了一种完全悖离于现实的规则,法律与社会之间过分的脱节也必然会引起法律改革的呼声,从而使法律规定跟上社会发展的实践,有效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正当利益。这种改革一定程度上在2002年的《第二法案》中得以实现。
三、《德国民法典》2002年修正后的情形
(一)条款的变化
《德国民法典》原第847条位于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第八章(各种债务关系)第二十七节(侵权行为)中,属于债法分则中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因而,相关的非财产损害仅得以一般侵权行为为基础请求赔偿。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将原第847条的主要内容转移到了第253条第2款之中,该条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处于第二编(债务关系法)第一章(债务关系的内容)第一节(给付义务),属于债法总则,其规定适用于债法调整范围内的所有情形。尽管原第847条第1款与第253条第2款在内容上大体相似,但由于编排体例的变化,使得符合相关条件取得损害赔偿的依据不再局限于侵权行为,而是扩大到包括合同责任、危险责任在内的整个债的范围。另外,《德国民法典》第249条至第255条涉及的是一般性的损害赔偿的规定,它们不仅调整债法分则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也调整其他各编中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甚至还调整《德国民法典》之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由此可见,修正前后的变化异常重大,致使原来适用非常狭隘的条款,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得以适用。
(二)修正理由
关于抚慰金条款修改的理由,德国联邦司法部在《关于修改损害赔偿法规定的第二法案草案》中给予了充分的说明。第一,这种调整是为了消除法律上的不一致状态。修正之前,抚慰金请求权仅存在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中,而在不取决于过错的危险责任以及合同责任的范围内(除少数例外情形)均不存在抚慰金请求权。由于在危险责任与合同责任范围内排除了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在这些领域内发生的身体、健康和自由受到严重侵害而造成的非财产损害均无法获得赔偿。另外,从受害人的角度看,同样是非财产损害,由于责任基础不同,在侵权行为领域得到赔偿,但在其他领域则无法获得赔偿,造成了法律上的差别。修正后的法律正是创设了一个统一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即在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决定受到侵害时,不再区分责任基础,而均可给予金钱赔偿。第二,这种调整也是为了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法律相适应。如在法国和英国,并没有将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限制在合同之外的明确规定。[16]
事实上,上述理由并不充分,就第一点理由而言,考虑到各个法律领域自身的特点,尤其是侵权法与合同法之间的种种差异,对同样的损害在不同的责任基础上予以区别对待实乃常事。比如,惩罚性赔偿在侵权法领域大量存在,但在合同法领域则一般认为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侵权法除了补偿受害方的损失外,有时还兼有惩罚、阻吓侵权行为人的功能,而合同法救济的目的主要是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因而不具备惩罚的功能。这里恰当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同样的非财产损害在不同的责任基础上绝对的赔或不赔是否符合债法相关部分的目的,这样的区分是否过于绝对,尤其是在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日益融合的今天。因此,第一点理由在理论上绝非完全不存在可议之处。[17]就第二点而言,《德国民法典》大幅度修正的目的之一便是与欧盟其他国家的法律更为接近,从而在欧洲法律统一化的进程中扮演更为重要和积极的角色。然而,就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而言,欧盟各主要国家的立法和实践差异相当大,例如修正前的德国民法除极少例外,完全排斥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而法国法上的做法则恰恰相反,法国法非常慷慨地在合同法领域给予非财产损害赔偿,而与侵权法上的损害赔偿不加区分;英国法上,早期著名的addis v.gramophone co ltd案[18]确立了违约非财产损害一般不予赔偿的原则,但随着社会的演进,逐步发展出了一系列的例外,主要包括合同的重要目的在于提供精神上的利益以及违约行为引起了身体上的不便或不适的情形。因此,就一定情形下给予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而言,德国法修正后与法国法、英国法较从前更为接近,但由于英、法之间模式的总体上的对立,德国法的修正很难说推进了欧洲合同立法的统一化进程,德、法、英三国之间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相当的差异。
另外,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教授所著《侵权行为法》一书中,在论述《第二法案》对危险责任下非财产损害赔偿改革时提及了两点立法理由:第一,对于立法者来说,协调与欧洲邻国的法律规定也很重要,因为在这些规定中,在保证痛苦抚慰金时,一般未根据过错而有所区别。第二,立法者还强调了这一新规定对审判程序合理化的效果。现行法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一定的领域内,创设一个以简单客观的风险分配为基础的补偿机制,而这一目的在原法中实际上却无法实现,因为原法对痛苦抚慰金的规定,总是会涉及侵权行为法的过错责任。[19]前述第一点理由前文已提及,但是,此处换了一种说法,即非财产损害的赔偿不应以过错为基础(侵权责任),在非过错的情形下,应同样给予保护。《第二法案》的改革的确减少了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在非财产损害赔偿领域的差距,但仅仅这样的改革力度,离统一化还有过于遥远的距离。并且,如果单从协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出发,德国的立法者完全可以放开手脚,而不是畏畏缩缩地将保护法益限定于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领域。德国法改革后对非财产权益的保护水平,实际上并不一定达到英国的水平。比如婚姻相关合同,葬礼合同等情形,德国法似乎仍然无法给予足够的保护。就第二点理由而言,“创设一个以简单客观的风险分配为基础的补偿机制”的确是一个具有相当说服力的理由。但是,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为何立法者不可以将这样一种简单客观的补偿机制推广到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领域之外的所有领域呢?如果将现有的机制扩张到任何非财产损害的情形,似乎更符合这种简化的思维模式。
《德国民法典》上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立法理由尚有可议之处,仅上述理由似乎并不能充分充分说明立法上颠覆式修正的理由,尤其是在思维严谨的德国法上,这样大幅度的变革显得尤为不成熟。[20]
(三)新条款适用条件
依据《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获得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前提是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了侵害。由于修正后的法律体例的变化,抚慰金赔偿义务建立的法律基础不再局限于侵权行为,而是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与原第847条内容相比,第253条第2款除将适用条件扩大到“性的自我决定”上,并无明显变化。而第253条第2款所涉及的身体、健康、自由的内涵亦与第823条第1款中之相关概念一致。[21]
1.关于侵害身体与健康。对身体的侵害是指对外部身体完整性的损害。与侵害身体相反,侵害健康是指对内部身体完整性的损害(即造成身体内部功能的紊乱)。侵害身体就是指损害身体的完好性。侵害健康是指任何身体机能不利的反常状况的产生或加重,而是否导致痛苦或身体状况的重大改变则并不重要,简而言之,就是侵扰了一个人生理、心理或者精神的正常状态,使其产生了病态。按照通说,只要损害了身体的完好性,为 治疗 疾病而实施的手术也是侵害身体的行为,但通常这种行为都是免责的。
2.关于侵害自由。第253条第2款保护法益的自由,并非与一般的行为自由意义同一,通说将其理解为身体的活动自由,或者说是离开某一地点的可能性。实践中,侵害自由最重要的案例是对人进行监禁,以及以违反法治国家原则的方式促使国家机关对人进行拘捕。如果某人因过错引起 交通 堵塞,则其行为并不构成侵害他人自由,因为交通堵塞而受到影响的当事人仅仅是不能开动其机动车,其身体活动的自由并没有受到妨害。[22]
3.关于侵害性的自我决定。《德国民法典》原825条的规定为:以欺诈、威胁或者滥用从属关系,诱使妇女允诺婚姻以外同居的人,对该妇女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有赔偿义务。原第847条第2款规定:对妇女犯有违反道德的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或者以欺诈、威胁或者滥用从属关系,诱使妇女允诺婚姻以外的同居的,该妇女享有相同的请求权(抚慰金)。修订后的第825条为:因欺诈、胁迫或滥用从属关系而诱使他人实施或容忍其(性)行为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修订后的第825条保护的对象有所扩大,即受害方主体不受年龄、性别及婚姻状态的限制。原第847条被废除,其主要内容移转到修订后的第253条第2款中,其保护的主体与第825条保持一致,亦有相应的扩展。因此,违反第825条造成非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第253条第2款作为依据,请求赔偿非财产损害。事实上,法律修订前后的变化,主要反映在保护对象范围的宽窄上,具体内容并无实质性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侵害性的自我决定现在并不限于婚姻之外,而是延伸到婚姻之内,受到侵害的配偶一方同样享有请求权。
尽管依第253条第2款,非财产损害的可赔偿性是以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侵害为前提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身体、健康或自由遭受了侵害,即可主张抚慰金请求权。依照德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如果受害人的健康只是短时间且微不足道地受到损害,则不能请求抚慰金。对此,德国法院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案例。并且,一般而言,只有在其他救济方式不能为受害人提供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法院才会给予非财产损害赔偿。[23]
(四)制度分析
2002年德国法上相关制度修正后,在一定的法益范围内肯定了一般性的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因而,可将其称之为“有限的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根据《德国民法典》修正后的第253条第2款,在身体、健康、自由以及性的自我决定的法益范围内,承认以违约责任为基础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权,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划时代变革”。然而,与法国法的模式相比,修正后德国法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显然要“吝啬”得多,法国法上无论何种合同何种法益受到侵害,均得请求非财产损害救济;而修正后的德国法则明文限定于“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受侵害的情形,只有在此范围内才不考虑救济的责任基础。除此之外,即便存在严重的非财产损害,囿于第253条法定性的限制,很难得到 法律 上的救济。
德国法上的这种模式并非首创,在2002年德国法修正之前,其他国家、地区已有类似的立法例,如瑞士、荷兰及我国的 台湾 地区等。《瑞士债法典》第九十九条(责任程度及赔偿范围)规定:“1.债务人一般应当对其任何过错行为承担责任。2.责任的程度依交易的具体性质而定,特别是在欠缺为债务人谋利益的故意时,应当考虑减轻责任。3.对上述问题,侵权法中有关责任 计算 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之内同样适用于合同过错行为。”根据该条第3款之规定并结合法典上的其他规定,均体现了在一定的法益范围内,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样可以成立。[24]《荷兰民法典》第6:095条规定:“根据损害赔偿的法定义务应当予以赔偿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其他损害,后者以法律赋予获得相应赔偿的权利为限。”第6:106条第1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权要求财产损害以外其他损害的公平赔偿:a、该责任人有加害的故意;b、受害人遭受身体伤害、荣誉或名誉的损害或者其人身遭受了其他侵害;c、对死者未分居的配偶或者二等以内血亲对死者的怀念造成伤害,但以该伤害在死者在世的情形下会产生他对荣誉或名誉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为条件。”[25]我国台湾民法典中有关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条文,包括第18条第二项、第194条关于侵害他人生命权、第195条第一项(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或其他人格法益的情形)、第977条第二项、第979条第一项、第999条第二项、第1056条第二项关于婚约、婚姻之解除或撤销而对无过错方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但1999年修订后的台湾民法典于“债之效力”一节中增加了第227-1条,增订“债务人因债务不履行,致债权人人格权受损害者,准用193条至195条及第197条之规定,负损害赔偿责任”,即在债务人违约造成债权人人格权受损害的情况下,应当认为债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26]由此可见,尽管瑞士、荷兰及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具体法律规定上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均与修正后的德国法模式大体相似。
修正后德国法模式的优点之一在于可以避免全面性的颠覆,将此种变革的影响力控制在一定的法益范围内(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这对于传统上排斥违约非财产损害抚慰金赔偿的德国法来说显得相对较为容易接受。换言之,在有限的法益范围内肯认违约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而除此之外的其他非财产损害情形则加以否定,此种“中间路线”式的进路实乃妥协的产物,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缓减了持传统观念的人们的担忧。
违约行为造成非财产损害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引起非财产损害的违约行为同样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在此情形下,存在所谓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尤其是当违约行为侵害了合同当事人的人身权时,这种责任上的竞合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前述 旅游 合同之下,旅客遭受了身体伤害的情形。按照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观点,此种情形下,可由受害的当事人选择以违约责任,抑或以侵权责任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其二,违约行为造成了非财产损害后果,但违约行为本身并不符合侵权行为的相关要件,无需承担侵权法上的责任,而只需对违约引起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本文将此种情形称为“单纯由违约引起的非财产损害”类型。由于不存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此类情形并不涉及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问题。比如,旅游合同下,并未造成人身伤害时的,无益度过假期的损害即为适例。由于不存在侵权责任,此类情形下的非财产保护途径仅为违约责任,因而,当违约责任下不包括非财产损害救济,相关精神损害将无从得到法律的保护。
分析修正后德国法上的违约非财产损害的制度模式,其重要意义在于:德国法上确立一般性的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领域是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等法益遭受侵害的情形,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一般并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大致上可以对应于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及性自主权等人身权,换言之,违约行为引起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损害时,往往也可能构成了侵犯相关人身权的侵权行为。从而在多数场合下,德国法修正后的非财产损害保护大都可以归类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相竞合的情形,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存在竞合的情形下,引入违约非财产损害的实际影响主要在于,为受害人提供不同救济渠道的选择,拓展在此类情形下非财产损害的救济方法。由于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在构成要件、举证责任、时效期间等方面存在着相当的差别,对于受害的合同当事人而言,选择不同的责任基础当有重大的实际意义。比如,前文所述旅游合同下,违约责任对痛苦和折磨形式的非财产损害不提供保护,而侵权法上则予以救济;未伴有人身伤害的旅游合同下,可由当事人约定赔偿损害的限额为旅游费用的三倍(第651h条);时效期间上,合同下的时效期间较短(一个月或者两年),而侵权法上的时效期间往往较长,一般为三年。如此一来,便可以解释缘何联邦最高法院倾向于在旅游合同之中加入侵权法的责任。
然而,在单纯由违约行为引起非财产损害的情形下,修正后的德国法尚难提供法律上的有效救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等法益受侵害时,往往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而极少出现单纯由违约引起非财产损害的场合;同时,这些法律保护利益的范围仅仅构成整个法律保护非财产利益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上这些法益的涵盖范围相对有限,相当部分的非财产权益无法纳入这些法定保护利益的范围,因而在单纯由违约行为引起非财产损害的情形下,修正后德国法模式的效用仍显得非常有限。实际上,越是单纯由违约行为引起的明显精神损害的情形,其对于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需求度越高。德国法此次修正所采用的立法模式与现实保护非财产利益的强烈需求仍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德国法的修正模式还带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如何有效地确定受违约责任保护的非财产法益的范围,换言之,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的保护范围是否具有理所当然的内在合理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一结论可以通过将德国法与瑞士法、荷兰法、台湾地区法进行比较后得出。瑞士法主要以人身及名誉为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对象,就保护的范围而言,仍然显得比德国法更富于弹性;荷兰法上,以“身体、荣誉、名誉或其人身”为违约非财产损害救济制度的保护对象,由于立法上采用了较为灵活的语言,因而在法律适用中具有较大的解释空间,比德国法的法益保护范围要灵活宽泛得多;台湾地区法保护利益的范围系侵害人格权,范围亦较德国法为宽。由此可见,德国法将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一般性的限定于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受侵害的范围内,而将名誉、隐私等人身权利排除在外,其内在的合理性值得商榷。
(五)案例适用分析:预订婚礼房间案
由上分析可知,当出现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侵害等非财产损害情形时,修正后的《德国民法典》不再固守原有的以侵权行为为依据的窠臼,而是将抚慰金请求权的基础扩大到合同责任及危险责任,从而实现了德国债法上抚慰金制度的一次“ 历史 性变革”,彻底变更了非财产损害赔偿取得的依据,进而在合同责任、危险责任领域引入了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然而,应当注意到,德国法上的抚慰金制度的变化严格局限于身体、健康、自由以及性的自我决定法益范围内,除此之外的其他非财产利益仍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而且,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无论如何灵活地加以解释,其所涉及的非财产利益只是众多非财产利益中有限的一部分,大量非财产利益由于受到第253条第1款的限制而无法得到相应的保护。因此,从实践的角度看,德国民法上抚慰金制度变化的“历史性”意义也要大打折扣。尤其与英、法等国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相比,德国法上的变革仍然是谨小慎微的。
以前述预订婚礼房间案为例,修正前的德国法院实践不支持原告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假定该案的发生时间是在2002年8月1日《第二法案》生效之后,原告提出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能否得到支持?在前述法院的判决中,已经论证了侵权责任无法成为取得抚慰金请求权的基础,加之其与危险责任无涉,此处需详加分析的主要是合同责任。根据修正后的第253条规定,如果原告的身体、健康、自由或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侵害并存在非财产损害,原告即可以合同责任为依据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结合该案案情,新娘所受到的损害主要表现为“终日以泪洗面”、“达到了承受压力的极限值”、“数周未能正常与人谈论此事”等,作为婚礼的相关案件,新娘所遭受的这些精神上的损害完全属于正常人可以理解的范畴。然而,除非有证据表明新娘的精神损害达到了侵害身体、健康及自由的程度,否则无法取得非财产损害赔偿。对照上述关于侵害身体、健康、自由的界定,新娘遭受的感情上的痛苦很难纳入相关保护利益范围之内,即便扩张解释也很难达到此种效果。因此,《第二法案》修正后的第253条尽管将责任基础从侵权责任扩展到合同责任及危险责任领域,但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以外的其他非财产法益仍然游离于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本案即为例证。原告新娘所遭受的精神损害为社会上一般人所公认,而近乎“吝啬”的立法模式使其精神抚慰金之请求几无实现之可能,此与实质公平与正义明显有违。环顾德国左邻右舍,无论是一般性肯定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法国法,抑或例外情形下给予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英国法,毫无疑问都会在类似情形下支持原告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以弥合其遭受的精神痛苦。以此视角观之,尽管第253条的修正是历史性的,但其重要意义更多体现在理论蕴味上,而非司法实践中。换句话说,德国的立法者在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领域迈出的只是“理论上的一大步,事实上的一小步”。
四、结论
《德国民法典》颁布实施百余年来,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即抚慰金请求权)原则上仅存在与侵权行为法领域。尽管在旅游合同和雇佣合同领域,司法和立法均先后为抚慰金请求权开启了有限的例外,但原则性的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得到法律的承认。在危险责任领域同样如此。2002年《第二法案》生效实施后,在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遭受侵害的情况下,无论是以侵权责任,还是以合同责任、危险责任为基础,受害方均可以请求非财产损害赔偿。因此,在“身体、健康、自由及性的自我决定”这些非财产利益范围内,一般性的抚慰金请求权得以确立,而无需考虑其责任的依据,实为此百年法典在抚慰金制度上的一次重大变革。经由这样的变革,抚慰金请求权适用的标准得到了统一,法律不再区分合同与非合同、过错与非过错,使得相关法律的适用更为清晰流畅;同时,该变革使确认抚慰金请求权的基础从侵权责任延伸到合同责任与危险责任,大大扩展了抚慰金的适用范围,抚慰金请求权的主体在性的自我决定方面也有所扩大。法律上的变革强化了对受害人非财产利益的保护,简化了对非财产损害的保护程序,适应了社会 发展 与进步的需要。德国法采用的此种变革模式不失为一种值得效仿且行之有效的法制渐进模式。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违约责任下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定性尚存在不同的认识,有完全排斥者,有完全肯认者,亦有有限承认者,因而,德国法上的变革为我们从观念上认同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的合理性奠定了思想基础,至少,违约的非财产损害赔偿不再是天方夜谭式的空想。作为 中国 法主要借鉴对象之一的德国法经历了如此的变革,势必可以更新我国学者和司法者的观念,消除他们心理上的障碍。德国法上的变迁为中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演进提供了具体的 参考 模式:即我国亦可以尝试首先在亟待保护的法益范围内对非财产损害实施救济,进而推进全面建立一般性的违约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如是,则既可以为相关法益的保护提供现实的渠道,又能够避免全面变革可能带来的震荡与不安。
注释:
[1]本文中所谓之非财产损害(non-pecuniary damage、non-financial damage、non-economic damage、non-patrimonial loss),与精神损害(mental sufferings、intangible loss)以及非物质损害(immaterial damage)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均指受害人的非财产性质的损害。对于“非财产损害”的内涵界定,参见程啸:《违约与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3页。
[2]《德国民法典》,郑冲、贾红梅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本文所引用之《德国民法典》条文,除另有说明外,均以该翻译版本为参照。
[3]关于德国法上一般人格权发展较为详尽的论述,参见p.r.handford,moral damage in germany,27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49,1978.关于一般人格权的内涵界定,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219页。
[4]关于商业化的理论,参见下文旅游合同部分的相关案例和论述。
[5]bgbl.2002 i 2674.
[6]《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