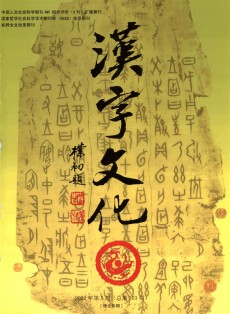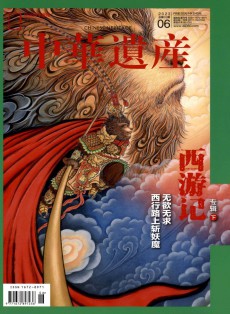汉字与古代文化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5:35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汉字与古代文化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与大火相对的是微火,微火最初用“幽”字表示。“幽”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会意,其中即丝字,丝线的特点是比较细微,故从火从正可以表示微火之义。引申为凡微小之称。《尔雅•释诂》:“幽,微也。”如今杭州等地仍将微火叫作幽,这是古代汉语在现代方言中的遗留。由于甲骨文中“山”和“火”形体相近,经常发生混同,所以后来“幽”字就变成从山了。《说文解字》中小篆的“幽”字作,从山从,这其实是从火从的讹误。
《管子•轻重》记载:“炎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腥,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学会用火加工食物,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如“炙”字,小篆作,《说文解字》云:“炮肉也。从肉在火上。”所谓“炮肉”,就是以火烤肉。籀文作,添加了一个表示肉串的偏旁,进一步说明了“炙”的具体方法,是将切割好的肉块用东西串起来进行烧烤。《诗经•小雅•瓠叶》:“有兔斯首,燔之炙之。”毛传曰:“炕火曰炙。”孔疏:“炕,举也。谓以物贯之而举于火上以炙之。”这些释义正可与《说文解字》籀文相印证。火烤是人们最早掌握的加工食物的方法,后来随着陶器的发明,人们才知道燃火于器皿之下,用沸水来煮熟食物。例如“爨”字的构形,正反映了烧火煮食的形象。“爨”字小篆作,上像两手持釜甑等灶具之形,中间“冂”像灶门,下像两手持木柴添入火中,几个部件组合在一起,正是一幅烧火做饭的画面。
除了用来熟食,火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照明。如“叟”,现在作老叟讲,但其最初的意思是搜寻。“叟”字小篆写作,甲骨文作,上像屋舍,下像一只手高举火把,组合起来正是手持火把在屋中搜寻的形象。隶楷之后,“叟”的形体发生讹变,全然看不出本来的意思了。据《方言》记载,战国时代齐、鲁、卫等国将老人称作叟,《说文解字》也说“叟,老也”,可见“叟”作老叟讲也是很早就出现了。为了区分搜寻和老叟这两个意义,人们便在表示搜寻义时增添了提手旁,写作“搜”。
火在古代田猎活动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原始围猎的主要方法就是焚田。所谓“焚田”,就是以火烧毁丛林草木,使百兽无处隐匿,最终被火围困在中央,便于集中捕杀。《尔雅•释天》:“火田为狩。”郭注:“放火烧草猎亦为狩。”“焚”甲骨文作、、、、、等形,从火从林,或从火从,或从火从木,像以火烧草木之形。古文字中从与从林、从木意义往往无别。甲骨文“焚”字还可以写作,这是较为复杂的写法,下面增添了秉持火炬的一双手,但整个字的构意并没有发生变化。商代卜辞中,提到“焚”的时候都是指的田猎之事,这可能是由于上古时代草莽丛生,禽兽繁衍,所以卜辞屡见焚田的记述。如《甲骨文合集》10198片:“翌戊午焚,禽(擒)?”意思是说,第二天以烧山林的方式打猎,能够擒获野兽吗?先秦其他典籍中也有不少焚田围猎活动的记载。如《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于大陆,焚焉。”《孟子•滕文公》:“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可见,这种围猎方式在古代十分常见。但是,焚田而猎的方式有似于竭泽而渔,不利于动物的繁衍,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危害,如《韩非子•难一》:“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但在远古那种生存环境中,人们的这种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火在这两件大事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字,小篆作。《说文》:“,柴祭天也。从火从。,古文字。祭天所以也。”“”字甲骨文作、、、等形,像木柴架在火上燃烧的样子,周围的点画象征四溅的火星;下面有的加“火”,有的不加“火”,这只是形体繁简的不同,构意上并没有多大差别。《尔雅•释天》:“祭天曰燔柴。”郭注:“既祭,积薪烧之。”邢疏:“祭天名燔柴。《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说的就是烧柴以祭天的仪式。《吕氏春秋•季冬纪》:“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高诱注:“燎者,积聚柴薪,置璧与牲于上而燎之,升其烟气。”燎祭就是将玉帛、牲畜置于燃烧的薪柴之上,用产生的烟气上达于天来祭天的仪式。这里的“燎”就是“”字。“”字形里本来是有“火”的,但由于字形的讹变,其中的“火”看不出来了,为了强调“”与火有关,人们就在“”的形体上又添加了一个“火”,这是汉字顽强地坚持表意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其实,在小篆形体中,“”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形,看不出木柴燃烧的形象了,许慎根据小篆字形所做的解释并不符合“”字的最初构造意图。
篇2
当然,对于“祭”字中的点到底代表着什么,还有些不同的看法。如有人认为,点代表的不是血,而是碎肉末。古代祭祀的时候,为了方便神灵的享用,人们事先要另外准备一些切碎的肉末,撒在大块的肉上,祭祀时祭祀者左手提着肉块或盛肉的器具,右手抓取上面的肉末慢慢抛撒,好让神灵前来享用。随着祭祀的进程,肉末越来越少,就好像神在一点一点地享用一样。这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殡葬时撒纸钱的仪式,左手持斗,右手从中抓取纸钱撒向空中,口中不停地祷告让亡灵前来拾取。《仪礼》说:“右手执肺,左手执本……绝末以祭。”这里的“本”应该是大块的祭品或盛祭品的器皿,“肺”应该是切碎的肺末,可以抓取,“绝末”就是把肉末一点一点地撒出去。从《仪礼》的这一记述来看,把“祭”字中的点解释作肉末,似乎也有一定的根据。还有人认为,“祭”左边的不是肉,而是盛酒器,手持酒器将酒倒出,以这种方式进行祭祀,点就代表从器皿里淌出的酒滴。不过,这种说法目前还找不出更多的证据。
“祭”字甲骨文还可写作、,字形中除了手、肉、血滴之外,下面增加了或,所增加的部分就是“示”字。其实,多数与祭祀或神灵有关的字,都会带上这样一个偏旁。《说文解字》:“示,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许慎对“示”字的解释,依据的是其小篆字形,他认为,上面的两横是“上”字,“上”代表天,下垂的三笔分别代表日月星,上天用日月星所形成的不同天象,映射人间的祸福,提示人们遵照行事;人们则通过天象观察自然的变化,了解神的旨意。这种根据小篆字形所得出的解释,无法与“示”的甲骨文字形相切合。“示”在甲骨文中有多种写法,按照叶玉森《说契》的说法,“乃最初之文。上从一,象天;从丨,意谓恍惚有神自天而下,乃以丨为象征。变作,下从一,象地,谓神自天下地也。又变作、,上从二,乃从一之讹。……更变作、,与小篆合。即许(慎)三垂日月星之说所由来,亦即近儒汉族崇拜三光之说所由推演。实则初民崇拜大自然,惟觉有神自天下降而已。‘示’本繁变之字,许君及近儒之说,并不免附会。”叶玉森批评了许慎的说解,但他自己的解释也同样有附会之嫌,把其中的“丨”解释作仿佛有神自天而降,确实显得过于玄虚。
将解释为神主的说法也很流行。神主大致相当于现在所供奉的神灵或祖先的牌位,古时候的神主多为一根竖立的木头,或者将几根秸秆捆在一起,外面涂上泥,以此作为神的依附,供人们祭祀供奉。但这种说法很难解释神主上面所加的一横究竟是什么含义,变成两横又是什么含义,酒或者血为什么能从神主上流淌下来,这些都还是疑问。相比较而言,我们更愿意相信另一种说法,即像祭坛, 像祭坛上摆放有祭品,、、则像酒或血从祭坛上流淌下来,或者是祭品的碎末从祭坛上撒落,这样解释似乎可以与“祭”字中的点相印证。
我们还可以通过“祝”字的甲骨文字形(见图1)来观察的形象。祝是祭祀时负责向神祷告的人,也指祭祀时的祷告词。其甲骨文字形正像一个人跪在地上,面向神坛向神祷告的样子。“祝”的这些字形中,有的祭坛上没有祭品,只是跪在神坛前作祷告状;有的则像伸开双手,在祭坛上摆放祭品之形;更有的就像前面所说的左手持盛肉的器具,右手抛撒肉末的样子(如第一行的第4、5个字形),这说明,认为“示”字中的点是肉末的说法,在字形中也可以找到根据;而第二行第1个字形中,“示”字的四点从祭坛的两侧直接下落,又确实像液体(血或者酒)向下流淌的形象。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当时祭祀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有的以血与肉祭,有的以酒与肉祭,有的则是“绝末以祭”,不同的造字者选取不同的方式作为字形的取像,于是便有了“示”和“祝”等字的不同写法。这种为同一个字选择不同取像的情况,在甲骨文中相当常见,如“牢”本指圈牲口的地方,有的圈牛,有的圈羊,有的圈马,于是“牢”字也就有了、、等不同的写法,这是因取像不同而给同一个字造出几个不同字形的典型例证。由此看来,关于“祭”字中的点究竟代表什么,正确答案很可能不止一个。
篇3
“兵”字在小篆中写作,上面的构件已经发生了讹变,象形性降低,已经难以看出斧头的形状了。隶变后作,上部定形为“斤”,小篆中下面表示两只手的构件简化成了,上的一横又和“斤”粘连在一起变成了“丘”。“兵”的本义是兵器,引申为持兵器的人,也就是士兵。旧社会对兵痞常贬称为“丘八”,正是因为隶楷之后,“兵”字的构形理据变得模糊,人们根据楷书“兵”字的写法而做出了错误拆分。《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个故事,说东晋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皇帝为苻坚)有一个大将叫慕容垂,此人是军事天才,据说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慕容垂有一次行军前梦见自己在赶路,走着走着没路了,突然看见路旁有孔子的坟墓,周围还围着八座坟,他醒后觉得很奇怪,就找占梦的人来解梦。占梦人说:“前方没有路,说明此路不通。孔子名丘,周围有八座坟,丘和八合起来是个‘兵’字,这条路一定有伏兵。”于是,慕容垂就改变了原定的行军路线,后来得知那条路上果然有伏兵。这个故事反映出那时人们已经将“兵”拆分为“丘八”了。
随着兵器的不断改进,用做兵器的斧头逐渐与用做生产工具的斧头分道扬镳,在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戚、我等新兵器。这三种兵器的形制与斧大致相同,但各有特点(见下图)。《说文段注》说:“,大斧也。”比斧略大,刃较圆,一般向两边张开,有时柄端还带有金属尖。《诗经》“干戈戚扬”,毛传“戚,斧也”。戚与相比,刃张开度小,略内敛;与斧相比,戚的边缘带有锯齿状槽沟,斧则边缘平滑。“我”与斧相比,特点是刃部呈锯齿状。、戚、我三者都是长柄的斧类兵器。甲骨文中这三个字都是象形字,古人在造字时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三种兵器的典型特征,“”字突出了圆刃,“戚”字突出了带沟槽的边缘,“我”字突出了锯齿形的刃部,从而将三种形制相似的兵器区别开了。到了金文中,三个字中像柄的部分均已经类化成表义构件“戈”(戈是古代常见的兵器,我们已在前面的文章中介绍过,不再赘述),“戚”字更是加上了声符“”(戚、古音相近),成了一个形声字,“”和“我”的象形性也有所减弱。后来,“”表示斧钺时添加了表义构件“金”,分化出“”字;“戚”的常用义已不再是武器名,而是被借去表示“亲戚”的意义;“我”的武器义则完全消失,被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古代斧钺既是兵器,也是用来执行斩首之刑的主要刑具,金文中有个族徽,像执钺刑人之形。《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攻克商王王宫后,用黄钺斩了纣王的头颅,悬于太白旗上。因此斧钺又是主掌生杀大权的权力的象征,常被帝王用作典礼和出行时的仪仗,是威严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王”字甲骨文作,也取象于斧钺,像一把平置的斧形。《司马法》中记载说,夏朝时执黑色的钺为仪仗,商朝用白色的戚为仪仗,周朝用黄金装饰的黄色钺为仪仗。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中,出土了两件大型青铜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她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巾帼英雄,曾多次率兵出征,这两件大钺正是她权威的象征。
矛和斧一样,也是较为原始的兵器。矛是一种用于直刺和扎挑的兵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用兽骨、竹片、尖形石块刺杀动物,后来加上柄,这大概就是矛的前身。“矛”在金文中作,作为构件参构别的字时也作,是一个象形字,像矛头与矛柄,中间的环是用来挂饰物的。矛上挂的饰物不仅有装饰作用,还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刺击时晃动的饰物可以干扰敌人视线;刺中敌人后,血会顺着矛尖流出,饰物可以防止血沿着矛柄流到抓握的位置。战国文字中“矛”作,字形中缠绕的条纹,突出地表现了矛身上的饰物。湖北包山二号楚墓中出土了三件刺矛,矛柄上依次缚扎着三束羽毛,每一束都环绕矛柄。《诗经》中有“二矛重英”的说法,“英”就是饰物,这句诗大意是说两支矛的柄上都有重叠的饰物。这些都能与此战国文字形体相印证。《说文》中还收了一个古字作,是在的基础上又添加了表义构件“戈”。矛的柄很长,出土实物中最长的有四米多,可见小说中常说的“丈八蛇矛”并非太夸张。
两军对阵,还常用到远程型武器。远程型武器中弓和矢配合使用,“弓”、“矢”甲骨文分别作、,均为象形字。射箭的“射”字甲骨文作,像箭在弦上之形,这些均为人们所熟知,此处从略。除此之外,炮也是一种重要的远程型攻击武器。象棋走法口诀中说“车走直路炮翻山”,正是对炮攻击特点的形象描述。象棋中红黑两方之炮一作“炮”,一作“”,二者原本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字义符为“石”,肯定与石有关。《集韵》:“,机石也。”“机石”就是一种发射石块的装置,也叫做“抛石机”,炮弹就是石块,借助杠杆的力量把石块抛到敌人的阵地,达到伤敌的目的,或用来攻城。相传战国时期范蠡著有一部《范蠡兵法》,汉代贾逵曾引用其中的文字:“为机发行二百步,飞石重十二斤。”这是以机发石的较早记录,“”大概就来源于此。《说文》“”字下说:“建大木,置石其上,发其机以追敌。”虽然《说文》中这段话不是解释“”的,但据此可以肯定的是,发石装置的出现最晚也在汉代。“炮”字义符为“火”,本义是一种烹调的方法。《说文》:“炮,毛炙肉也。”就是把带毛的肉用泥裹住之后放到火上烤,类似于今天叫花鸡的做法。火药发明以后,逐渐被应用到军事方面,大约南宋时期出现了火炮。《宋史•兵志》说:“又造突火枪,以钜竹为筒,内安子窠,如烧放,焰绝然后子窠发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这种“突火枪”的功能和抛石机相似,但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使用了火药,不再单纯用杠杆原理发射炮弹了。“炮”字从“火”,于是又成了记录“火炮”一词的本字,与表示烹调方法的“炮”同字异词。古代的火炮也多发射石弹,所以用“”字来记录“火炮”依然有理据,但现代武器中炮弹均已为金属所制,此时再用“”字来记录,就没有理据可言了,因此“”也就彻底被“炮”字所取代。从“”到“炮”的转变,正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文字的影响。
篇4
“炮”字从火包声,其中的部件“包”除了表示声音之外,还表示包裹的意义。郑玄注所说的“裹烧之”,也就是用泥巴包裹着食物放进火里去烧,这种加工食物的方式类似于现在的“叫花鸡”。关于叫花鸡,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古时候江苏常熟有个叫花子,有一天很幸运讨了一只鸡,他怕其他叫花子知道后也来分享,便将整只鸡连毛用荷叶包裹好,再涂上泥巴伪装起来,胡乱塞入火堆里烧烤,等别的叫花子都不在时,他赶忙把鸡从火堆里扒出来,砸掉裹在外面的泥巴,惊喜地发现,烧鸡不仅通体金黄,而且味道异常香酥可口,还略带泥土的芬芳,堪称是鸡中极品,从此以后叫花鸡便成了一道名菜。其实,从“炮”的字形以及《礼记》的记载来看,类似叫花鸡的做法早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
“燔”和“炙”都是放在火上烤,在古代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二者到底有什么不同了。从“炙”的字形看,下面是火,上面是“肉”的变形,再结合郑玄所说的“贯之火上”,可以想见“炙”是将肉串起来,架在火上去烤,估计与现在的烤羊肉串的做法差不多吧。不过,当时的烤法不一定非得把肉切成小块,有时候也会把整只动物串起来架在火上烤。
“烹”是一种用水煮食物的熟食方法。“烹”字原来没有下面的部件,只写作“亨”。甲骨文作,金文作,《说文》作。《说文》所解释的本义是把煮熟的食物献给鬼神。其字形有的说是像宗庙之形,有的说像盛满食物、上面加了盖儿的器具之形,但各种说法都离不开宗庙祭祀,由此可见熟食与祭祀之间的密切关系。“古之大事,惟祀与戎”,祭祀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当时烹饪的目的也不像今天这么单纯,当时除了要供给人们膳食之外,还有很大比重用作鬼神的祭品。《周礼》有一种官职叫“亨人”,其职责就是在准备祭祀品的时候,专门负责煮食物的火候大小和锅中水量的多少。《周礼》还有两种和做饭有关的职务,叫“内饔”和“外饔”,“饔”的意思就是熟食,内饔是掌管宫廷内王、后和世子们的伙食的,外饔是掌管祭祀时设计祭品的。亨人在内饔、外饔的工作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水量和火候的把握,是食物煮得好坏的关键。
其实,不仅“烹”、“亨”二字本来是一个字,还有享受的“享”,也与“烹”字属于同一字源。“烹”、“亨”、“享”在古文字中同为一形,后来才逐渐分化成三个意义密切相关的字。煮食物的意义专用“烹”字;食物煮熟之后,供奉给宗庙上的鬼神,诚意通达于鬼神,这样便有了亨通的“亨”字;鬼神闻到祭品的馨香,便欣然享用,这样便有了“享”字。直到现在,方言里还有将这几个字混用的情况,如湖南北部某些地区称用铁锅烧水为“享水”,用瓦罐把茶烧开叫“享茶”。通过“烹”、“享”、“亨”几个字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烹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饮食与祭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烹”字现在与“饪”连用,构成一个双音词,泛指做饭做菜。但在古代汉语中“烹”、“饪”很少连用,即使连用,也是各有各的意思。烹是煮的意思,而饪则表示把食物煮得熟透。《说文》:“饪,大熟也。从食,壬声。”《论语•乡党》:“失饪不食。”何晏注释说:失饪,“失生熟之节也”。也就是说,煮食物必须熟度刚好,既不能半生不熟,也不能过于熟烂,这样才符合礼仪的要求。特别是祭祀的时候,食物的生熟度如果不符合标准,是绝对不能用作祭品的,否则就是对鬼神的不敬。“烹”“饪”二字连用,最早见于《周易》:“鼎,象也,以木翼火,烹饪也。”这里的“烹饪”虽然连用,但还没有成为一个双音词,其中“烹”表示煮的过程,“饪”表示煮的结果。“烹”、“饪”相连,构成了食物原料由生变熟的一个完整的加工过程,反映了古代由烤炙的熟食法发展到烹煮的熟食法,再到讲究食物生熟度的进程。
“烹饪”是对食物进行加工处理的过程,“饮食”则是对“烹饪”的成果的享用。“食”字很早就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意义,既可以指吃的动作,又可以指吃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吃的对象都可以叫食,最初食是专指主食,“食”泛指一切食物是后来的事。“食”字甲骨文作“”,一般认为像一个盛食物的器具,上面像器具的盖子,下面是盛食物的圆形器具。这种圆形的盛食器应该就是“簋”,因为其形象与“簋”的字形非常接近。“簋”是古人盛黍、稷、稻、粮等主食的器皿,圆形,上面有盖子,以便使食物保温。《说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这里以“方器”释簋是错误的,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凡自铭为“簋”的器物大多为圆形,因此应释为圆器。郑玄注《周礼•地官•舍人》说:“方曰,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具体来说,簋的形状很像大碗,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或木制,或陶制,或以青铜铸造。商代簋多无盖,无耳或两耳。西周和春秋初期簋的形制有较大发展,常带盖,有两耳或四耳,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四足者。到春秋中晚期,簋作为食器已经不很流行,只是在传统的礼器体制中尚有发现,但形制有了较大变化。“簋”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或,字形的左半边像簋中盛满饭食,右半边像手持匕匙、从簋中取食之形。《韩非子•十过》:“昔者尧有天下,饭于土簋,饮于土。”可见簋是古人吃饭的主要用具。
对于“食”字的构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下面像盛食物的器具,而上面的则像倒着的口,表示人张开大嘴趴在盛食器上来进食。这种说法似乎不太符合实际,因为“簋”这种盛食器有时候直径可达几尺,需要借助勺、匙之类的器具辅助,直接用嘴趴到簋上进食是不方便的。
篇5
金文中还有一个“车”字(见图2),与图1的构件基本相同,但取象角度稍有区别,其字形的上部朝右侧弯曲,这体现了车的特殊形制。《周礼•考工记》:“凡揉欲其孙而无弧深。”通过这一描述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车并不完全是直形的。车是一根用火煨烤而成的整木,压在车舆下面的部分与舆底平行,探出车舆底座的部分呈浅弧形,逐渐上扬,至顶端又趋于水平,整个外形就像一个左右拉伸开的“Z”字形。制作车时,要让它的弯曲处自然顺畅,不要有太深的弧度。图2的字形正是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巧妙地反映了车的微曲上扬的姿态。
车上最重要的部件莫过于车轮了。据说古代的圣人从转动的飞蓬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轮子。但单纯的轮子只能转动,而不能载物,所以圣人又制造了车厢,安置在轮子上,于是便有了车(《后汉书•舆服志》)。且不论“观蓬为轮”说是否可信,但车轮的发明,一定与古人对圆形物体便于旋转的生活经验有关。“轮”字是从车、仑声的形声字,其声符“仑”同时又兼表意义。汉代的《释名》是专门解释事物名称来源的书,该书解释“轮”字说:“轮,纶也。言弥纶周匝也。”之所以可以用纺车的线纶来解释车轮,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一方面它们的功能都必须通过旋转而获得,另一方面线圈的缠绕和车轮辐条的分布都必须很有条理。《说文段注》说:“三十辐两两相当而不迤,故曰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制作车轮的技术要求有十条之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用悬线察看相对应的辐条是否笔直,三十根辐条要两两相对而不倾斜,才能达到要求。可见,旋转和有条理,是车轮得名的两个重要依据,而这两层含义都是由“轮”的声符“仑”表达的。《说文》:“仑,理也。”《康熙字典》:“仑,叙也。”“仑”的繁体字作“”,从从册,是个会意字。,音jí,义同“集”。册就是把用竹简编制的简册卷积起来,所以“仑”既有条理的意思,又有旋转的意思。还有几个以“仑”为声符的字也与“仑”的这些意义有关。如“伦”是人的不可混淆的辈份、长幼次序,“论”是有条理有层次的语言,“沦”是有条理的水的波纹,等等。这些字都可以和“轮”“纶”“仑”构成同源关系。了解了“轮”字的声符“仑”所提示的意义,我们对车轮名源的理解也就更深刻了。
车的另一个重要部件是车轴。《说文段注》:“轴,所以持轮者也。从车,由声。”“轴”是一个形声字,其声符“由”同时也兼表意义。“由”是从的意思,可以表示一件东西从什么地方出来。“轴”与同声符的“抽”、“袖”是一组同源字,它们都含有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意思。“抽”就是把一件东西从别的东西中拉出来;而衣袖的“袖”得名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们是筒状的,两臂可由其中抽出。同样,车轴的得名,也是因为它可以从轮毂中抽出来。《释名》说:“轴,抽也。入毂中可抽出也。”“轴”的这一意义特征,与古人对车轴的保养意识有直接的关系。
古时候的车轴多为木制的,车轴伸出车轮外面的两端很容易被撞坏,为了保护轴头,人们用金属制成两个圆筒状的套,套在两端的轴头上,这种零件叫軎(音wèi)。《说文》:“軎,车轴(即“端”)也。从车,象形。”字形中的“口”就像套在轴头的軎的形状。杨树达说:“(此字)当横看做‘’形乃得之。车轴两端皆当有軎,此省去一端也。”軎上和车轴的两端有对穿的孔,将两轮装在车轴上之后,用一个插销从孔中穿过去,以防止车轮和軎从车轴上滑脱,这个插销就是前面所说的辖。辖虽然是一个小零件,但却是行车的关键;没有车辖,车轮就会脱落。《淮南子•人间训》:“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汉书•陈遵传》:“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由此可见车辖作用之重要。由于车轴肩负着承载整个车身及货物的任务,容易断裂,所以古人很注意保护车轴,不用的时候便将车辖取下,将车轮卸下,以减轻车轴的负担,需要用车时再重新装上。而卸下车轮,就相当于把车轴从轮中抽出,“轴”字的命名就包含有这层意思。
《说文》还收了一个“车”字的籀文形体,从两车两戈。《说文段注》说:“从戈者,车所建之兵,莫先于戈也。从重车者,象兵车联缀也。重车则重戈矣。”意思是说,车上所配备的兵器,最早的就是戈。所以“车”字中可以增添部件“戈”。类似的形体在金文中也能见到,如图3所示,其中的构件就是“戈”的象形字。而配备有戈的车无疑是古代的战车。河南淮阳马鞍冢出土的古代战车,车厢上就设有专门插戈的圆筒,正好与此字形相印证。
古代的战车多用马驾。驾马的数量有二、三、四、六不等。《说文》中“骈”、“骖”、“驷”分别表示驾二马、三马、四马,这几个字的意义都跟它们的声符有关。“骈”字从“并”得声,含有“两个并列”的意义特征。“骖”字从“参”得声,《广雅》:“参,三也。”因而“骖”就有了“三”的特征。“驷”字从“四”得声,《说文》:“驷,一乘也,从马四声。”由四匹马拉的车称为一乘。《论语》中说:“驷不及舌。”由四匹健壮的马所拉的车,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但它还是赶不上舌头的速度,这话是告诫我们说出的话就难以收回了,所以要出言慎重。成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源于此。而驾六匹马的是级别最高的车,只有天子才能使用,一般人是不敢僭越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千乘之国”便是大国,“万乘之国”要算是超级大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