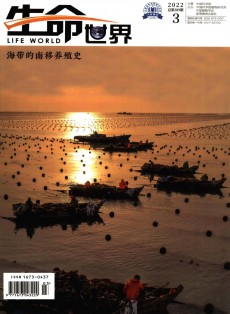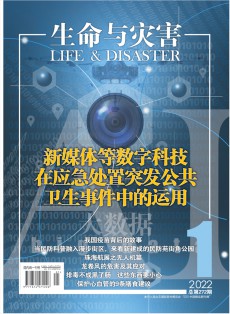生命的根源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7:33:01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生命的根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从远古至今,中国艺术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在这艺术发展的岁月长河中,上一眼望去,似乎不见源头;下一眼望去,好像永无尽头。如若对中国的艺术思想进行探源,那么老庄“虚静说”的提出和发展,则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其认为“虚静”是自然的本质,是生命的本质,亦是艺术的本质,从而“虚静”成为中国传统艺术创作所需要的一种必要的态度。正是无数的中国艺术家通过对这种态度的内心关照,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从而使艺术回归到生命和自然中的本质状态,从而在艺术长河中激起了无尽美丽晶莹的浪花。
一、老庄“虚静”学说的产生
早在先秦时期,老子提出了道家修养的主旨为“致虚极,守静笃”。 他认为世间一切原本都是空虚而宁静的,万物的生命都是由“无”到“有”,由“有”再到“无”,最后总会回复到根源,而根源则是最“虚静的”,从而认为“虚静是生命的本质”。因此人们要追寻万物的本质,必须达到“无知、无欲、无为、无事、无我”的状态,回其最原始的“虚静”状态。老子把“虚静”作为一种人生态度还提出了“涤除玄览”观点,他认为只有排除一切杂念,让心灵虚空,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澄明,才能以更明了的目光去观察大千世界。
此后,庄子在吸收老子“虚静”思想的基础上,对老子有关“虚静”的论述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要达到“致虚守静”的境界必须做到“心斋”与“坐忘”,庄子认为“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在庄子看来人要达到“虚静”的境界必须忘了世间万物,忘了自己的存在,远离世俗切利害关系,不受私欲杂念干扰,以无知、无欲、无求的心态去感受世间的“道”达到物我同一达到“物化”的状态,才能真正的体会自然,认识自然,创作出真正与自然相通的艺术作品。
这为后来的艺术创作者切入艺术体验的境界找到了理论渊源,也对后人的艺术创造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虚静”说在艺术领域的引入
老庄的虚静思想,最早只是作为一种人生态度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应用到艺术领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虚静”说被引入了审美的视野,进而渗透到艺术创作实践中,这时“虚静”不仅仅成为创作之前所要必备的心理状态,而且在艺术创作的各个环节中都渗透着“虚静”的思想。
最早把“虚静”说引入艺术领域的是西晋文学理论批评家陆机,他在《文赋》中提到“伫中区以玄览”,强调一个好的作品要对外界事物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观察,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要不受外物干扰、思虑清明、心神专一,他所强调的是在创作之前主体必须具备“虚静”的心境,不受外物和杂念的束缚与干扰,内心清明,心神专一,这样才能实现全面的审美观照。所以,他认为“虚静” 是作者进行创作所必不可少的心态。但是这时陆机没有明确使用“虚静”这个概念,其“虚静说”还停留在思想叙述的阶段,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直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写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这是才将“虚静”的概念引入了文学理论范畴,而且还对“虚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将这一说法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虚静”是创造者在创造过程中所达到的最佳创作状态,能使创作主体虚静凝神,排除内心的杂念和欲求,以及外界的一切干扰,它使主体从世俗中解脱出来,进入审美观照的境界,进而创造出与自然相通的艺术作品。
随着玄学的兴起和发展,老庄的“虚静说”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南朝山水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 “澄怀”是对体验者审美心胸的要求,这受庄子“心斋”说的影响要求主体澄清胸怀,涤除俗念;“味象”之“味”,即体味、品味、玩味,也即体验;“象”指客体物象、审美对象。所谓“澄怀味象”,就是审美主体以清澄纯净、无物无欲的情怀,品味、体验、感悟审美对象内部深层的情趣意蕴、生命精神。“澄怀味象”的美学主张,将“虚静说”直接引入到艺术创作的审美领域,他把创作主体所必须具备的审美心胸和作为客体的自然之美联系起来,使得“虚静”理论的体系更加清晰分明。
篇2
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是强大的生命力的根源。
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前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理论最深刻、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心灵的根源
人做事要经过大脑,大脑所思考后得到结果,经过实施而变成现实,但是什么是心灵的根源?
树的根源是种子,经过人类对他的培养,有小小一点点慢慢成长,慢慢长大,与先前的形体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鸟的根源是蛋,这是一个奇妙的蚋变 ,都知道蛋中的生命是由液体而逐渐成形,由一个无生命体变成一个有思想、有生命的生物,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也是鸟的根源。鱼儿的根源是卵,有透明、松软的圆球形成的,而变成海洋中的一员,任谁也不明白,一个看似毫无生机的东西,却是能够成为有思想、有生命的生物,这是一个根源问题,心灵也有根源,是什么,让人有意识,那是心灵中的一丝丝善意,人之初,性本善,既然人刚出生是善良的,那么心灵的根源就是洁净的,然而经过岁月的蹉跎,人的的心灵在一点点改变,儿时的善良、美好、天真,都随之灰飞烟灭,心灵的根源就这样一点点被侵蚀,欲望、贪念占据了人的心灵、大脑。根源被污染,一双无形的大手在背后操控着,心灵的根源不知去向,也许她死了。
根源就这样抛弃了我们,如果说这是真的,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篇4
生命精神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生命关怀也被认为是贯穿中国传统哲学之始终的根本意蕴。中国传统文化生成和发展的千百年来,诸子百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生命问题,但最集中、最突出地弘扬古老文化传统中之生命精神的却是道家。道家哲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生命哲学。要走进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殿堂,道家的生命哲学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
一、道家哲学中生命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道家生命价值观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生命观念,理论上有其原创性,但并不排除其资料上的继承性。从前人那里继承的历史资料便构成了道家生命价值观的理论渊源。
(一) 上古神话中的生命意志
神话被誉为是哲学的史前史,对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国上古神话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生命意志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创生型、抗争型、转生型、不死型四种类型。“开天辟地”是创生型神话的典型,以垂死时将身躯化作宇宙万物的辉煌成就来化解生命有限性的遗憾;“夸父追日”是抗争型神话的典型,以夸父追逐烈日找水源的行为来表现对威胁人类生命的自然条件的抗争;“鲧复生禹”是转生型神话的突出代表,通过讲述鲧因治水死后以顽强的生命意志孕育出最终征服洪水的大禹的故事来表明古人对群体生命无限性的追求;“精卫填海”则是不死型神话的代表,通过讲述炎帝侄女淹死后化作精卫鸟衔石意欲填平吞噬她生命的东海的故事来表明古人生命意志的顽强及追求生命目标的艰难。这些上古神话都在某种程度上使老子产生了一定的神话思维和复古情结,从而成为道家生命价值观的理论渊源之一。
(二) 原始宗教中的生命崇拜
原始先民在探讨自然与人生奥秘的过程中先后产生了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最原始的,但最能直接反映原始先民生命意识的则是母神崇拜。母神崇拜是母系社会女性重要作用的反映,“母”之所以值得被崇拜,是因为她有孕育生命的功能,实际上就是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崇拜,本质上也是一种生命崇拜。道家文化是母系氏族文化的衍生物,《老子》中就有非常明显的崇母意识,将道生万物比拟为母生子,以“母”称“道”,以“道”创“生”。老子在确定了“道”是万物之母的主体地位之后又提出了“贵食母”的价值取向,主张“得其母”、“守其母”。老子的崇母意识所反映的同样是一种生命崇拜意识,是对原始宗教中母神崇拜意识的继承与提升。
(三) 古代典籍中的生命关怀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理论源头,其浓郁的生命情怀对道家的生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周易》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认为“阴阳合而万物生”;另一方面,《周易》将宇宙间最高尚的品德归结为创造生命,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与儒家传承《周易》的群体生命意识不用,道家侧重传承的是《周易》的个体生命意识。从老子创立的“长生”之道,到庄子提出的“达生”之方,到杨朱倡导的“贵生”主张,再到黄老道家整理的“养生”之术,无一不是个体生命意识张扬的体现。另一层面,道家诸子对《周易》生命思想的传承也具有一定的逻辑渐进性。从老子到庄子再到黄老道家生命思想的传承及演变,便是从生命存在意识到生命超越意识再到落实生命超越意识的渐进发展过程。
二、道家哲学中生命价值观的主要内涵
(一) 生命的根源――道
“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最高范畴,亦被道家诸子视为终极性的存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第一章便提出了“道”是世间万物产生的总根源,从时间上确定了“道”的优先性。同时《老子》第二十五章还有“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言论,认为“道”还是统领和支配天地万物的总规律和总法则。庄子理性继承了老子关于“道”为生命本源的观点,在《大宗师》中对“道”做了如是集中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认为“道”虽然无形无像,却具有实在性,是比天地更为古老的原始存在,是化生万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可见,道家生命哲学是用“道”来解释生命的根源。
(二) 生命的价值――重人贵生
篇5
引言
学生普遍认为句子The teacher is boring. 是错的,因为他们学到的语法规定:-ed与人有关,修饰人;-ing与事有关,修饰物。这个句子主语“老师”是人故不能跟-ing形式的形容词搭配使用,正确的应为The teacher is bored。事实上,这两个句子既合乎传统语法规定,在语义上也是正确的,只是把英语作为外语学习的我们无法像英语母语者那样体会二者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别。有类似区别的-ing和-ed分词形容词词对还有很多。这些词大都由表情感的及物动词转化而来,并在长期使用中当形容词看待,姑且称其为情感形容词对。本文尝试利用情感产生的根源或原因与情感体验者功能角色阐释情感形容词词对在使用中的语用差异,担任同一语法成分时的属性差别,以期从新的视角准确理解、使用这些词对。
句子功能观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句子不仅仅是由主、谓、宾等语法成分构成的语言模块,它还是对情景或事件的描述;动词除担任谓语成分还表征某动作或状态类型;动作过程期待不同的参与者;参与者又进一步区分为施事和受事;作为参与者的实体在动作或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比如句子A thief stole my pen.
在功能语法框架内,这个句子不只是个主谓宾结构,它还是一个偷窃事件的表征。这个事件的中心是“偷窃” 动作,其中涉及两个角色:施事角色“小偷”(动作执行者)和受事角色(受动作影响的事)“我的笔”。这个施事角色是有生命的实体人,受事是无生命的非人实体笔。这个施事人可以看作动作的根源或原因——发出或实施这个动作。作为动作根源或原因的施事实体通过发出的动作影响非人受事实体,施事和受事两个角色从而产生关联。这个动作产生根源或原因及施事受事之间因动作而关联的思路可以用来探讨和理解英语-ing和-ed情感形容词词对所表达的感情问题。本文尝试区分情感源头或原因,情感的体验者角色来解释-ing和-ed情感形容词对的使用。
情感形容词词对
1.词对聚类的开放性
英语中的情感形容词词对是由表达情感、情绪的动词转化而来。情感动词指能够激发人产生某种情感或感觉的及物动词,描述人们内心世界喜怒哀乐等情绪状态及感情变化,隶属于心理范畴,有使役特征。学者从不同视角采用不同的术语,对情感范畴进行了广泛研究。龙献平收集了四十个常用情感动词并将其翻译为“使人……”,“令人……”,如 bore 使人烦闷;tire 使人疲倦。龙献平仅从动词切入,视-ing、-ed为相应动词的分词变形,未将这类词归入形容词词类,这一点跟《英语形容词用法词典》、《朗文英语语法》、《通用英语形容词、数词教程之四》、《张道真英语语法》等语法书相左。事实上,这些分词已经在长期使用中以形容词形式固定下来,具有形容词的属性特征,有些分词还正经历着语言实践的考验,随着使用频率的变化逐渐被人们接受,从而具有形容词的特质。换言之,-ing和-ed情感形容词对聚类是开放的。
2.属性及句法功能
词对具有动态的、客观的、绝对义属性。与其他形容词一样担任句子表语、定语成分。但传统语法及相关研究视-ing只能修饰事、物等没有生命的物体,-ed只修饰人。个别修饰人的-ing只是例外,如frightening face,脸不像有生命的人、动物那样具有产生这种情感的生理能力,这样的用法是不可接受的,只是这类词的用法例外。而这样的例外在Yule的情感划分中却是常态化的。
Yule认为我们谈论情感除情感的生理过程外,还可以讨论其来源或谁正在体验着这种情感。情感的来源在此不指情感产生的生理过程,只是描述情感来自于哪里,它既可以来源于有生命的人、动物,也可以来源于无生命特征的事物。这样,就不存在被修饰语的人与物的区分。也就是说,-ing修饰人说明情感来自于该人,修饰物说明情感来源于该物;而-ed修饰人时说明此人正体验着这种情感。比如前文提到的a boring teacher和a bored teacher。在前者中,“烦”这种情感来自于老师,他是个让听课的学生感到无聊的老师。而后者的老师正体验着“烦”这种情感,是个正“烦着”的老师。从情感来源角度解释-ing修饰名词不仅与使役的解释是一致的,而且操作起来更加方便,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学生无需区分被修饰词是人还是物,只需弄明白自己表达的目的:是相关感情的来源、还是表达谁在体验这种情感。若谈情感来源即选用-ing形容词,若谈情感的体验者则用-ed。比如一位总能让学生感兴趣的老师就是an interesting teacher;而an interested teacher却是正对某事感兴趣的老师。前文提到的a frightening face则是让人看了就害怕的脸,“害怕”这种情感来源于这张脸,或者该脸指代的人,体验“害怕”情感是别人,非脸指代的那个人。根据Yule对情感的划分,我们眼中的例外在英语母语世界里是正常的,只是语义上的细微差别不容易被外语学习者理解而已。
情感形容词做定语与名词搭配时,被修饰的名词可根据形容词的特性分为:产生这种情感的人、事、物和体验着这种情感的人、事、物两类。-ed形容词做表语时可以跟介词to、at、by sb.或sth.搭配;不定式短语搭配使用;还可与表示身心感受的动词feel、become搭配使用。
结 语
作为语言工作者,英语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更加积极地向学生讲授情感形容词词对的语用差异,使学生真正理解其使用规则,最终能准确适用这些词对。
参考文献:
[1]Yule, George. How to Teacher English Grammar[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