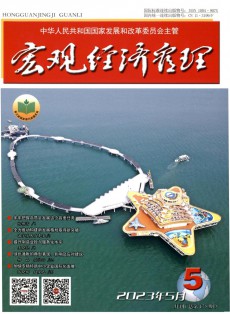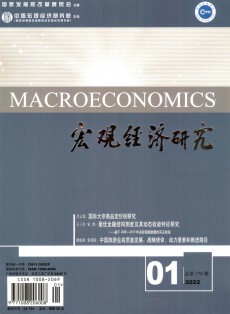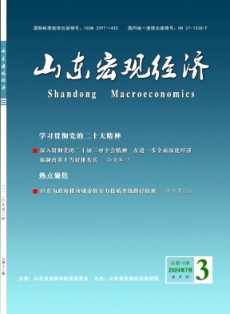宏观经济波动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7:33:12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宏观经济波动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关键词:
信贷配给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它使得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信贷配给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加速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不断改变,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要求越来越严格,监管部门要平衡信贷市场的整体利益,所以,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作用更为重要。
一、信贷配给的内涵
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贷款时,不仅依靠利息的高低进行贷款,利息达到一定的标准就给融资企业贷款,而是还要根据融资企业具体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贷风险的行为进行准确判断,确保信贷风险在一定范围内的情况下才将资金贷给融资企业。也就是说,信贷配给是指商业银行通过对贷款利息和融资企业的信贷风险的判断,不完全依据利息率机制,从而决定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进而实现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重要的一点内容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少于企业要求所需的贷款金额。
二、非对称信息与信贷配给的形成
(一)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商业银行在给融资企业借贷的过程中,融资企业对自己的内部实际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和实力以及真正质量就不了解了,这就造成商业银行信贷配给的非对称信息的形成,这种非对称信息主要分为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和事后的非对称信息两种,事前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借贷投资项目未来收益的具体相关信息,融资企业投资的未来收益情况取决于融资企业自身的具体情况、企业的自身实力、投资类型、投资风险程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都是融资企业自己所掌握的,商业银行能真正了解到的具体情况非常之少。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是指融资企业达到融资的目的之后,违反与商业银行的融资约定,擅自改变投资方向和项目,改变资金的用途,对投资的收益实际情况有所隐瞒,对偿付义务的相关信息熟视无睹,严重损害了商业银行的切身利益,这些情况都属于融资企业的“逆向选择”行为。其实,商业银行可以根据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做出让融资企业还款的具体方案,但是另一方面,融资企业的还款概率和预期收益商业银行都属于其机密信息,这些信息商业银行都无从获取,从而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最后导致,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之间,还款概率低于平均水平,预期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高于平均水平的不良现象,这种现象对商业银行的收益非常不公平,融资企业在很大程度上都占有优势,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就减少对融资企业的贷款,甚至不贷款和融资企业,造成了信贷市场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又提升了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形成恶性循环。
(二)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行为是在事后的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发生的,具体有三种表现。其一是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之后,企业就拿资金去投资风险高、成功率小的投资项目,但是投资一旦成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而投资一旦失败,从银行贷款的资金就很难还上,从而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其二就是融资企业有足够的资金偿还商业银行的贷款,但是在权衡还款与不还款的相对利益下,融资企业选择获取更大利益的不还款的行为,也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行为。还有就是融资企业从商业银行贷款成功后,为了保证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采取消极的工作态度进行投资工作,从而严重造成了融资资金的损失,从而导致的“道德风险”行为。融资企业由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合发展的鼠目寸光,导致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从而对信贷配给进行调整,采取少贷款或者干脆不贷款给融资企业的策略,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萧条,信贷配给情况不容乐观,宏观经济衰退,而且商业银行给融资企业借贷的利息率一度提高,进一步导致融资企业“道德风险”行为的发生。
三、信贷配给作用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理
宏观经济发生波动变动时会影响商业银行成本,而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波动。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所引起的宏观经济变动当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时,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就会随之上升,这样影响到银行本身本金的获得,因为商业银行的前期利润直接决定着其本金获得的情况,所以宏观经济的衰退会导致商业银行的本金获得。商业银行为了保全自己的利益,就会对信贷配给做出适当的调整,但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借贷风险有时是银行自己无法承担的,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银行破产,走向灭亡。而当宏观经济处于繁荣期时,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性就会相对降低,资本充裕,从而银行之间互相挤兑的情况也会相对减少。
(二)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的变化宏观经济衰退时,促进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会降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商业银行与融资企业的关系发生了大转折,一般情况下企业融资借贷是为了更多的投资,拓展企业业务,但是这种特殊时期,企业向银行借贷完全是为了生存,为了保全自己,这种情况下,企业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导致信贷配给形成非常严重的不对称性,进而促使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程度大大提高,贷款申请人的实力下降,从第带来资本运行风险。
(三)借贷配给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借贷配给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加速器的作用。宏观经济一旦出现衰退的现象,对企业的投资造成严重的阻碍作用,企业的发展和投资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中,从而影响了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宏观经济衰退的进程。
四、浅析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动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的实力和质量都有所下降,投资能力不容乐观,从而造成融资企业与商业银行的借贷违约情况发生率升高,导致银行借贷风险提高,预期利润得到的本金回收下降,所以,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会降低,严重到一定情况时商业银行无法承担起贷款风险,资金无法流转,银行间的挤兑现象严重,甚至导致商业银行破产走向灭亡,从而影响金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商业银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采取策略,相关的监管部门也会提高对商业银行资金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为了保全大局,避免金融秩序紊乱,损害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
(二)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商业银行贷款环境恶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融资企业的贷款的“道德风险”行为增多。其二是融资企业和商业银行的非对称信息,由于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多,多融资企业的贷款风险和预期收益信息都无法掌握,导致商业银行和融资企业在借贷配给上的非对称信息。其三是,贷款申请人的质量下降,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体制的变化,导致没有实力而喜欢高风险投资的人不断增加,从而使得商业银行的借贷风险提高。这样当宏观经济衰退时,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相比,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其自有资本高于临界水平,从而成功的避免宏观经济衰退带来的风险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借着非对称信息的空档增加对商业银行的贷款申请,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也就是说,宏观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有实力的融资企业会减少贷款申请,而没有实力的融资企业则增加贷款申请。所以,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升高,从而恶化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而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贷款环境会相对优化,借贷风险降低,贷款金额就会相对提高。
(三)融资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融资企业自身就是一个商业银行,需要融资时,融资企业可以给自己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提供信贷。宏观经济衰退时,融资企业经营情况恶化,企业向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信贷也会减少所以,企业要减少在各个方面的投资行为所以说,其实融资企业的可得性是一种扩散效应。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要减少自己的投资项目,缩小投资范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对企业正常运行进行恢复,并且减少了相关产品的供应,导致与之合作的企业的正常运行受到阻碍,从而造成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进一步恶化了宏观经济的衰退,从而导致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所以说,宏观经济与融资企业信贷可得性相互影响,通过扩散效应造成恶性循环的现象。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稳定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变化情况。我国宏观经济衰退时,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升高,预期利润下降,融资企业贷款环境恶化,而且商业银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采取一定的措施调整信贷配给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自发抑制宏观经济的衰退程度。我们一定要重视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认真分析信贷配给的特征以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原理,以掌握商业银行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机理。从而在宏观经济的变动波动过程中,有效利用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行为,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进一步促进我国信贷市场的有力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J].商业经济,2014(24)
篇2
二、测度信用价差的GZ指数的构建方法
Gilchrist(2009)提出了测度信用价差的自下向上的方法,并用该方法构建了测度信用价差的GZ指数。其具体的构建方法如下所述:假设在时期t由企业i发行的公司债券k所承诺的现金流序列为(C(s):s=1,2,…,S),这里的现金流包括了按期付息与到期时的本金偿付。那么该债券价格可描述为:Pit[k]=ΣSs=1C(s)D(ts)(1)此处的D(t)=e-rtt为在时刻t的折现函数。为了计算与之相对应的无风险债券价格Pft[k],我们利用时刻t连续复利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对现金流序列(C(s):s=1,2,…,S)进行贴现。按此方法所得的无风险债券价格Pft[k]将被用来计算假定国债的收益率yft[k],该国债产生的现金流序列同样被假定为(C(s):s=1,2,…,S)。用yit[k]表示企业债券k的收益率,那么信用价差则可表示为Sit[k]=yit[k]-yft[k]。通常使用的计算信用价差的方法为将企业债券收益率减去与该企业债券到期日相同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上的收益率而得到的,而本文所采用的度量信用价差的方法与通常的方法相比将大大减少信用价差的计算偏误。按上述方法,我们将得到微观层面各个时期各种债券的信用价差。将微观层面的信用价差进行简单的综合,就可得到各个时期的信用价差指数。具体计算方法可表示为:此处的Nt指时期t的样本观测数,式(2)即为各时期度量信用价差的GZ指数。从式(2)可以看出GZ信用价差指数实际上是各微观个体债券的信用价差的简单算术平均值。
三、数据描述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在计算信用价差指数的时候,我们利用了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的企业债收益率数据、国债收益率数据以及国债的收益率曲线数据。由于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的利率期限结构数据最早开始于2006年3月,因此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为2006年3月至2011年10月,数据频率为月。在利用上述原始数据计算GZ信用价差指数的时候,为了保证计算结果不受极端观测值的影响,我们将个体信用价差低于5个基点以及高于3000个基点的观测值进行了删除处理。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宏观经济变量则主要包括产出、出口、投资、消费与通货膨胀。其中的产出用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来代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出口用出口总额的当月同比增速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投资则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当月同比增速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消费则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货膨胀则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当月同比增速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为与上述信用价差指数相对应,本文对宏观经济变量所选取的样本区间也为2006年3月至2011年10月。
(二)实证分析
篇3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回顾与述评
家庭借贷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经历了家庭债务的快速增长过程。与此同时,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刺激消费需求政策的不断出台,我国家庭债务的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均发生了巨大变化。1997年,我国家庭债务规模是172亿元,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仅为2.17%,截至2011年底,家庭债务规模达到了8.8万亿元,家庭债务占GDP的比率则上升到了22.3%。中国家庭债务总额上升的同时伴随宏观经济变量不断波动,那么中国家庭债务快速增长对居民消费、房价与公共债务等宏观经济变量有什么影响,反过来说,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如何影响中国家庭债务规模,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本文的重点内容。
国内外学者对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问题已做了较多的经验研究。Carmen(2004)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西班牙的消费与借贷的关系问题,结果表明:从长期趋势来看,借贷的偏差会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若借贷高于(低于)其长期水平,未来消费将会削减(扩张)①。Alan and Kim(2011)构建neo-Kaleckian模型,发现消费信用对有效需求、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等存在较大影响②。Kim(2011)通过构建VAR模型,考察了家庭债务、GDP与居民消费等变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短期内,随着家庭债务的增加,经济增长加快;但在长期中,家庭债务的增加将会阻碍经济增长③。Belkar(2007)采用澳大利亚家庭债务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④。然而,郭新华等(2010)则发现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存在非一致性关系,其原因在于:中国市场机制还不够发达、非自愿失业的人口增加、借贷者中持有高资产比例较高等⑤。Debelle(2004)认为低利率和流动性约束的降低推动了家庭债务的增加,家庭部门容易受到利率的影响,当利率处于一个合适的水平时,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就会偏小,有利于保持家庭金融稳定性⑥。Sophocles(2008)根据抵押贷款需求方程发现,在失衡住房抵押市场,住房价格不会改变。这表明,在长期关系中,从抵押贷款到住房价格这种因果关系不存在。但从短期来看,我们发现两者存在双向因果关系⑦。
从上述研究来看,现有文献集中于探讨家庭债务对单一宏观经济变量(如消费、房价、劳动参与率、GDP等)的影响,缺乏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同时考察家庭债务与多个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以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依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宏观经济变量(如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公共债务等),建立VAR模型,利用1997~2011年季度数据,考察我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长短期关系。
二、模型设定
Palley(1994)把时间、总产出、消费者债务、债务偿还比以及利率5个变量纳入VAR模型,考察了家庭债务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模型表达式如下:
outputt=β0+β1time+β2outputt-1+β3Δconsumerdebtt+β4debtservicepaymentt+β5ratet+εt(1)
式(1)中β0为截距项,β1~β5为参数,εt为误差项。通过式(1)可以看出,总产出与上一期总产出、时间、消费者债务、债务偿还比及利率存在关系。该模型得出的结论为:家庭债务的增长促进GNP的增长,但是债务偿还比的增长会减少GNP。
Kim(2011)在Palley(1994)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VECM来分析美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Kim选取GDP、居民消费、家庭债务(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用之和)、资产净值4个变量构建多变量的VECM模型,多变量的VECM模型方程式如下:
Δyt=α11(yt+θ1xt+θ2zt)+β11Δyt-1+β12Δxt-1+β13Δzt-1+ε1t(2)
Δxt=α21(yt+θ1xt+θ2zt)+β21Δyt-1+β22Δxt-1+β23Δzt-1+ε2t(3)
Δzt=α31(yt+θ1xt+θ2zt)+β31Δyt-1+β32Δxt-1+β33Δzt-1+ε3t(4)
上式中(yt+θ1xt+θ2zt)表示x,y,z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α11~α31是调整系数即各变量回归到均衡位置的调整速度,ε1t~ε3t表示其他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该模型的结果表明:在长期内,家庭债务扩张阻碍了GDP的增长,而在短期内,家庭债务扩张有利于GDP的增长。
本文在Kim(2011)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商品房销售总额与公共债务2个变量,分析中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波动效应。模型设定如下:
Δyt=α1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11Δyt-1+β12Δxt-1+β13Δzt-1+β14Δlt-1+β15Δmt-1+β16Δnt-1+ε1t(5)
Δxt=α2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21Δyt-1+β22Δxt-1+β23Δzt-1+β24Δlt-1+β25Δmt-1+β26Δnt-1+ε2t(6)
Δzt=α3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31Δyt-1+β32Δxt-1+β33Δzt-1+β34Δlt-1+β35Δmt-1+β36Δnt-1+ε3t(7)
Δlt=α4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41Δyt-1+β42Δxt-1+β43Δzt-1+β44Δlt-1+β45Δmt-1+β46Δnt-1+ε4t(8)
Δmt=α5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51Δyt-1+β52Δxt-1+β53Δzt-1+β54Δlt-1+β55Δmt-1+β56Δnt-1+ε5t(9)
Δnt=α61(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β61Δyt-1+β62Δxt-1+β63Δzt-1+β64Δlt-1+β65Δmt-1+β66Δnt-1+ε6t(10)
上述模型中(yt+θ1xt+θ2zt+θ3lt+θ4mt+θ5nt)表示x,y,z,l,m,n六者之间的协整关系,α11~α61是调整系数即各变量回归到均衡位置的调整速度,ε1t~ε6t表示其他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
三、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变量包含GDP、家庭债务、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公共债务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7~2011年,本文采用Eviews6.0软件,把各变量的年度数据转化为季度数据。每个变量的含义及数据来源如下:
家庭债务(Household debt):家庭借贷主要通过向正规金融市场上的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及民间金融市场实现。由于家庭在民间金融市场借贷的数据难以获得,因此本文用正规金融市场上,银行和非银行机构向家庭发放的消费信贷数据近似代替家庭债务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http:///)。
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国民经济活动的核心指标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
居民消费(Consumption):根据核算GDP的支出法可知,GDP由一定时期内消费、投资、政府购买以及出口构成,其中消费支出包括购买耐用消费品、非耐用消费品和劳务的支出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社会商品供给和有支付能力的商品需求的规模所决定,是研究居民消费、社会零售商品购买力、社会生产、货币流通和物价的发展变化趋势的重要指标⑨,所以本文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居民消费的变量。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金融资产(Financial assets):金融资产是指单位或个人所拥有的以价值形态存在的资产,包含银行存款和其他一些有价证券。基于一些金融项目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率,本文选用数据是由居民储蓄、金融债、保险及A股筹资额相加而得,能比较正确反映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去向。居民储蓄和金融债的年度数据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整理所得,保险和A股筹资额年度数据根据财新网的宏观数据整理而得。
商品房销售总额(Real estate sales):商品房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经营资格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包括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经营的住宅,均按市场价出售。商品房销售总额=商品房房价×商品房销售面积。商品房房价与商品房销售面积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公共债务(Public debt):公共债务即政府债务,指的是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凭其信誉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在一定时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格式化的债权债务凭证⑩。我国公共债务包含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1997~2004年中央债务数据以历年国债余额替代(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10);2005~2010年数据来自中央财政债务余额(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地方债务年度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审计结果公告2011年第35号(总第104)里计算所得;2011年中央债务和地方债务是根据往年平均增长率估算而得。
四、实证过程及结果讨论
1. 实证过程
(1)单位根检验
本文选用ADF检验上述6个变量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在进行单位根检验之前对所有的数据取对数,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可知,除了家庭债务外,各变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单位根,而一阶差分都拒绝存在单位根假设,所以可以判定所有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2)协整检验
JJ协整检验法适用于多变量的协整检验过程,因本文有6个变量,所以选用JJ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变量的滞后阶数为2阶。
滞后阶数确定之后,我们对各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在5%临界值水平上各变量之间至少存在4个协整方程,因此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GDP、家庭债务、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
(3)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由协整检验可知,6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基于此,本文构建VAR模型进行VECM检验。根据反复操作实验,当滞后期取1时拟合度最佳。VECM检验结果如下:
lnGDP=0.57lnCons+0.13lnPd+0.06lnRes+0.03lnFa6+0.03lnHd+3.2式(13)
式(13)是由VECM检验输出的协整方程式。通过此式可知,家庭债务对GDP的影响是正相关,即当家庭债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则GDP增加0.03个单位。
由表4可知,GDP(系数为-0.054)、居民消费(系数为-0.002)及金融资产(系数为-0.012)的调整系数都为负,在统计上不显著,对修复均衡状态没多大影响;商品房销售总额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53,表明它偏离均衡状态;公共债务(系数为0.234)与家庭债务(系数为0.52)误差修正项系数都为正,表明它们向均衡状态偏离,影响力度较大。
(4)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建立VAR 模型之后,本文采用Generalized分解方法,分别给VAR 模型中各变量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可以得到关于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冲击力度),脉冲响应得出结果如下:
图1~5是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的变化对家庭债务的冲击。由图1~5可知,给金融资产一个正冲击,它在0~6期内对家庭债务的影响是负方向的,其后对家庭债务的影响是正相关并稳定在0.005这一均衡点;当给GDP、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一个正冲击后,它们对家庭债务的影响都是正相关,商品房销售总额对其影响最大,居民消费次之,GDP及公共债务最小。
图6~10是家庭债务的变化对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的冲击。由图6~10可知,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后,家庭债务对GDP的影响在0~5期内是正相关的,相关度呈递减趋势;在6期后,它对GDP的影响呈上升正相关趋势。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后,居民消费在0~1期内是正相关关系,1~15期内呈负相关关系,16期开始呈正相关关系;金融资产呈负相关关系,冲击力度由弱变强,再由强变弱。当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后,商品房销售总额和公共债务都呈正相关关系,冲击力度相似。
(5)方差分解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冲击的重要性,需要进一步利用方差分解,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判断各变量的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重要性。图11~20是方差分解的结果,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变量变化的贡献率(%)。
图11~15表示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冲击对家庭债务变化的贡献率。由图11~15可知,在短期内给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各变量一个正冲击后,公共债务对家庭债务变化的贡献率最大,其贡献率一直上升,贡献率由5%上升到40%;商品房销售总额对家庭债务变化的贡献率次之,贡献率维持在20%左右;GDP、居民消费及资产的贡献率维持在20%以下。
图16~20表示家庭债务冲击对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变化的贡献率。由图可知,在短期内给家庭债务一个正冲击后,它对GDP变化的贡献率最大,其贡献率达到20%;它对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变化的贡献率由开始的0上升到10%左右。
2. 结果分析及讨论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1997~2011年,中国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的主要变量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1)通过VECM检验可知,1997~2011年,中国家庭债务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1997年以来,随着金融市场改革的推进,银行等金融机构放宽家庭借贷条件导致了家庭债务规模快速增加,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效应是积极的。而Palley(1994)和Kim(2011)依据Minsky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发现在长期中家庭债务扩张会阻碍经济增长。本文与他们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就在于本文样本区间只有15年,中国家庭债务的增长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的负面影响还未凸显。在短期内,家庭债务、商品房销售额与公共债务短期波动明显,增长速度快,偏离均衡状态程度大;其余变量处于均衡状态。由于VECM中6个估计模型中都是滞后一期影响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较大,说明家庭债务与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各变量关系以短期波动为主。
(2)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1)家庭债务和GDP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家庭债务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GDP的增加促进家庭债务的积累。家庭进行借贷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平滑消费,居民消费水映出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家庭债务增加在促进居民消费增加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GDP增加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量的增加,当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量存在缺口时,家庭债务就会增加弥补此缺口。2)居民消费的增长会带动家庭债务的增长,而家庭债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复杂的,由最开始的促进消费累积转化到抑制消费增长。在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存在缺口时,家庭通过消费融资来平滑消费,因此家庭债务就会相应增加;随着家庭债务的增加,家庭债务偿还负担就会增加,居民未来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比重加大,从而会降低居民未来的消费水平。3)家庭债务由中长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者信用两部分组成。中国家庭一般通过中长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购买住房资产,房价上涨促进中长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增加,即家庭债务的增加;家庭债务的增加促进家庭购买住房资产,进而促进商品房销售总额的增加。4)公共债务与家庭债务存在一定的关系。家庭债务与公共债务的形成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社会年龄构成、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和财政政策等因素同时影响着家庭债务和公共债务规模(Kvasnicka,201011)。公共债务和家庭债务通过企业产品在市场的需求量产生重要关联。消费者对企业产品的需求越大,会对家庭融资量与融资方式的选择有正面影响(Berlin & Butler,199612)。5)金融资产增加阻碍家庭债务的增加,金融资产包含储蓄、金融债等有价证券,居民消费不用通过家庭债务平滑;家庭债务的增加阻碍金融资产累积。
(3)方差分解分析可知:1)家庭债务增加对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各经济变量的贡献率不是太大,基本保持在10%~20%,家庭债务不是影响GDP、居民消费、金融资产、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增长的主要因素。2)商品房销售总额与公共债务增加对家庭债务的贡献率较大,相互间的关系度较强;GDP、居民消费及金融资产的增加对家庭债务的贡献率较小。
五、结 语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家庭债务的增加促进经济的增长。(2)家庭债务增加促进GDP、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的增加;GDP、居民消费、商品房销售总额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促进家庭债务的增加。(3)家庭债务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复杂的;家庭债务增加阻碍金融资产增加。(4)家庭债务增加引起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但不是影响他们的主要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为:(1)政府及相关机构应制定相关政策控制家庭债务的合理增长,以防出现家庭债务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2)政府和金融机构协力加快消费金融市场建设,加快金融工具创新的步伐,保持家庭债务规模的合理增长,达到扩大内需与实现经济增长的目的。(3)居民应合理配置家庭资产结构,加强家庭债务管理风险意识,提高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实现家庭债务的效用最大化。
注释
①Carmen Martínez-Carrascal,Ana del Río:“Household borrowing and consumption in Spain:a VECM approach”,[2012-03-25],http://bde.es/f/webbde/SES/Secciones/Publicaciones/PublicacionesSeriadas/DocumentosTrabajo/04/Fic/dt0421e.pdf.
②Alan G Isaac, Yun K Kim:“The Macrodynamics of Household Debt”,BIS Working Papers,2011.
③Kim:“Th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Household Debt:An Empirical Analysis”,Preliminary Draft,2011.
④Rochelle Belkar,Lynne Cockerell,Rebecca Edwards:“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and Household Debt”,[2007-05],http://rba.gov.au/publications/rdp/2007/pdf/rdp2007-05.pdf.
⑤郭新华、黄贞贞:《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09年数据为依据》,《现代经济探讨》2011年。
⑥Guy Debelle:“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ising household debt”,BIS Working Papers,2004.
⑦Sophocles N Brissimis:“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rtgage Financing And Housing Prices in Greece”,The Journal of Real Estate Finance and Economics,2009.
⑧郭新华、何鑫:《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变动的实证研究:1978-2009》,《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篇4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经济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计算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分析(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研究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
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 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
“牛鼻子”(周正庆,1991)。社会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理论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研究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企业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分析,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 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经济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
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问题、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法律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理论分析与实例研究,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方法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 员鹑耸敌小比辉颉暗氖焙颍媪俦鹑艘捕运鞘敌型摹比弧埃峁赡苁顾蔷晨龈佣窕4送猓绻笠狄恢辈扇细竦摹比辉颉埃箍赡芊涟笠导浜侠淼纳桃敌庞霉叵档姆⒄埂?br>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
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目前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
篇5
通常我们从统计数字中看到的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包含着通货膨胀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中间产品(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因为企业间相互拖欠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的交易引起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于扩大了企业的实际购买力,增加了中交易手段的总额,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因素(有人认为在独联体国家,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见Rostowski,1994)。特别是经济高增长时期(繁荣时期或”过热“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会影响到以后物价水平的上涨。但在有些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主要受前期通货膨胀引起的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导致同一生产资料的交易款项因价格上涨而较前期增多(我国1993-1995年期间可以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况)。
人们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来企业间的”实际债务“(Rostowski,1994),我们也按照这种办法进行了(见表2)。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在体制转轨经济中,经济结构一般距均衡点较远,不同市场上物价变动幅度相差较远,用物价总水平的变化率(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并不能准确地说明主要由生产资料(中间产品)交易引起的企业间债务。比如,在最近的一次周期性波动中,1992-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roducerindex)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消费品价格指数增幅不大;而当开始实行宏观紧缩政策之后,生产资料价格开始下跌,而消费品价格在1993年下半年以后因成本上涨而大幅度上涨(见表4,各种价格指数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更详细的分析还应计算以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为平减指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从而对企业间债务的实际增长率有一较清楚的认识。例如,在1993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小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而在1994年,由于生产资料价格趋于稳定,以此计算的债务实际增长率就高于用GNP平减指数计算的增长率(见表4)。
3.2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
除了物价水平的上涨会引起企业债务增长之外,经济的增长、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本身也会引起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生产的东西多了,每一笔交易的数量大了,企业间相互欠债的规模自然也会加大。当然,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什么样的实际债务增长率是”自然的“。一个复杂的因素是: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可能正是与企业间债务的过分增长相关(见后面的分析),但是,为了近似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与经济增长率,总产值(工业企业的总交易量)增长率相等的债务增长,为企业间债务的”自然增长率“。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有的年份(比如1994年)企业间债务大规模增加,大大超出正常增长的范围,导致下一年的债务增量虽然绝对值也很大,但与前一年的总量相比增长率却较小甚至出现增长率下降(比如1995年)。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以货币紧缩政策实施以前的债务增量为基数,乘以各年的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得出一个乘积,可视为”企业实际间债务自然增量“;然后各年实际债务增量与这一”自然增量“的关系,可得出一个债务增长是否正常的概念。
3.3 企业间债务的”超常增长“
我们在现实中直接观察到的是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用d表示;而要得到需要我们着重研究的”实际债务的过度增长率“(用d′表示),需要从d中”减去“以下因素:
通货膨胀率,用p表示;经济增长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用g表示;
即:d′≈d-p-g
(此外,还有在前面第2.1小节分析过的企业间债务”体制性增长“的因素。由于统计上存在的困难,我们在对近年债务增长的分析中对其忽略不计)。
举例来说,1994年37万家工业企业间债务的名义增长率(d)约为82.65%,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为18.6%;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为26.8%;我们所能得到的”企业间实际债务过度增长率“(d′)约为37.97%。这一数字比我们直接观察到的名义增长率要小许多,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3.4 当前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
尽管我们指出了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常的或”自然的“,但仍然不能否定我国近年来债务问题的严重性。这可以由以下几个指标看出:
--连续3年超正常增长。在减去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因素之后,我们看到企业间债务从1993年开始连续以较大幅度”超正常“增长,1993年为69.6%,1994年为38%;1995年初步估计还会达到近20%的水平(见表2);
--企业间债务与工业增加值(相当于工业GDP)的比重,1994年已达到43%,已超过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仅低于日本(英国为20%,美国为17%,法国为38%,日本为59%);
--企业间债务的平?quot;周转天数”(表明人欠债务与总产值即总交易量的比重的指标),已经达到114天,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法国为110天),甚至越过了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经济转轨初期(1992)的水平;
--企业间债务与银行(工业)贷款的平均比率,已提高至67%,个案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该比率已接近于一甚至大于一,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一般为一左右);考虑到我国企业的银行负债率本身较高,从整体看67%这个水平也已经很高了。
四、宏观波动与企业间债务行为
从前面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企业间债务自1985年以来一直在增长,但经济高涨时期的增长率和经济紧缩时期的增长率是有差异的,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两次宏观调控的初期,企业间债务都出现了突发性的高增长;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产值的比率以及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货币供给)之间的比率,在经济波动的不同时间是不同的,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
同时,在现实中,人们对企业间债务问题的严重性的感觉,在宏观波动的不同时期也是不同的,在紧缩时期企业拖欠的问题变得十分严重,而在高涨时期,尽管企业间债务也在增长,但人们似乎感觉不到,也并不引起实际的经济问题。这表明企业债务的相对规模和作用也是受宏观经济影响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宏观上对企业债务问题进行分析。
4.1 高涨时期的企业债务
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也会增长。从1985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应收款”一直呈增长的趋势,包括1985-1988年的经济高涨期,和1992-1993年的经济高涨时期。但是,经济高涨期的企业债务变动,相对于紧缩时期,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增长率相对较低。1985年12月至1988年6月紧缩之前,企业名义债务的增长率没有超过35%;1992年经济逐步复苏之后,名义债务增长率从40%以上降至20%左右,1993年1-6月则是近10年来企业债务增长率最低的时期,最高的月增长率为11.8%(1993年6月),最低只有2.6%(1993年1月)。
80年代后期,企业债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幅度较高①,其原因之一是经济“信用化”。1985年开始搞企业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原有的中央计划体制,企业间的横向经济联系扩大,企业间债务从无到有,开始增加。这首先可以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中看出。在1986-1988年9月的长时间里,4000家主要大中型国有企业应收预付货款与工业贷款总额(全部企业)的比率只有7%-9%,没有超过10%;而在1992年底这一比率已达到17%。从企业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来看,1985年12月只是3%,1987年12月只有4%;而到了1992年底,已达到7%。总之,在经济增长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一部分属于正常增长。
第二,企业债务与工业净产值的比率相对较低。1985-1988年经济高涨期,这一比率在3%-5%之间,而1989-1991年的紧缩期达到19.2%,而在1992年经济高涨期中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企业债务的“平均周转天数”相对较短。总的来说,企业债务的周转天数这些年来具有逐步增长的趋势,但是1989年以前只有18.78天,而1989年实行紧缩后突增到32.68天,199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4.53天。而在1992年底,周转天数回落到26.57天,1993年中,实行紧缩政策后,年底平均拖欠时间增至78.32天,1994年底则增至114.43天。
从逻辑上说,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是必然的。一方面,由于经济高涨,大家对未来还款的信心都比较强,相互间欠债的发生也就较为容易;另一方面,高涨时期的总需求因货币量的增大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增长较快,实际的货币购买力较大,企业债务的偿还事实上也较有保证。如果将“经济信用化”的因素剔除,在经济高涨时期,企业间债务可以因货币量的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有很大幅度的增长,而且可能在债务增长的同时,出现债务/贷款比率的下降和债务/产值比率的下降。
4.2 紧缩时期的债务增长
企业债务一般来说是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信用化程度的提高而增长;在企业预算软约束的特殊体制下,企业债务的规模和比重会更大一些。但企业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因,取决于宏观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状况。
80年代后期以来,经历了两次经济波动,而企业拖欠债务的两次突发性大幅度增长,都发生在经济过热之后的两?quot;宏观调控“的初期。一次是1988年中期,6月份的企业名义债务同比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27%增至38.8%,然后继续攀升,12月达到80.2%。最近一次,在1993年7月中央政府实行宏观调控政策之后,8月份的企业债务名义增长率,一下子从上月的11.76%猛增至104.9%,然后继续攀升,12月底达到214.5%,1994年6月份最高峰达到241.8%。
紧缩时期企业间债务猛增的基本原因是货币供给量的突然紧缩而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相应的减少。货币量减少导致企业支付手段紧缺;大量原先在高涨时期预期可以还上的债务现在因资金紧张而无法偿还;已经上马的项目还想继续进行下去,于是又欠下大量新债。这一基本因果关系表现在:
第一,债务周转天数迅速延长,比如1989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1988年的18.78天猛增至32.68天;1993年的债务周转天数从上一年的26.16天猛增至78.32天。
第二,企业欠债总额与贷款(货币供给)的比率,迅速攀升。1988年6月(4000家重点企业)的企业债务与全部工业贷款的比率为0.88%,银根紧缩后迅速上升,1989年6月已升至13.76%;1993年6月该比率为17%,宏观紧缩后1993年12月底猛升至36.86%。企业债务增量与工业贷款的比率也同样迅速增长。
第三,企业债务总额、企业债务增量与净产值的比重,也在紧缩初期迅速升高(见表3)。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是作为货币(国家法定信用)的替代物,在紧缩时期中介着交易活动,是在货币量增长速度放慢,而企业又要继续按原有速度扩大生产,进行投资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有许多体制上的原因,这在前段已经分析过了。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企业间负债会逐步增长,无论在经济高涨时期还是在紧缩期,都是这样。这种基于体制原因的债务增长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包括所有制关系、法制、信用制度、银行结算制度等等)条件下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常数“。而债务增长率?quot;波动”,或者说,那部分“额外的”增加,却有其宏观经济运动的原因,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相联系。因此,我们必须将企业间债务突发性的、大幅度的超常增长,作为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加以对待并由此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
4.3 最终需求即“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历次经济过热,都以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特别是以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为起点。各地方、企业出于各自的利益,用各种办法扩大投资规模,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投资超概算”。据国家计委的统计,1983年以来全国投资项目实际投资平均超概算32.6%。1990年国有、集体单位投资共3477亿元,而资金到位只有2965亿元,存在512亿元“缺口”(见周正庆1990);1994年,据有关部门统计,投资项目的资金到位率也只有70%左右。这超出的部分本身造成企业间相互拖欠。并都期待银行多发贷款来“补足”。也正因如此,每次“宏观调控”也必然首先从“压缩投资规模”为起点。迄今为止,相应的政策措施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手段,压缩建设项目,包括停建、缓建已上马的项目和停止批准新项目上马;其二就是货币政策,压缩贷款规模,从支付手段上进行控制,减少投资支出。
在传统的行政计划体制下,行政手段本身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能较为有效而迅速地压缩投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紧缩之后由于项目下马,不再发生新的购买行为,企业债务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大幅度超常增长的时间也不会很长。而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行政分权,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导致中央的宏观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大大减弱;在地方、部门和企业利益的驱使下,人们往往会对中央压缩投资规模的政策采取抵制的态度。这一方面使中央政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货币政策即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整个压缩投资政策的有效性会越来越弱,地方和企业会想尽各种办法避开中央宏观政策的影响,使自己的投资项目以及地方增长计划继续进行下去。所谓“各种办法”,归根到底就是在缺乏货币交易手段的情况下,用欠债、赊账、不还旧帐等办法,得以继续获得投资物品,维持项目进行。正是对投资资金供给的压缩和地方企业继续维持投资规模的各种办法,导致了企业间拖欠债务的增加。
不仅如此,投资项目和投资物品(主要是建筑材料、机电产品、车辆工具等)货款拖欠造成的企业间债务,在中国经济中还是整个企业债务链的“源头”或“牛鼻子”(周正庆,1991)。总产品可分为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两类;中间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需求;而最终产品的需求又分成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其大小取决于消费品购买力与投资品购买力。在宏观调控初期,消费购买力并不发生紧缩,相反,由于经济过热,物价已开始上涨,通货膨胀预期加大,人们的消费需求会加大。而宏观紧缩政策的主要作用方向就是压缩投资需求。投资品购买力因货币供给的紧缩而下降,与此同时投资项目拖欠款增加,构成企业债务大量增加的初始点。
投资项目拖欠,导致投资品生产者“人欠款”增多,流动资金开始紧张,本身无力支付购买原材料的款项,于是也开始“欠人”,即欠中间产品制造厂家的货款;接下去位居生产流程“下游”的中间产品制造厂家因周转不灵,开始拖欠“中、上游”中间产品制造者的货款,于是企业拖欠一环环扩展开去,向整个经济蔓延。
如果我们假定由于企业拖欠,使投资活动与其他生产活动的水平(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同时工资支出(用现金)与生产保持同步增长,那么消费需求也就可以保持不变。这说明,上完全可以仅仅因为投资项目拖欠而造成整个经济中企业间债务的增加。在现实中,1993年以来宏观调控期间,消费品需求基本上保持了过去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生产经过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供销衔接也基本上处于良好状态;企业债务的增长,主要是由于投资项目拖欠和投资品需求缺乏资金保证所引发的。据在东北三省的调查,企业欠人款总数的25%是投资项目欠款;而这25%的欠款,又直接引发“上游”产业的欠款,加起来能占欠人款总额的75%(周正庆,1993)。关于湖北钢丝厂的案例研究表明,货运汽车这一最终产品(投资品)生产厂家的拖欠,引起了“上游”一大片企业拖欠问题的愈演愈烈。这一分析提醒我们充分注意“最终产品需求”这一重要环节。
当然,宏观货币紧缩政策一般也会引起企业流动资金的普遍紧张,从而在一些中间产品生产环节上加剧企业拖欠的发生。比如1995年山西流动资金贷款规模比上一年少增加2000万元,而同期工业生产增长了17.1%,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最终产品需求是有资金保证的,一切中间产品的购买最终也会有支付手段与其相对应。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总需求说到底是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我们事实上可以将货币供给量减少引起的购买力(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部归结为最终产品购买力的减少。同时,还要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金不足,企业通常的一个对策就是“挪用”流动资金,这是造成所谓流动资金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近的二个实例是山西某化学工业集团1995年动用6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因资金不足而不能完工的投资项目上去;山西某液压件厂动用2000万元流动资金投入到投资项目上去,流动资金一下子减少20%。
总之,把握企业间债务的增加与最终需求减少的关系,对于理解企业间债务这一现象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关系以及解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等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4.4 不同的宏观政策与不同的“债务链”传导过程
虽然从基本经济关系上看企业间债务的突发性大幅度增长可以归结为最终需求的紧缩,但债务增长过程中的“传导”过程,可以因宏观政策的不同以及操作方式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这可以由1989-1990年和1993-1994年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出现的不同情况中看出。
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时起主要作用的首先是压缩投资规模,减少投资贷款。这首先导致投资项目欠款增长,然后,因此为“源头”,债务链一环一环的传导下去,整个经济发生“市场疲软”,并使企业间债务逐步增大;企业间债务的增长由最终需求规模缩减所决定这一关系也就表现得较为明显。
而1993年实行紧缩时首先起到决定作用的政策是“抽回贷款”,也就是紧缩货币,而且力度较大。因此,这时出现的情况是所有环节上都发生“资金紧张”,并导致所有环节、所有部门的企业间债务突然增大。然后,随着债务周转天数以及债务的进一步增加,投资项目拖欠的决定性作用才逐步明显起来(由于缺乏不同部门的数据,因此无法在此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定量分析,但以上的说明是对于我们个案调查与各方面情况反映的概括)。
4.5 企业间债务拖欠与宏观政策效果的减弱
企业间相互拖欠债务的突发性增加,是在紧缩货币供给,而企业又没有相应地缩减投资与生产的条件下形成的,企业间债务的这种增长,其宏观效果就在于“抵消”或“瓦解”了中央货币政策的效力。在宏观货币紧缩的背景下,大量增加的企业间债务相当于企业用相互之间给予的信用,代替减少了的国家法定信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实现了产品的购买,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本文前面给出的公式(1)(见第一节)表明,在一定时期,若PT为一定(增长速度为一定 ),V不变(假定),M减少或增长速度下降,必然是因为D,即企业间债务增量增加。这一关系体现为企业间债务与贷款量(M)的比率,与工业总产值(PT)的比率增加。
1993-1994年的经济紧缩时期,上述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1993年7月之后货币供给量的增幅速度下降,而企业间债务猛增。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居高不下,GDP在30个月内仍保持在10%以上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与此同时,间债务的增加还是通货膨胀率长期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原因,关于1993-1994年通货膨胀原因的,参见樊纲1994、1995)。宏观调控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来控制通货膨胀。但是,企业间用相互欠债的方式来中介其投资物品和中间产品的交易,就使得有限的、甚至是相对减少了的货币量得以“节省出来”用于其他物品特别是消费品的交易,使得工资性支出和消费品市场上的购买力仍能持续增长,从而使得以消费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这是这些年来政府与民众主要关注的指标)在实行货币紧缩政策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居高不下,延缓了通货膨胀率下降的过程。这一关系在1993-1994年的宏观调控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4.6 产成品积压、“资金占用”与企业债务
在紧缩时期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产成品库存增加,个别企业资金“被占用”或被“套住”。由于这一现象往往与“资金紧张”和“企业间债务增加”共同发生,于是经常听到人们说“库存积压引起资金紧张”,或者“企业债务拖欠引起库存积压”。这些观念似是而非。
首先,是因为没有人买或人们买不起,即没有资金来购买产成品,才发生了库存积压。如果以前在正常情况下产品卖得出去,现在因货币紧缩而发生库存增加,则说明是“资金紧张”造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当然可以说是产品卖不出去,占用了资金,资金回不来,无钱买东西发工资,也不能还别人的债;但是,从全的角度看,资金是流通的,不是在A的手中使用,就是在B的手中使用(当然流通速度会发生变化);产成品积压是因为“别人”资金缺乏不来买你的产品,而不是因为你的产品积压而导致社会的“资金紧张”。
其次,产品积压,没卖出去,说明就这些产品来说没有交易发生,即没有货币中介的交易,也没发生由企业间债务为中介的交易,也就根本没有引起什么企业间债务的增长。“下游企业”在“最下游企业”拖欠债务而没有购买“上游企业”的产品,是由于“最下游企业”缺乏购买手段,既没有货币,也无法再用制造企业间债务实现购买,总之是因为有人盲目生产,又没发生企业间的债务,才形成了库存积压,而不是相反,是库存积压导致了企业间债务。
有的企业产品老化,没有市场,但又继续购入原材料进行生产,结果是产品积压,欠的债还不上。这种“坏债”,当然是经济当中的一种微观的或结构性的隐患(只能用停产、破产、改革等方式解决)。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中,我们也要分析一下:第一,这些企业在经济高涨时期卖得出东西,而现在卖不出去,这是因为宏观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第二,假设这些企?quot;改好了“,生产对路了,产品卖出去了,如果经济的总体规模没有变,总需求还是那么大,那么人们买了这个企业的东西,一定少买了另一些企业的东西,这个企业不欠帐了,另一些企业却会增加欠债。这说明,微观的”生产不对路“、市场竞争问题,与宏观的总需求缩减问题是不同的,是可以分别加以分析的,也是需要由不同的对策加以解决的。
当库存积压发生,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有钱来买东西“?就微观问题或结构问题来说,是因为产品”不对路“或质量太差而没人要;就宏观问题来说,则是因为人们缺乏购买手段,或是缺乏货币,或是无法继续增加企业间债务(不能?quot;赊卖”),而不存在相反的因果关系。就宏观问题而言,是“资金紧张”(这件事的发生可以是因为必要的紧缩政策)引起“库存积压”和“企业拖欠”这两个后果,而不是相反;同时,也不是“库存积压”引起“企业拖欠”。
五、各种“清欠”方式及其效果
5.1 我们面临的特殊问题
企业间债务不能无止境地扩大下去,问题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如何解决的问题。
如果企业是“预算硬约束”的,自己的债务要由自己负责,还不上债要受到社会的制裁,直至破产倒闭,由债权人对其进行清偿或强迫还债。那么,一方面,企业间债务的极限会很快达到,另一方面,企业间自己会采取各种方式及时偿债,因而会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一种企业间自己自动或被迫清债的机制。企业清债的措施包括:第一,减少自己本来的资金储备?quot;闲置资金“;第二,出售或抵押一部分自有资产,包括拍卖一部分别人欠它的债务或自己欠人的债务(这需要存在一个商业票据交易机制,而卖出债务的价格显然要依当时的经济形势与企业的市场前景、还债能力等所决定而打一折扣)。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债务长期不还的最终后果便是破产,这当然是信用状况彻底恶化的苦果。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却是企业预算软约束,欠债可以一直拖下去不还,也不会受到什么惩罚,至少不会破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间债务量会无限增长,另一方面也不会?quot;自发的还帐机制”,再加上市场体制还不健全(比如说还不存在债务转让或拍卖的市场),信用制度与体系(执法)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和处理企业间债务问题?
5.2 一些“清欠”措施的局限性
解决企业间债务增长的根本性措施当然是要进行制度的改革,最终实现企业的预算硬约束。但体制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不可能一时奏效,在此过程中债务还在增长。因此,问题便归结为在中、短期内,如何缓解这一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题。以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主要有三:第一,银?quot;注资清欠“;第二,债务各方”多方磨债“,即相互抵销一部分债务;第三,”三不原则“,主要就是不还旧债、不付货款、不发新货,以此来逐步减少债务。
以往的经验已经证明用银行注资清欠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反倒会前清后欠,越欠越多。同时,由银行出面注入资金统一清欠的作法还是属于一种”一刀切“的计划经济作法,而不能使市场的优胜劣汰选择机制发挥作用。企业与企业是不同的;不同企业欠下的债务的性质与质量从而其债务的”市场价值“也是不同的;有的企业产品有销路,经营状况也好,一时由于其他企业拖欠而欠下债务,从长远看是能够还上的,因而其市场价值就高些;而有的企业属于该破产、被淘汰之列,所欠债务本身就属于不良债务,不值什么钱,银行帮它还债,实际是高估了其价值,使它占了好企业的便宜,并助长了不良企业靠在国家与好企业身上而不思进取的恶习,因此,属?quot;劣币驱逐良币”的作法。在向市场机制过渡过程中,这种作法应尽量减少与避免。
企业间实行的所谓“磨债”,即多方债务人与债权人走到一起,将相互之间可以抵销的债务冲抵掉,这种办法当然有助于削减一部分债务,但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普遍实行。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分析与实例,由于企业债务?quot;源头“是投资资金和最终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而在投资项目还未完成投产之前,债务链不会是”闭路“的,大量债务无法通过企业磨债加以处理(无论是银行组织还是企业自己进行)。第二,在”实物偿债“的场合,这显然受到实物交换本身的限制,受到实物的”通用性“的局限。如果是象能源、基本原材料这种通用性较强的部门欠债,情况会好些,但恰恰是这些处在生产环节的最上游的部门企业被人欠最多(最下游的债务最终都会递推到这些最上游部门)。这些部门的债至少是无法用磨债的解决。
”三不原则“是在企业间拖欠问题发展到一定极限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较为严厉的措施,也是有利于打消人们无限借债预期的较为有效的措施。事实上,1993年以来,出于宏观调控、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需要,中央货币当局自己一直在采取一种不妥协原则,即一直不搞”注资清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产业已经被巨额拖欠首先逼到了”极限“,到了再没有现金收入就难以为继(发不出工资)的地步。于是我们看到了煤炭、电力、冶金等”最上游“部门最先搞起了”三不主义“,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三不原则“自然是有效的。1995年上半年,在全国企业间债务继续增长15%左右的情况下,煤炭行业人欠款下降了16.2%;冶金行业下降8.3%。事实上,在各行各业,只要欠债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使企业难以为继下去,都会或多或少地采取”三不原则“,有的更严厉些,有的则采取”至少付50%现款“或至少还20%才发新货的办法,等等。对个别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的界限在于它是处在生产流程和债务链条的哪一环节上。上游企业人欠大于欠人,三不原则就可以较为严格,因为不必担心别人也对它实行三不原则;而对另一些处在”下游产业“的企业来说,实行”三不原则“就较为”心虚“,因为当它们? 员鹑耸敌小比辉颉暗氖焙颍媪俦鹑艘捕运鞘敌型摹比弧埃峁赡苁顾蔷晨龈佣窕4送猓绻笠狄恢辈扇细竦摹比辉颉埃箍赡芊涟笠导浜侠淼纳桃敌庞霉叵档姆⒄埂?BR>
从宏观角度看,当企业间债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往一段时间是靠着较高的债务增量来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下,大家都真正实行”三不原则“可能导致交易量和增长率的猛然下降和失业率的猛然上升。由于前一阶段企业债务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瓦解“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作用,迫使中央货币当局在延长紧缩时间和紧缩力度上,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过猛“的方式(如1994年末以来的实际情况);当企业开始被迫采取”三不原则“,企业间债务停止增长的时候(D=0),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就是说,使M有较多的增长),则经济的失业率将会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这里的悖论在于:如果要求企业实行三不原则减少债务而无适当的货币扩张,失业率会猛升,而若同时采取增大货币供给的措施,又可能使企业因资金宽裕而放弃实行三不原则,使企业间债务又重新增长,对政府的”软约束预期“提高,经济再度进入过热状态。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有效政策组合,是解决企业间债务及其连带问题的一个关键。
六、对策思考:调节总需求
与降低债务/产值比率
6.1 长期出路:通过基本体制的改革,”硬化“债务人的预算约束
从微观层次上看,企业间债务拖欠情况恶化最根本地出于两个基本的原因:一是国有企业靠在国家信用”背景“上,欠债人并不能在事实上对自己的债务负责任,欠多少债也能生存,花多少钱也不会破产;二是整个信用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债权人利益得不到保障,拖欠者得不到应有的、有效的处罚,结果形成了”欠得越多越占便宜“的”欠债文化“。如果这两方面的制度(国有企业与法律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改革,企业拖欠问题就不会得到根治,良好的信用关系不可能建立起来。
产权关系改革(包括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企业改革、银行制度的改革、破产制度的建立、法律制度的完善,等等,都是硬化债务人预算约束的必要前提。
这些制度的改革,都是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实现并见效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在这些基本制度要素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在中短期采取可能使情况有所改善或得到控制的对策。
6.2 中期改进:加强银行对企业债务的监控,发展商业票据交易与结算机制
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较为具体的一个体制上的原因是由于市场不健全,银行部门没有严格履行对企业信用状况的监督,防止企业间债务恶性膨胀;另一方面,企业间债务之所以能在较大程度上抵消和瓦解宏观货币政策的作用,原因之一则在于企业债务不能与货币(贷款和现金)更紧密地”挂勾“,企业大量拖欠,并不妨碍其继续获得贷款,继续大量申请贷款,甚至可以在银行有存款仍然拖着债不还;企业债务本身也不能通过某种市场机制进行”货币的评估“。
银行对企业债务往来应实行更加严格的监控,将其与银行贷款联系起来,实行”债贷挂勾“。比如,当企业欠人债款达到某一规模(比例)时对企业贷款实行一定百分比的”清债预留“;达到某一更大规模时停止银行贷款,以此从贷款与债务的关系上降低企业的”拖欠极限“。
商业票据交易机制是资金市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间债务的凭证即商业票据的可交易、可转让、可抵押、可兑现,是对企业信用状况、负债状况以及经营状况进行市场评估的重要机制。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好帐“与”坏帐“可以通过票据的转让价格显示出来;也可使企业通过这样一种竞争性机制获得更多的公开信息,也使较好的企业获得应有的流动性。票据市场本质上也是企业间多头”磨债“的一种机制,但由于信息的公开性和更多企业的加入,它可以突破少数相关企业”磨债“在信息和交易手段上的局限性。
发展商业票据结算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但应结合《票据法》的实施,尽早开始,逐步完善。
6.3 短期对策:”三不原则“加宏观政策的调整
体制改革、市场发育都是中长期才能奏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面对大量现存的、并且还在继续增长的企业间债务,我们还必须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制定短期的政策加以缓解,以使好的企业摆脱债务拖欠困扰,保持经济的增长与稳定。
根据前面的一系列分析,我们知道,第一,企业间债务的过度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宏观现象,是与压缩最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相关联的。第二,以往用在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清欠资金“只是一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的具体形式)的办法,放松银根、缓解企业间拖欠问题,由于并没有解决最终需求不足的问题,结果只能造成前清后欠及企业库存增加,还能造成好债坏债一锅煮,企业更加放心大胆地拖欠的不良后果。第三,如果企业拖欠问题进一步恶化到极限程度,迫使更多的部门和企业实行”三不原则“,企业间信用突然紧缩,又会导致宏观经济过度滑波。
根据这些分析,我们建议在情况下,即在1993年7月开始实行紧缩政策30个月之后,在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10%、经济增长率下降到10%左右、宏观调控目标已基本实现的情况下,采取以下的综合治理措施:
--进一步明确宣布今后不再搞注资清债;
--鼓励企业之间自行”磨债“,银行适当帮助提供信息,为企业”搭桥“(但银行本身不负责清欠);
--在人欠大于欠人的行业继续鼓励企业实行”三不原则“;
--在实行以上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向在建和一些新建项目发放投资贷款,在投资资金这个与最终需求直接相关的环节上向经济中注入资金,缓解企业资金不足的境况,压缩企业间债务。
--对一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能够出口或实现进口替代的企业,适当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国内最终需求和减少”对国外的最终需求“,而不是”挤掉“另一部分国内需求);但要明确不能再普遍追加流动资金贷款;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第一,在最终需求环节上注入银行贷款,增加了货币供给,可以在宏观调控目标基本达到的情况下实现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仅仅在经济的中间环节上增加流动资金供给而不扩大最终总需求,不可能实现此目的,而只能增加库存。
第二,用这种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然后逐步流通到整个经济,可以通过经济内部的选择与竞争机制(我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了一定的竞争机制),让企业去自行解开债务链,使好的企业获得更多的流通手段,差的企业获得较少的补贴(目前情况下还不可能完全取消),而不象”注资清欠“或普遍增加流动资金贷款那样抹杀”好债“与”坏债“的差别。
第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一般地说总是政府应该履行的公共职能;在目前能源、、城市基础设施仍大量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这些领域里的投资,既可以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并更充分地利用目前已出现闲置的生产资料生产能力,又能缓?quot;基础瓶颈”,释放出过去被瓶颈压抑的大量生产能力,增加总供给,缓解总供求之间的矛盾,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同时,在目前地区间差异较为突出的情况下,适当增加对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可缓解这方面的矛盾。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出面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质上属于“财政政策”的范畴;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于缺乏完善的货币市场和政府?quot;公开市场业务“机制,我们执行这种财政政策,事实上还不得不通过直接由银行增加政策性长期贷款的方式进行,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式,也会造成一定的扭曲(当然比单纯增加流动资金贷款所造成的扭曲要小)。这是需要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逐步创造条件加以扭转的。
6.4 当前考虑宏观对策时应注意把握的几个原则
在当前制定解决企业间债务的对策时,要注意把握以下一些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