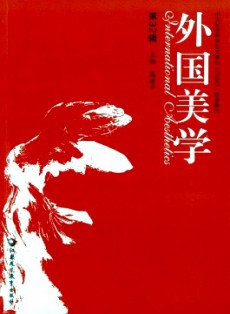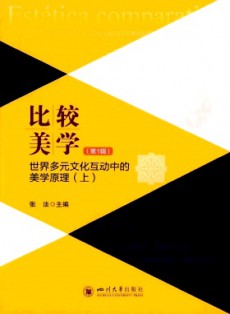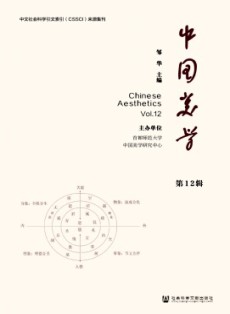美学六种审美形态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7:47:10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美学六种审美形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近来,笔者研读了本学期选用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中《音乐鉴赏》教科书,其中的第二单元《音乐的美》,使笔者感到非常欣喜。总之,笔者认为《音乐的美》这一单元的内容,填补了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中音乐美学基础知识的空白。该单元将音乐美学知识作为专题内容提供给学生,将古今中外23首优秀音乐作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加以分类。(笔者归纳见表)
篇2
一、前言
现代设计产生于西方,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大量的外来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中国的商品在与外来商品竞争的同时,需要设计和包装,站在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即是一些物质与精神的沉淀。
本文探讨当代设计的着眼点从设计的客观存在与设计师的主观意识上转移到把设计本身置于传统文化领域内,从传统的文化价值形态中进行分析中国味的视觉表现和其应用。
二、中国传统美学观
中国味的设计是以传统美学观为基础的,下面浅谈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审美的几点特质。
1.以和为美
在“美在整体”的基础上,生发出“以和为美”的审美思想,既要保持一个整体就要讲究“万物的和谐”,而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节制”,这种节制表现在美学上就是“尚清”、“尚淡”审美追求。
2.意境之美
画外有画,景在画中,意在画外的情趣美,将含蓄之美融入意境之中,始终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家追求的目标,这种艺术境界的追求正是具备了情、景、境、形、神多方面因素,综合统一的结果。
3.神与物的统一
中国传统审美强调人的精神与审美事物的和谐统一,即“神与物的统一”,这种审美情趣也是来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神与物的统一”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的审美活动之中。
三、中国特色的视觉元素和现代设计
在传统美学观基础下,中国特色的视觉元素本文从图案,色彩,文字三方面来阐述。
1.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本文试以吉祥图案的审美特征为标准,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1 汉语言谐音的运用
中国人逢遇喜庆吉祥,偏好讨个“口彩”。例如,一只鹌鹑与九片落叶组成“安居乐业”(鹌居落叶);鱼谐音“余”,馨谐音“庆”梅谐音“眉”、等等。
1.2 对动物生态属性的借助
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喻志,附会象征。例如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
1.3 对有代表性事物的寓意
用代表性事物来寓意吉祥喜庆,是吉祥图案对素材较为直接的应用方式,能给人最为直观的祈福印象。例如金钱、玉石、元宝等都是属于财物象征的,将其直接应用于工艺品上,表示对富贵的追求。
1.4 吉祥文字的直接应用
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张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客体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
1.5 古代诗情画意的应用
古代试词歌赋历史悠久,沉淀深厚,常借用比、兴之法,借物以言志,思路广阔如野鹤行云,这些特点被吉祥图案巧借,可以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氛。
2.汉字特色
古老的汉字通过象形、会意等六种构成手段来传达特定的表意性。加之“图形化”“符号化”的表现特质,可以说是标志的最原始形式。同时,甲骨文、篆、隶、楷等各书体不同的表征也为现代标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2010年世博会会徽,就是以汉字“世”为基础设计的,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的图形,象征着“你、我、他”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崇尚和谐、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
3.传统色彩
传统色彩来源于传统艺术,包括民间和宫廷的,最能反映色彩的莫过于中国画,还有文学作品里的描述可见一斑。
4.传统元素的应用
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借鉴。现代设计必竟要反映出当代生活的时代面貌,当代的语言与形式,采用复古形式,照搬传统肯定是不行的。把现代与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并能较好的反映出“传统中的现代”或“现代中的传统”,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设计理念及设计手法,是值得借鉴或采用的。
后现代主义设计中大量采用历史主义、古典主义、装饰主义设计元素,强调以历史风格、古典风格为借鉴,并从中吸取装饰营养,采用折衷手法,对历史风格采用抽出、混合、拼接、嫁接的方法,但这种折衷处理基本上是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历史风格、古典风格、装饰风格来改造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对传统的重构,不是随意地进行重新组合,而应是基于美学原则的理性思维之下的,要符合现代形式美原则。
四、结语
当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的个人问题而是设计师与大众的配合的问题,寻找相同的切入点,即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参考文献:
篇3
文学作品取材于生活,也表现了生活;塑造了人物,表现了人性:这是文学作品的特点,也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面对生活?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审美教育性问题。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不同的视角进行探析。
一.文学审美性之美学视角――掌握理解美的形态与价值
文学是美学的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以及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学和美学的学科边缘在不断变化。审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审美趋于泛化,种类繁多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成为了美学良好的载体,无处不在地表现着美学。优美、自然主义,如朱自清的《春》;崇高,自由,浪漫,诗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悲惨,沉思,小说,如《狂人》;丑陋,荒诞,批判主义,如《悲惨世界》……这些丰富多彩的表型形式、作品风格中,处处揭示着美的价值,或正面,或反面,或歌颂,或批判。是对人性的教育,是对人格的教育,是对伟大和崇高的歌颂,是对丑陋的反思,是对黑暗的批判……
二.文学审美教育性之教育视角――塑造优秀人格
文学是对生活的再现,是对人的再现。文学教育的实质是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培养。加强文学审美教育,意义重大。
文学审美的价值的教育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会做人,以较高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培养认真负责的态度;学会做事,形成高尚的价值观;学会认知,塑造完整的人格。文学审美教育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同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富有感染力。在陶冶情操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读屈原的《离骚》让人涌现无限的爱国之情,读《论语》会积极思考自己的所言、所做、所为。正是这些文学审美教育活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也塑造着我们。
三.文学审美教育性之心理学视角――感受审美体验,把握人生社会
文学审美教育性活动具有一定心理学的基础。加德纳的八种智能结构中,六种与审美有关。艺术心理学则很好地说明了审美的心理体验过程,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学作品中,很多描绘通感的词语来源于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和熟悉的表达方式。宋代词人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简简单单的“绿”将春回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非常灵动地表现给读者,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给读者以极大的美学体验。
文学审美教育性是情感的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性审美情感,主要是在认识审美活动过程中得以体现。体会艺术家将自然情感经过处理和提升之后的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的具有符号性质的审美情感。第二个层次就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更深层次的理性道德情感,诸如善良,勇敢,崇高,伟大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所表现的爱国情怀让人动容与佩服和尊敬。美只有与善结合,才是真正的美,也只有体会到了这种美才是真正的体会美。高尚的道德需要与美好的情感相结合。
四.文学审美教育性之生命学视角――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学作品中塑造着形形人物,他们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各自的命运,但是都可以归纳为两类:或从正面进行歌颂,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从反面进行批判,例如《巴黎圣母院》和《双城记》。尽管角度不同,但是都给读者以思考,思考生命。我们应该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的奇迹,敬畏生命的价值。文学作品中生命意义的教育,给我们震撼,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命的价值。
五.文学审美教育性之语言学视角――理解文学语言,体会文学意蕴
篇4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小胺攮、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同时还包含欣赏活动或创作活动中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
篇5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自然物象与主体情、意、理、等相契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书法是一门意象艺术,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借助汉字载体,表现书家的个性、情感、禀赋、学识、修养甚至瞬间感情波变,她是最简明而又最神秘的寄情艺术。
一、“意象”概议
书法艺术的意象转换,也即自然之象到书法符号之间的转换,关乎自然原理与对应规律的辩证统一体。在魏晋以前,象与意一直处于一种自治的融合状态,还未出现对“象”或“意”的单维强调。在书法领域第一个使用“意象”概念的,公推唐代的张怀瑾,其《文字论》自评书云:“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动。或擒若虎豹,有强梁孥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蠼之势。深刻而形象的阐明了意象在书法创作中的核心作用,并讲述了“意与象”的辩证关系,主客体相互渗透互补而成“意象”。
二、书法形成的意象美
一幅美的书法作品,都是局部与整体和谐统一在一起的,也就是由线性语言符号到文字语言的过度。书法语言的运用,即用笔,用墨,章法等皆依附于文字这一载体,然而文字的起源也同样源于自然物象,其创造途径有二:一是描写形象;二是符号抽象。东汉许慎总结提出汉字的构造,创造的六种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其中对象形的解释:“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对指事的解释:“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正是画图、符号两个方面。汉字的主要源头应该是原始图画,它不像任何具体事物,但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当然,图画文字也不是事物客观形象的具体描绘,而是捕捉其最有特点的部分特征加以简笔勾画而已,这也就是对具体事物加以概括、夸张、抽象的意象思维过程,不像之象,便是意象。但成熟的文字体系便是由象形图画到具有象意结构的方块字体的完结,这也正是我国古人对于空间观念思维方式的完美体现,把汉字随体诘屈的图画文字演化为我国独有的方块文字,后来在为满足书家对文字语言审美的要求过程中,笔墨纸砚不断出现,同时融入创作主体的情感意识,在心理上与自然相通,“天迹心象”“物我合一”,形成我国抽象的书法艺术之美。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书法艺术的创造过程是对客观现实事物的美的反映。自然美的观念所关系的理论范围可能是很广泛的,它的形成过程也许是很复杂的,书法艺术的诞生也是基于自然,肇于自然的。一幅完美的书法作品,必须以简单的汉字及自然物象为基础,经过书家主体意识的形象思维活动,由具象概念加以提炼发展而成为意象,再由意象发展而形成美的观念。所以,最终的意境美是由物象一表象一意象的过度。物象是指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表象则是主体潜在意识的加工过程,意象则是书家在表象基础上渗透了主体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思想,审美观点以及其构思过程,从而形成的意境美。
三、有象具意通雅韵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