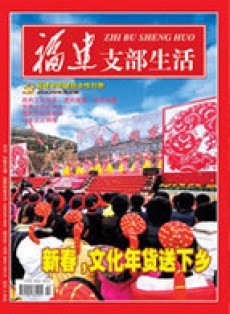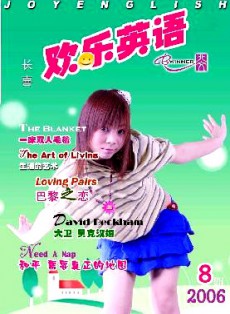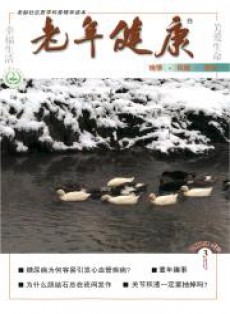社交焦虑治疗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1 17:33:26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社交焦虑治疗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20-0004-04
一、前言
社交焦虑障碍指对社交场合或在人前表演(操作)存在显著的、持续的担忧或恐惧,是一种常见并具有潜在致残性的精神疾病。社交隔绝和社交技巧贫乏可导致青春期的多种问题,其中包括抑郁、消极的自我评价以及孤独(Rubin & Stewart,1996)。其他可能结果有物质滥用、持续的学习和就业困难,日渐贫乏的人际关系等。
社交焦虑障碍在儿童青少年中发病率高,危害大。但社交焦虑障碍通常会被误认为是“害羞”问题而被忽视,再加上社交焦虑障碍者本身就具有回避陌生人和害羞这一特点,不能主动寻求帮助,从而导致社交焦虑障碍患者的诊断治疗被延误。因此,对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诊断与治疗进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社交焦虑障碍的临床特点及诊断
社交焦虑障碍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对社交场合存在持续恐惧,当患者暴露于公共场合时会感到极度焦虑;另一个是患者本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恐惧是不合理的,但是却无法控制。一般说来,社交焦虑障碍患者在与自己认识的人相处时社交功能良好,但当他们与陌生人交往或处于自己认为会得到负面评价、会丢脸或困窘的场合中时,就会出现惊恐症状。如患有社交焦虑障碍的儿童在有陌生人的场合会哭叫、发脾气、发冷或退缩等[1]。有学者研究发现,患有社交焦虑的儿童几乎不能参与传统的课堂和学校活动,在课堂上会拒绝回答问题或提出问题,拒绝在同学面前讲话,拒绝使用公共盥洗室以及在食堂吃饭;避免与同伴交谈,拒绝与同学通电话,拒绝参加团体活动,也不愿意邀请朋友一起玩耍;患有社交焦虑的青少年则会拒绝与异性的约会、参加同龄人的社交活动,甚至不愿寻求工作[2-3]。社交焦虑通常有泛化和未泛化两种形式。社交焦虑未泛化者只有经历典型性情境时才会感到焦虑,通常只对操作性事件产生恐惧,如害怕或逃避在公众前的演讲等。而社交焦虑泛化者即使在独处或未被他注视或评论时都会感到痛苦,如参加正常的聚会、维持交谈等[4]。
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四版(DSM-Ⅳ)关于社交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为:(1)处于一种或多种社交或表演场合,如暴露于不熟悉的群体或者有可能被别人仔细观察时,就会产生显著而持续的恐惧,认为自己可能会做出一些使人难堪的行为,并为此感到害怕或显示出焦虑症状;(2)处于特定的恐惧场合几乎总能引起焦虑,可能表现为情境相关型或情境易感型恐惧发作;(3)求助者认识到这种恐惧是过分的或者不合理的;(4)求助者总是回避处于这些社交或者表演场合,如果无法回避则极度焦虑和苦恼;(5)对于这些社交或表演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回避、焦虑和苦恼,显著影响求助者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社会关系,求助者为自己有这种恐惧症而感到显著痛苦和烦恼;(6)年龄小于18岁的求助者,病程持续时间至少六个月以上;(7)这种恐惧或回避的症状不是由于某种物质(如药物滥用、药物治疗)或者某种一般性躯体情况所直接造成的生理作用,也不能归结于其他精神障碍;(8)如果患有某种生理性疾病或另外一种精神障碍,那么(1)中所表述的恐惧症状与生理性疾病或这种精神障碍无关;如果是泛化型则需要满足绝大部分的社交场合都会引发恐惧(同时可以考虑回避型人格障碍)的诊断。[5]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诊断标准(CCMD-3)认为,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以过分和不合理地惧怕社交场合和人际接触为主的神经症。病人明知没有必要,但仍不能防止恐惧发作,恐惧发作时往往伴有显著的焦虑和自主神经症状。病人极力回避所害怕的客体或处境,或是带着畏惧去忍受。求助者常伴有自我评价低和害怕批评的特点。[6]
三、社交焦虑障碍的心理治疗
社交焦虑障碍作为一种抑制儿童社会交往活动的精神障碍,会损害病人的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如果儿童在早期没有对之进行有效的治疗,会延续到成人期,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目前认知治疗技术、行为治疗技术、认知行为治疗等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社交焦虑障碍。
(一)认知治疗(CT)
认知治疗理论认为认知抑制是社交焦虑的核心因素。社交焦虑症患者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并且设想别人会给自己负面的评价。社交焦虑障碍患者这种特征在长期实践中相对稳定下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式的认知模式。通过认知治疗可以帮助患者辨认并纠正顽固存在于头脑中的错误的、非理性的思维模式,帮助患者建立交往信心、减轻对交往情境或交往对象的恐惧和担忧。
1.理性情绪疗法(REBT)
理性情绪疗法的理论基础是情绪ABC理论。治疗师根据ABC理论对社交焦虑患者的问题进行初步分析和诊断,找出其情绪困扰和行不适的具体表现(C),以及与这些反应相对应的诱发性事件(A),并对两者之间的不合理的信念(B)进行初步分析。通过分析让患者意识到自己社交焦虑的根源不在于社交情境或交往对象,而在于患者头脑中对于社交情境或对象的非理性、不合理的认识。然后通过阐释证明、引导领悟、与不合理信念辩论、RET自助表和合理自我分析报告等技术,改变社交焦虑患者头脑中歪曲的、不合理的认知,建立起较为正确的、合理的理性信念,从而调节和改善患者的交往行为。
2.贝克(Beck)的认知疗法
贝克的认知疗法认为,人们如何感觉和行动取决于他们如何感知和建构自己的经验,要想理解某种具体的情绪体验或困扰的实质,就必须关注个体对不良事件的想法、假设和信念。同时,他认为个体关于事件的认知是多层次的,存在“认知结构”,从表面到核心依次为自动思维、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
贝克认为改变功能失调的情绪和行为的最直接方式就是修改不正确的、功能失调的思维。咨询师教给求助者如何通过一种评价过程来确认这些歪曲的、功能性的认知,尤其是那些消极的自动思维。然后治疗师开始训练他们用现实来检验这些自动思维,并评估和修正其自动思维及背后的中间与核心信念。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师的注意力放在求助者没有意识到的思维和信念体系的障碍性偏差上,通过矫正这些认知偏差来改变来访者的情绪和行为。
后来贝克进一步提出了五种具体的认知治疗技术:(1)识别自动化思维,这种思维往往是患者意识不到的、在出现不良情绪反应以前就存在的思想;(2)识别认知性错误,指患者在概念和抽象性上常犯的错误,如任意的推断、过分概括化、全或无思维等,这些错误比自动化思维更难识别;(3)真实性验证,即将患者的自动性思维和错误观念视为假设,然后鼓励求助者在严格设计的行为模式或情境中对这些假设进行验证,这一过程是认知疗法的核心;(4)去中心化,咨询师通过创设交往情境,引导和帮助患者记录他人不良反应的次数,通过客观事实让患者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别人注意的中心;(5)忧郁或焦虑水平的监控,鼓励患者对自己的忧郁和焦虑情绪加以自我监控,让患者意识到情绪有一个开始、高峰和消退的过程,人的焦虑水平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从而增强患者信心。[7]
3.自我指导训练
梅臣鲍姆(Meichenbaum)认为个体的自我陈述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其行为,求助者必须注意自己是如何想的、如何感受的和行动的以及自己对别人的影响,这是行为改变的先决条件。要发生改变,求助者就需要打破行为的刻板定势,才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评价自己的行为。梅臣鲍姆也认为痛苦的情绪通常来源于适应不良的想法,但是与REBT不同的是,自我指导训练更注重帮助求助者察觉他们的自我谈话。
自我指导训练治疗过程包括教会求助者进行自我表述以及训练他们矫正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他们能更有效地应对所遇到的情境。自我指导训练包括三个阶段:第一,自我观察,这一过程主要是求助者学习如何观察自己的行为,尤其是适应不良的行为,要让来访者愿意和有能力自我倾听。第二,开始新的内部对话,引导和帮助来访者察觉他们的自我谈话,鼓励来访者将他们的内部对话外化,然后改变这些内部对话对他们自己的指导作用。通过增加对适应性自我对话的应用,使社交焦虑患者消极的自我对话内容变得积极,能够识别和处理对自己的负性判断。第三,学习新的技能,教给求助者一些更有效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应用的技能,并且观察和评估它们的结果。
此外,治疗师还要鼓励患者经常使用正性的自我表达和评价陈述,并使用积极的自我指导来促进自己的社交表现。
(二)行为疗法
无论是经典条件作用原理还是操作性条件作用原理都认为,强烈恐惧和焦虑的过敏反应是求助者习得的结果。按照行为主义的解释,求助者最初产生社交焦虑是因为在特定的社交场合对与人交往感到不能应付、不能控制时发生的。由于条件刺激的泛化作用,其他与最初社交刺激没有明显联系的情境也能诱发社交焦虑,这就形成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8]。因此,个体可以通过学习来消除已习得的不良或不适应行为,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所缺少的适应行为。常见的行为疗法有:暴露疗法、社交技能训练和应用性放松。
1.社交技能训练(SST)
社交技能训练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社交焦虑干预手段。其理论假设来自两方面:一是儿童青少年之所以表现出社交焦虑,是因为他们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技能,如果帮助儿童掌握这些技能,就可以有效改善社交焦虑(Greco & Morris,2001)。另外,也可能由于社交焦虑患者回避社会交往,从而缺乏社交技巧,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对社会交往的恐惧,形成了恶性循环。通过进行社交技巧训练,可以帮助患者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建立友谊,从而打破这种恶性循环。[9]
社交技能训练主要是对言语、非言语沟通手段及情绪表现和识别能力进行培养,让社交焦虑患者学习和掌握一些应对社交恐惧的基本社交技巧。具体内容包括如何积极倾听,如何开始、继续和结束谈话,如何提出和回应他人的批评与拒绝及如何表达情感和观点等。常用的社交技能训练方法有示范、练习、指导、小组讨论、反馈与强化等。社交技能训练的具体内容和开展形式在不同研究中各不相同。但无论具体训练程序如何,都要包含两点:一是直接教授社会技能,并经常提供练习机会;二是当个体正确运用这些技能时,要给予及时强化(Christensen,Young & Marchant,2007)。
2.暴露疗法
暴露疗法是建立在行为理论基础上的,是用来治疗恐惧和其他负性情绪反应的一类行为方法。暴露疗法认为条件性焦虑是社交焦虑症的根源,是习得的反应,重复的暴露练习可以使个体逐渐适应或减轻对社交情境的焦虑程度。它通过严格的环境控制,引导求助者进入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情境中,使之逐渐耐受并适应的治疗方法。暴露疗法的实施程序包括:首先,让患者暴露于能引发其焦虑的社交情境中,让患者不回避自己的痛苦而进入所恐惧的情境并坚持下来,以使其体验到的焦虑自然缓解(习惯化);其次,暴露提供给患者一个机会,练习一些社交情境中所需要的行为技巧;最后,暴露可以让患者检验他们的非理性信念是否真实。
(三)认知行为治疗(CBT)
认知行为疗法(CBT)被证明是用于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最好的心理治疗方法,其疗效优于单独的认知治疗、教育支持治疗和药物安慰剂。它包括很多不同的技术,如应用性放松和社交技能训练等。其理论假设焦虑中有认知、情绪和行为三个成分,认知过程决定着行为的产生,同时行为的改变也可以影响认知的改变。认知和行为相互作用的关系在一些人身上常表现出了恶性循环,即错误的认知观念会导致不适应的情绪和行为,而这些情绪和行为也会反过来影响认知过程,给原来的认知观念提供证据,使之更加巩固和隐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10]
认知行为疗法的具体治疗策略如下:(1)介绍社交焦虑认知行为模式和治疗原理,让患者认识到焦虑是一种正常的情绪体验,是健康的反应;同时,还要帮助患者了解社交焦虑障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暴露练习的机制及其如何进行。(2)进行低生理唤醒和身体症状的放松训练,如肌肉群、呼吸的调整和放松。(3)认知重组,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情绪问题源于自己的认知建构方式,学会用正确、理智的观念来代替头脑中不现实和非逻辑的认知。(4)针对社交回避行为进行系统的分级暴露训练。通过让社交恐惧症患者暴露于引发焦虑反应的情境,使其运用已经学会的交往技能、放松技巧和认知策略。(5)进行在学校和家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社会技能训练。(6)进行提高应激能力的意外事件管理训练。(7)进行在家中和学校的巩固训练,制定详实的防御计划并将治疗中习得的技能概念化形成系统的结构以应对未来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在治疗结束之前,治疗师还将采取一些措施,以帮助患者应对可能的复发,包括再次评估患者症状,确定对于患者而言的“危险”情境,逐步减少指导,让患者制定一份自助计划。[11]
另外,诸多研究证明,家庭环境与社交焦虑的病因和症状的持续时间有很大关系,父母的一些做法和态度会导致儿童回避社交活动,父母的焦虑障碍会妨碍儿童社交焦虑治疗的进展[12]。因此,在社交焦虑的心理治疗过程中,父母的参与也很重要。治疗师要鼓励社交焦虑患者的父母改善自己的行为,并就如何引导儿童交往对父母进行培训,以改善他们对孩子症状的不良影响。父母还要注意在儿童的成长早期用心照顾和抚养孩子,建立安全的亲子依恋;尊重和关爱孩子,及时满足孩子心理和情感上的需求,培养儿童对人际交往的信任、勇气,以预防和减少社交焦虑障碍的产生。
参考文献:
[1]卡尼.儿童行为障碍个案集[M].孟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20.
[2]Beidel D C,Turner SM,Morris T L.Psychopathology of childhood social phobia[J].J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1999,6:643-650.
[3]La Creca AM & Lopez N.Social anxiety among adolescents:linkages with peer relationships and friendships[J].J Abnorm Child psychology.1998,2:83-94.
[4]郑海燕,张姝.儿童社交恐惧症的评估与治疗[J].中国特殊教育,2005(12):75-78.
[5]BarlowD.H. & Durand,V.M..异常心理学[M].杨霞,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6]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分会.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7]郭念锋.国家职业资格培训教程心理咨询师(二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7):93-95.
[8]江光荣.心理咨询与治疗[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211.
[9]李元吉,汤宜朗.社交焦虑障碍研究进展[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1(15).
[10]许若兰.论认知行为疗法的理论研究与应用[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6,4(14):64.
篇2
1 心理社会治疗
1.1 各种心理社会疗法的共同点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治疗进行系统研究,回顾相关方面的文献发现,各种治疗方法都有以下四个共同点:(1)各种治疗方法几乎都是行为治疗与认知行为治疗的变式,虽然也有些关于心理动力疗法的报道,但没有对其疗效进行对照性研究,因此我们主要讨论认知行为疗法各种变式的疗效;(2)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治疗方法本质上都是对成人社交焦虑干预措施的修改,但其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及干预措施都基于青少年这一年龄阶段的发展特征;(3)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研究是针对那些符合SAD或回避性障碍诊断标准的患儿进行的,大部分的研究其被试都是几种焦虑(如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及广场恐怖症等)并存的患儿,以下主要回顾文献中关于前者的报道;(4)除两个研究外[3,4],其它研究均为治疗组与非随机对照组而不是替代性治疗组或安慰剂组进行的对照研究。以下主要回顾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心理社会治疗所展开的研究。
1.2 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心理社会治疗方法简介 到目前为止,有两种针对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干预措施,即儿童团体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for adolescents:CBGTA)和儿童社会效果治疗(socialeffectiveness therapy for children :SETC)。这两种治疗方法都是模仿成年人社交焦虑障碍的治疗方案建立起来的,其共同点都是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并且都需要对儿童进行社交技能的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在两种治疗方案里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也是治疗社交焦虑与其它焦虑的差别所在。
在CBGTA的治疗方案里,社交技能训练包括给儿童传授一些细节性的社交技巧,例如,怎样接受他人的表扬,怎样提问,怎样变得自信,怎样识别合作者的情绪并做出适当的反应等等。CBGTA社交技能训练中的创新性成分是在每阶段的训练过程中使用"快餐打断"(snack break)式进行"微量暴露练习"(miniexposure exercises),即不仅要求儿童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吃快餐,而且在吃快餐时还经常被打断,通过这种方式来介绍与加强各种社交行为。
SETC是专门为青春前期的儿童设计的,社交技能训练除了传授一些类似于CBGTA社交技巧外,其创新性在于增加了一种"同伴共同参与计划"(peer generalization programming)的活动,即在同一个社区里的社交技能好的同伴也和社交焦虑障碍儿童一样参与计划好的活动,这就给患儿提供了一个模仿适宜行为的机会,并且学会友好地对待同组的成员。在每次社交训练结束后,接下来让其在自然情境中通过进行有趣的小组活动如打保龄球、钓鱼等,使他们有机会与内心羡慕但又回避与之交往的儿童进行交往,从而使他们逐渐社会化。
1.3 有关儿童认知行为团体治疗和社会效果治疗疗效的研究 Albano(1995)等[5]对5名患儿进行治疗,年龄为13~17a,治疗以小组形式进行,共16次,其中4次有选择性地安排一些家庭成员参与,前2次主要是给儿童与父母讲解社交焦虑障碍的性质、维持其症状的因素及治疗过程;在第8次治疗中,儿童与父母都参与一次关于家庭因素在维持SAD中的作用的交流训练;第15次治疗中,父母观察儿童在暴露任务中的表现,并且交流他们对治疗的期望及在本次治疗中的收获。治疗后,虽然没有临床资料显示其疗效,但是,经3mo的治疗,80%的SAD患儿症状显著减轻;1a后,所有儿童不再符合SAD诊断标准,1名儿童症状明显改善;并且,父母与儿童本人也报道其积极情感增加,人际关系质量提高,经过治疗后全部被试的身体健康状况均有所改善。
Hayward(2000)等[6]以35名符合SAD诊断标准的女性青少年为被试,把她们随机安排到治疗组(12名)与非治疗组(23名)。结果发现,通过儿童与父母诊断问卷调查表明,治疗组与非治疗组相比,治疗组45%的儿童不再符合SAD的诊断标准,而在非治疗组只有5%。并且在单相重型抑郁症的治疗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治疗组只有18%的儿童符合重型抑郁症的诊断标准,非治疗组却有41%。虽然研究结果表明CBGTA是很有前景的方法,但1a后,治疗组与非治疗组符合SAD诊断标准的人数却没有显著性差异(40%和56%),用成人社交恐怖症、焦虑症调查表(SPAIA)评定其平均得分分别是96.4与99.2。
以上两个研究表明,CBGTA对治疗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是有效的,不但使SAD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而且情绪障碍、其它焦虑障碍以及所有被试的身体健康状况都有明显改善。但是疗效的维持只有在Albano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因此,在CBGTA的治疗方案里必须注重加强疗效的巩固方案,有研究者也正在进行相关的工作。
Beidel[7]等人进行了对照性研究,比较了SETC组和其它治疗组的疗效,他们以67名8~12a的儿童为被试,这些儿童均符合SAD的诊断标准,把他们随机安排到SETC组或其他治疗组,其他治疗组在会谈次数及时间、治疗师的接触、社会暴露任务等方面与SETC组基本匹配,不同的是SETC组进行的是个性化治疗(the inpidualized nature of SETC)。结果发现,在SETC组,67%的儿童不再符合SAD的诊断标准,但在其他治疗组却只有5%。并且用儿童社交恐怖症、焦虑症调查表(SPAIC)评定,两者的差异也非常显著(53%和5%)。在进行6mo的治疗后,SETC组85%的儿童不再符合SAD的临床标准,且儿童本人、父母及其他评定者都认为患儿的社交表现明显提高。
以上的研究表明,SETC的疗效不仅是长期的、显著的,而且该研究还排除了其它非特定因素的干扰,其结果是可信的。因此,对青春前期的社交焦虑障碍儿童而言,SETC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仅仅由一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进行相关的研究。
1.4 研究的改进与创新 通过广大研究者的努力,对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心理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相关的研究还很少,得出的结论也有限,对于将来的研究应着重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团体治疗方式与个别治疗方式进行对照研究,以便确定最理想的治疗模式;(2)通过研究确定治疗以多少次为最佳;(3)各种治疗方法中的治疗要素对疗效的影响因素;(4)同伴共同参与计划的治疗方法有较好的疗效,其优点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的研究。
另外,在以上所报道的研究中,对疗效的评估还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创新:(1)在模棱两可的社会情境中评估儿童、父母及家庭成员的问题解决策略;(2)让儿童写两周有关自然情境中社交活动情况的日记;(3)对儿童的自信与亲社会行为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评估。通过以上多种方法对治疗效果进行综合评估,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SAD的干预措施能否推广。
最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还可以尝试采用以下手段对疗效进行评估:采取经验取样法(如电子日记)对社交活动、消极或积极的情绪的趋势进行定性定量评估;采用实验室实验法评估某些社交技能,如笑、自我揭示的互惠等;把评估纳入"积极心理学"体系中,构建诸如幸福、善良、勤奋等人格特质。
2 心理药物治疗
目前尚缺乏针对儿童或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进行药物治疗疗效的总结性研究。Birmaher(1994)等人[8] 的开放性试验表明,SSRI对治疗有多种焦虑障碍的儿童方面有较好的疗效,但是因其结果不是针对特定的焦虑障碍的,因此对青少年来说是否有同样的结果不能从资料中得以证实。Mancini(1999)等[9]报道7例有广泛性社交障碍的儿童(7~18a)应用帕罗西汀进行治疗,收到了较好的疗效。总之,这些结果指出,SSRIs对于儿童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疗效还应通过双盲试验、安慰剂试验等对照研究来进行证实。
由于没有对照性研究来证明药物治疗对儿童青少年广泛性社交焦虑障碍的疗效,对许多儿童病例,儿童精神学家只能求助于成人的标准来进行推断,因此以往研究的意义也很有限。对成人社交焦虑障碍的研究提示,MAOI类、氟西汀和其它SSRIs类药物治疗成年人社交焦虑障碍有效。尤其是SSRIs类药物是治疗成年人社交焦虑障碍较有效的第一线药物。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在使用药物治疗儿童社交焦虑障碍时还是必须谨慎,主要基于以下理由:首先,Kearney(1998)等[10]发现,在对有各种焦虑障碍儿童(主要是强迫症与厌学症)进行药物治疗的回顾中,大部分的研究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使用心理治疗作为辅助治疗,由于各种障碍与各种治疗方法交叉在一起,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的共同效果;其次,对成年人进行精神病学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何程度上可以推广到儿童青少年,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均未知。因此,一般认为,药物治疗不应被用作儿童焦虑障碍的唯一干预措施,而是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但是,还没有研究比较药物治疗、心理治疗以及这两种联合治疗中究竟哪种治疗方法对治疗社交焦虑障碍更有效。Heimberg(1998)[11]等最近以有社交焦虑障碍成年人为研究对象,比较了苯乙肼与安慰剂,认知行为治疗与"安慰剂"(支持性心理治疗)的疗效,结果发现,治疗12w后,通过多种评估工具的测量,两个治疗组均有同等的作用,均显著优于安慰剂组。这些研究都在探讨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及联合治疗的疗效。
3 结语
尽管目前对青少年社交焦虑障碍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是初步的,所进行的研究也很有限,但毕竟已经引起人们的研究,尝试深入了解这种障碍的病因学、症状学、流行病学,试图提高诊断及评估的正确性,从而开展有效的治疗。以后应进一步进行各种方法、疗效的对照研究,采取各种评估方式对治疗结果进行评估等,这将有助于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进一步理解和更有效的治疗,从而提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参考文献
[1] 李元吉,汤宜朗,蔡焯基.社交焦虑研究进展[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3):184
[2] Heimberg R G, Stein M B,Hiripi E,et al.Trends in the prevalence of social phobia in the United States:A synthetic cohort analysis of changes over four decades[J].European Psychiatry,2000,(15):29
[3] Beidel D C,Turner S M,Morris T L,et al .Psychopathology of childhood social phobia[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1999,(38):643
[4] Silverman W K,Kurtines W M,Ginsburg G S,et al .Treating anxiety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group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99,(67):995
[5] Albano A M,Marten P A,Holt C S,et al.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reatment for social phobia in adolescents:A preliminary study[J].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1995,(183):649
[6] Hayward C, Varady S,&Albano A M,et al.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for social phobia in female adolescents: Results of a pilot sthdy[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2000,(39):1
[7] Beidel D C,Turner S M, Morris T L. Behavioral treatment of childhood social phobia[J].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91,(22):205
[8] Birmaher B,Waterman G S,Ryan N, et al.Fluoxetine for childhood anxiety disorders[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1994,(33):993
篇3
关键词:大学生 社交焦虑 认知行为治疗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anxiety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作者简介:张瑾(1980-),女,江苏盐城人,江苏省盐城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心理咨询师,硕士。
一、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治疗
社交焦虑障碍个体有大量的自动想法,其中大部分具有自我贬抑的性质。对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治疗将认知重构技术和暴露疗法整和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治疗中。其具体过程为:(1)在第一、二次治疗中,治疗师对暴露、认知重构和家庭作业进行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并练习认知重构技术;(2)治疗师领导病人,完成个体化的暴露,在暴露开始前和开始后都在治疗师指导下进行认知重构的练习;(3)在每次治疗的最后,治疗师和病人确定要完成的家庭作业(包括家庭情境的暴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认知重构)[1]。
二、案例研究
男,20岁,大学生,没有,没有躯体残疾。没有心理咨询或者药物治疗的经历。
主诉:和别人在一起时感到很不自在,脸红,沉默,总感到别人在用挑剔的眼光看自己,对自己评头论足。喜欢独处,独自在校外租房子住。前来做心理治疗的目的:消除恐惧心理,能够自然地与他人相处。来访者低着头,极少与治疗师有目光接触,回答问题非常简短。根据DSM-IV的诊断标准,该患者被诊断为社交焦虑。
分析:造成来访者严重症状的核心认知是他认为自己脸红,没有话说,别人在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自己。由于有这个非理性的认知,患者感觉焦虑,采取回避行为,喜欢独处。这是治疗中需要进行纠正的认知和行为。
(一)第一阶段(第1次、第2次会谈)
向患者讲述有关社交焦虑的知识,包括患病率、症状表现、治疗疗效、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等,并初步学习认知重构技术。来访者表现出明显的紧张,脸红,回避目光接触。在家庭作业中,来访者反复提到其自动想法与在别人面前暴露焦虑有关,比如“脸红了”,“他们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二)第二阶段(第3次~第5次会谈)
在第3次会谈中,治疗师向来访者讲述暴露练习的方法和重要性,以使他对即将开始的治疗方法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在第4次会谈中,治疗师对来访者进行了第一次暴露治疗。治疗师选择一个与治疗目标相一致的情境,引发其中等程度的焦虑,而且来访者对此情境能够处理得比较好。来访者要与一位同学进行一次20分钟的交谈,交谈内容主要关于他们的一位老师。治疗师教会来访者使用情绪监控表,记录暴露练习中自己焦虑的情绪变化。家庭作业是每周至少让自己在感觉有中等焦虑的情境中与他人交谈,每次20分钟以上,每间隔5分钟记录自己的焦虑水平。
来访者向治疗师详细地介绍了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他感到自己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对情绪的焦虑转移到完成任务上来。随着暴露时间的推移,焦虑水平正在降低,但总体上焦虑感依然存在。
(三)第三阶段(第6次、第7次会谈)
治疗师设计了一个对来访者有些难度的情境,要求来访者和两个同学交谈至少30分钟。这个情境要求来访者能够在随意性的情境里插得上话,而且这个情境结构性不强,话题不确定。来访者报告了其自动想法:我没有什么话可说。
治疗师:“你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自动想法“交谈中我要一直有话说”?
来访者:“是的,如果停下来,我就觉得是我的错。”
治疗师:“难道谈话只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来访者:……(沉默约1分钟)“不,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们也有责任的。”
治疗师:“那么你在这当中的责任有多大?”
来访者:“三分之一。”
来访者表示出明显的轻松,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家庭作业是每周至少和身边的人交谈2次,每次至少30分钟,记录自己焦虑的情绪变化,对非理性自动想法进行分析。
(四)第四阶段(第8次会谈)
总结和结束阶段,来访者认为治疗使他增强了与人交流的信心。治疗师强调,每个人的头脑中都会出现一些自动想法,关键是要把这些自动想法拿出来当成假设去检验。2周后进行问卷测试,以防止“蜜月效应”。
三、问卷评估
采用交往焦虑量表(IAS)、自动思维问卷(ATQ)、 UCLA孤独量表(UCLA LonelinessScale)对来访者进行问卷测试。从测试的结果来看,认知行为治疗有效地改善了其症状。(见表1)
四 讨论
认知行为治疗有效地减缓了社交焦虑大学生的焦虑体验,改变了消极的思维习惯,降低了孤独感。治疗的关键在于动摇和重建来访者的非理性信念 。在治疗过程中,教会来访者认知行为治疗的基本原理,即要把使自己焦虑的自动想法当做是一个假设来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教会来访者一些常用的方法,比如A-B-C三栏表等,以使来访者有更多的主动性,在治疗结束以后,可以继续使用这些方法处理以后会面对的问题。
本文的案例表明认知行为疗法能够有效改善社交焦虑大学生的焦虑水平,未来还需要更多的治疗案例和实验研究来进一步揭示和提高认知行为疗法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患者的疗效。当然,也不排除来访者可能受到了情境性因素的影响。至于短期的治疗能否使来访者在消极的思维习惯、孤独感等方面发生改变,还有待我们进行长期的疗效考察。
篇4
本文采用认知行为团体疗法对高一社交焦虑学生进行干预实验,以探索降低高一学生社交焦虑的有效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苏州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年级学生为被试,共501人,其中男生264人,女生237人,平均年龄16岁,按照极端分组法,选取在社交焦虑量表(总分24分为高社交焦虑者)上总分最高的27%为被试(其他两个量表的得分作为参考,在惧怕否认评价量表上总分接近或等于60分,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上总分接近或等于28分者),再进行访谈抽取被试,并把被试随机分为实验组(6人)、自学组(6人)和对照组(6人)。
1.2干预方法
实验组采用暴露演练(角色扮演)、认知重构、家庭作业三种方法。共干预12次,每周一次,每次2.5小时;自学组采用自学认知行为疗法材料的形式,每周发一次自学材料,共发放12次,每周五下午上交自学作业;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
1.3工具
1.3.1 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ubscale of the self-consciousness scale)[1] 共6个条目,按0-3级记分,得分为0表示焦虑程度低,24分表示焦虑程度高。
1.3.2 惧怕否认评价量表(fear of negative evaluation scale, FNE)[2] 共30个条目,采用1-5级评分,得分越高,体验到更高的焦虑并更多地为可能的否定评价而烦恼。
1.3.3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ocial avoidance and distress scale, SAD)[3] 共28个条目,分为回避和焦虑两个分量表。采用1-5级评分,得分越高,回避及苦恼程度越高。
1. 4统计方法 采用平衡组实验设计。干预分前测(2006年9月14日)、认知行为团体疗法干预和后测(2006年12月25日)三个阶段进行。延时后测于2007年4月25日进行。进行t检验和方差分析。鉴于本研究被试例样过少,统计检验有阳性结果,但统计错误的可能性大,所以没有列出检验值。
2 结果
前测结果显示三组具有同质性。经过三个月干预实验,实验组的社交焦虑水平有降低趋势,自学组在惧怕否认方面有所降低,延时后测显示,实验组的社交焦虑水平相对于其他两组有降低趋势,见表1。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行为团体疗法的干预降低了高一学生的社交焦虑水平,进一步的延时后测也显示干预效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说明认知行为团体疗法的干预对降低高一学生社交焦虑水平的效果并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持续的;而自学方法单一,不适应学生实际状况和社交焦虑的复杂性。
以往研究[4-6]大多是针对成人与大学生的,而专门针对高中生进行的认知行为疗法的团体干预少见。本文以系统的认知行为理论与社会学习理论为基础,在前人干预大纲的基础上,运用了认知行为团体疗法的典型方法,并且把认知行为团体干预的对象扩大到了高中生。同时,在实验设计上补充了以往认知行为团体疗法干预的单一模式。这样结果更具有对照性。但本文存在以下局限:(1)在实验设计上考察的内容较为单一,只考察学生社交焦虑水平的降低与否,没有考察存在社交焦虑的学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是否随焦虑程度的降低而更加趋于健康等方面;(2)样本量过少,结果缺乏说服力;(3)实验过程中干扰因素较多,如学校日常教学和活动的安排以及家庭等因素,无法有效控制,制约了实验的效果。所以本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 马弘.社交焦虑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44-246.
[2] 马弘.惧怕否认评价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28-230.
[3] 马弘.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243-244.
[4] 张新凯,吴文源,张明园.社交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集体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上海精神医学,2005,17(4):200-202.
篇5
[中图分类号] R749.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3)02(b)-0042-03
目前各种社会压力明显增加,在临床工作中发现焦虑症是人群中最常见的情绪障碍,本院对住院的焦虑症患者进行了艾司西酞普兰片合并氯硝西泮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效果较好,现在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0年1月~2011年12月本院住院焦虑症患者共计90例作为抗焦虑治疗对象,并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入组标准:(1)年龄18~45岁,性别不限;(2)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 焦虑症诊断标准[1];(3)无重大躯体疾病现患和既往史;(4)无、酒精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5)入组前1周未接受任何抗焦虑药物治疗;(6)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14分;在治疗期间未使用除阿普唑仑的其他抗焦虑药,患者或家属签知情同意书。在上述病例中按筛选标准选取氯硝西泮注射液静脉滴注合并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的33例为研究组,采用艾司西酞普兰片治疗的32例为对照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1.2 方法
两组均使用艾司西酞普兰片(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治疗,剂量为5 mg/片,起始量为5 mg/d,1周内均加至15~20 mg/d,伴失眠患者两组均酌情给予阿普唑仑0.4~0.8 mg睡前服用。对照组给予0.9%NaCl溶液250 mL ivgtt qd。研究组同时给与氯硝西泮注射液0.5 mg+0.9%NaCl溶液250 mL静脉滴注,10 d后停氯硝安定针静脉滴注,仅给予0.9%NaCl溶液250 mL ivgtt qd。2周后两组一起停静脉滴注0.9%NaCl溶液。
1.3 疗效评价
治疗前及治疗后第1、2、4、6周末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总分 (HAMA)、副反应量表(TESS)进行疗效与副反应评分[2],并进行血、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谱、脑电图、脑TCD、心电图等检查。疗效以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总分的减分率作为主要统计指标,减分率=(治疗前总分-治疗后总分)/治疗前总分×100%。减分率≥75%为治愈,50%~74%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 25%为无效。显效率=(显著进步+治愈)/总例数×100%。
药物副反应,(1)中毒行为:意识模糊,兴奋或激越,情感忧郁,活动增加或减少,失眠,嗜睡。(2)化验异常:血象异常,肝功能异常,尿液异常。(3)神经系统:肌强直,震颤,扭转性不能,乏力,思睡。(4)植物神经系统:口干,鼻塞,视物模糊,便秘,出汗,恶心呕吐,腹泻。(5)心血管系统血压降低,头昏,心动过速,高血压,EKG异常。(6)其他:皮肤症状,体重变化,食欲减退,迟发型运动障碍。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t检验、确切概率法、χ2检验,采用Excel编写公式自行计算,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比较
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的HAMA评分从第1周末起明显下降(P < 0.05),且一直持续至治疗第6周末;而对照组HAMA评分从第2周末才开始明显下降(P < 0.01),且在治疗整个过程中,研究组HAMA评分比对照组下降明显(P < 0.01),即使未再使用氯硝安定针,其在治疗的2、4、6周末HAMA评分仍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在治疗的第1周末与其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在治疗的第1周末与其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第2周末开始与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治愈率为81.8%,显效率为90.9%;对照组治愈率为46.9%,显效率为71.9%;两组治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临床显效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2.3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对照组治疗中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分别为中毒行为(0,0)例,化验异常(0,0)例,神经系统(4、1)例,植物神经系(6、5)例,心血管系统(5、2)例,其他(治疗组食欲增加1例、减退2例,对照组食欲增加1例、减退1例),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分别有54.55%(18/33) 和31.25%(10/32)的患者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组间TE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前后进行血、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谱、脑电图、脑TCD、心电图等检查均未发现异常。两组均以口干、便秘及胃肠道反应恶心、食欲减退多见,此外,研究组还有明显的头昏、乏力,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4、5。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表明,人群中焦虑症的终身患病率13.6%~28.8%。有学者(1991年)报告在美国焦虑症的终生患病率为4.1%~6.6%,女性2倍于男性[3]。我国缺乏全国性的焦虑症调查资料,河北、浙江等省的调查显示 焦虑症的患病率为5%~7%,据此估计全国约有5千万以上的焦虑症患者。焦虑症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社交能力和学习工作能力[4]。艾司西酞普兰片为高选择性的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而对去甲肾上腺素(NE)和多巴胺 (DA)再摄取作用微弱,作为一种新上市的抗抑郁抗焦虑药,其抗焦虑的效果和不良反应报道较少[5]。目前有报道焦虑症患者自杀率在提高,要求临床快速安全地抗焦虑治疗,目前苯二氮卓类药物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缺点是效果持续时间短,不适合长期大量使用,有可能产生依赖和耐受性,以至于后期需要大剂量苯二氮卓类药物或者大量用药后也难以控制[6]。如何完美的将二者用于临床抗焦虑治疗,目前文献报道较少。
临床上三环类抗焦虑药(TCAs)或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s)抗焦虑治疗,通常起效时间是2~4周,显效时间通常需要8周[7-8]。苯二氮(BZ)类药物因其安全性和耐受性问题使其应用受到一些限制,特别不适合长期治疗。本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治疗整个过程中,研究组HAMA评分比对照组下降明显(P < 0.01 ),即使未再使用氯硝西泮注射液,其在治疗的2、4、6周末HAMA评分仍明显低于对照组。研究组在治疗的第1周末与其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对照组在治疗的第1周末与其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但在第2周末开始与治疗前HAMA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治愈率为81.8%,临床显效率为90.9%;对照组治愈率为46.9%,临床显效率为71.9%;两组治愈率、临床显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表明短期合并氯硝西泮注射液静脉滴注可以加快焦虑综合征缓解的速度,明显提高焦虑症的治疗效果。氯硝西泮注射液的主要副作用为嗜睡、头昏、乏力、共济失调等。据报道少数病例会出现激越不安、兴奋、攻击行为或者抑郁发生[9]。本组研究未发生这一现象,可能与本组样本相对年轻和使用药物剂量小有关。两组在治疗过程中分别有54.55%(18/33)和31.25(10/32)的患者出现各种不良反应,组间TESS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随氯硝西泮注射液用药时间的延长或者静脉给药的停用,有些不良反应能逐渐耐受消失,只需对症处理,不影响治疗。两组均以口干、便秘及胃肠道反应恶心、食欲减退为多见,研究组第1~3天还有明显的乏力、嗜睡、头昏,但是很快适应,第1周末两组TES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其发生率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前后进行血、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心肌酶谱、脑电图、脑TCD、心电图等检查均未发现异常。说明艾司西酞普兰片副反应小,同时也说明短期小剂量给予氯硝西泮注射液静脉滴注抗焦虑非常安全,且氯硝西泮注射液停药后无反跳或者戒断症状,实现了单用艾司西酞普兰片长期抗焦虑平稳的过度。
综上所述,短期合并氯硝西泮注射液静脉滴注可以加快焦虑症状缓解的速度,明显提高焦虑症的治疗效果,副反应没有明显增加,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 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 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05-107.
[2] 张明圆. 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134.
[3] 沈渔. 精神病学[M]. 4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60.
[4] Stein DJ,Berk M,Els C,et al. A double blind placebo cont rolled trial of paroxetine i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phobia(social anxiety disorder)[J] . South Afrian SAfr Med,1999,89:402-406.
[5] Wagner W,Labormy BA,Gray TE. Escitalopram:Areiew of its safety profile in worldwide studies[J]. International Clinical Psycho pharmacology,1994,9:222.
[6] 张心保,刘玉成,林其根,等. 氯硝安定治疗焦虑症100例[J]. 江苏医药,1992,18(5):287-288.
[7] 汪春运. 广泛性焦虑症的治疗进展[J]. 四川精神卫生,2011,24(4):25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