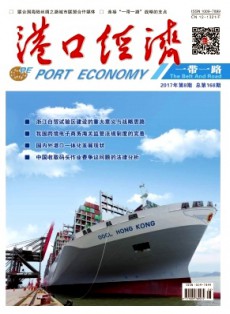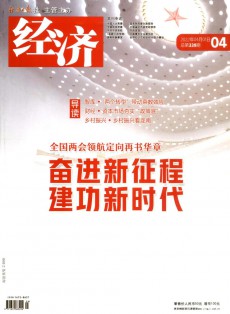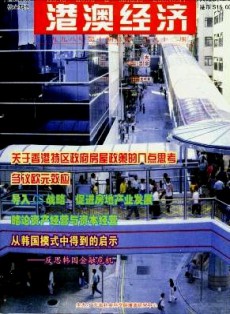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文
发布时间:2023-11-30 11:16:56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0010);扬州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ZS038)。
作者简介:陈 杰(1980-),男,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扬州大学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安 源(1986-),女,山东泰安人,扬州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3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5-0132-05 收稿日期:2011-09-2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体制转轨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总量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而经济周期波动则呈现不断缓和的态势。那么,体制转轨在促进经济增长、平抑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体制转轨的根本问题就是非国有部门的成长与国有部门的改革(樊纲,200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制变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国有制经济比重下降而非国有制经济比重上升。这种体制变迁的过程与市场化的进程、要素使用效率尤其是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年均经济增长的高速水平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展示出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上的合理性(刘伟 等,2002)。经济周期性波动根源于经济体制本身(张连城,2006)。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主体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转轨型波动特征不断消失的同时,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特征逐步显现出来(雎国余 等,2005)。从现有文献来看,
虽然有研究涉及了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中体制性问题的分析,但尚不够深入;尤其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学者使用数理模型来解释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同时实证研究方面也缺乏一个完整、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建立一个数理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周期波动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
一、理论模型
(一)前提假设
1.体制转轨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2.鉴于我国经济的投资驱动型特征,不同所有制企业经济活动波动程度的变化由各自企业投资活动的变化加以描述;所有制结构的变动用政府投资或民间投资①在总投资中比重的变化加以描述。
3.假设存在三部门经济,这时国民收入Y由三个支出流组成: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于是有Y=C+I+G。
4.消费C被看做是收入Y的函数,且有C=cY。其中c为边际消费倾向,0
5.一国投资I被分成政府投资Ig和民间投资In两部分,于是有I=Ig+In。
6.民间投资In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增加,即In=I2+k2ΔY。其中k2为民间投资加速数,k2>0。
7.政府支出被视为外生变量,即G=G0。
8.假设整个经济社会中有m家国有制企业和n家私有制企业,所有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m家国有制企业在相同的政策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冲动,因此各家国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g,从而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政府投资变动为mΔig;n家私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条件下具有一致的投资倾向,因此各家私有制企业均有相同的投资变动Δin,从而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即民间投资变动为nΔin。
(二)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
当经济过冷时,政府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政府就会减少投资,从而遏制总需求的过快扩张,使经济降温。因此,政府投资与经济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政府投资的决定可以用方程(1)表示
Ig=I1-k1(Y-Y*) (k1>0)(1)
由方程(1)可知,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由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的偏离决定。由于政府投资存在着相机抉择,从而政府投资变动的方向与实际产出对潜在产出偏离的方向相反。政府投资变动的大小与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密切相关。政府投资调整系数在微观层面反映了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政府调控的模式。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小,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小;政府调控模式越是“微调化”,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小。相反,政府投资调整系数越大,表明国有制企业的投资冲动越大;政府调控越是“大起大落”,政府投资的变动也就越大。
(三)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过程
根据前提假设、政府投资的决定过程,扩展后的萨缪尔森“乘数-加速数”模型可以用方程组(2)来表示
Y=C+I+G0I=Ig+InIg=I1-k1(Y-Y*)In=I2+k2ΔYC=cY(2)
整理方程组(2)后可以得到方程(3)
ΔYY=1k21-c-I1Y-I2Y-G0Y+k1k2?(Y-Y*)Y (3)
篇2
中外经济发展史的历程无可辩驳地表明,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会出现周期性波动的。对于经济周期的成因及其作用机理,西方经济学家从许多方面都进行过研究。其中, 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一同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可以看作近20多年来在经济周期研究方面的重要突破,这两位经济学家也凭此而折桂200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其核心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理论源流和明显的现实背景。首先,由理论来源分析,一是在20世纪80年度之初,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波动理论及其模型遭到普遍的质疑;二是理性预期与公众选择理论被吸收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Lucas由方法论角度探讨了经济波动问题;三是C. R. Nelson与Charles I. Plosse提出,实际因素对于形成经济波动的作用比起货币等虚拟因素来重要得多;四是一系列分析方法与分析工具的问世,也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建模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其次,由实践发展的层面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体现了供给方面的因素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但自三十年代一直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却对当时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束手无策,而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信奉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对于治理经济却颇见成效,这也成为催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实践佐证。再者,由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自身演进过程来分析,20世纪70年代之前,在经济周期研究领域一直是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到十年之后的八十年代,该领域中主导性的观点仍然认为经济周期的主要产生根源在于需求方面的扰动。后来,鉴于Lucas货币周期理论的引领,经济周期问题,又重新进入相关研究人员的视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因素对于经济周期的作用开始引起经济学家的重视。Finn Kydland与Edward Prescott首开先河,后来通过Kydland和Prescott以及Plosser等人的工作,外来的实际冲击因素被引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的模型,此处引起经济周期的主要解释不再是需求因素或者金融货币等虚拟因素,而是实实在在的外来技术冲击。这就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旨,它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外来的实际因素的扰动(如技术方面的冲击)是导致产生经济周期的根本原因。按照赞成实际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周期的成因不在于经济体系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因素,来自于一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像是技术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变化造成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变动,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和其他生产要素价格相应的变动,从而使得产出水平和生产发展方式也随之出现不同于往常的变动,经济机体本身对于这种意外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只能随之变动,于是就产生了经济周期的高涨或者衰落。
其次,经济变动的主要传递渠道是劳动提供方面的延递性变动。其中的内在运作机理是这样的;每当外来的技术方面的变化导致劳动生产率、要素价格等因素变动的时候,符合“经济理性人”假定的市场主体就会根据自己对市场走向的预期,在工作与享受闲暇之间做出选择,这样就会在劳动供给方面产生极大变动,进而使社会就业和总产出也随之产生变化,而且一次技术变动带来的产出变动可以是持续性的。同时,鉴于相关经济门类之间的联动效应,产生在一个部门的技术扰动也可能会导致其他社会生产部门乃至于宏观经济形势产生变动。.
再者,经济周期本身就体现了经济趋势在发生变动,而并非经济形势围绕着经济趋势这一轴心在变动。换言之,并非经济运行背离了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而是经济本身的均衡位置在变动,这就将周期理论与增长理论糅合为一体。根据这种观点,经济发展无所谓长期、短期,经济形势的短期变化与长期发展趋势二者之间并不矛盾,经济的短期变动并不是背离了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
另外,管理当局针对经济周期所采取的反向操作措施没有任何作用,换句话说,当局管理经济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根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经济波动乃是市场主体对于外来扰动的理性反应,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能够使经济状况自动达到就业与产出状况合理的均衡,而人为的政策调节却难以使调节者的主观意志同经济运行结果达到一致,反而会降低社会的总福祉。所以,管理当局调节经济造成的失误甚至包括调节行为本身都属于某种负面的外来扰动,据此,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政策性结论就是:管理当局力图熨平经济波动的反周期操作是无效的。
最后,货币的作用是中性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相关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周期问题解释上的异同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轫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属于主张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战后自由主义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先是以Friedman为首的货币主义,接着是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理论,现在是以由Kydland和Prescott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为主。在经济学说史上,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理论都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革命”,理性预期理论还被称为“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打破了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和短期,以及,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凯恩斯主义各派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外部冲击”。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分开的传统作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周期理论,也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从总体上讲,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认为,需求冲击使得短期中的经济偏离长期趋势,出现经济周期,而实际经济周期理将供给方面的技术变动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这是他们的主要区别所在。具体地分析,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分野尤为明显:
1.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而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首先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的变动。相应地,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
2.凯恩斯主义各派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无需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且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会成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加剧经济的不稳定性。
3.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面的冲击;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造成经济周期产生的冲击主要是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面的冲击。
4.凯恩斯主义各学派基本上都认为市场调节机制的不完善性冲击来临后造成经济周期的原因;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经济周期波动并非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而是趋势本身的改变。因此经济周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致。
5.凯恩斯主义各学派普遍主张政府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采用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外来冲击所做出的具有帕累托效应的最优反应,政府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减轻波动,政府的注意力应该集中于技术进步率的决定因素上。
相比之下,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因而其经济周期理论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1)都认为导致经济周期产生的根源是来自于经济体系之外的因素的冲击;(2)都强调经济主体的预期在经济周期形成中的作用,正是人们面对外生冲击在一定预期下采取的经济行为导致了经济周期;(3)都坚持新古典主义信条,认为市场调节机制完善、价格调整灵活、市场会在自然率处出清(4)都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认为政府的反周期经济政策无效且会造成扭曲,政府的作用不是采用反周期政策来调节经济,而是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它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1)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将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归结为影响总需求面的货币冲击,即根源于货币数量的变动或未预期到的货币扰动,因此其理论可称为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影响总供给的技术冲击。(2)货币主义认为冲击引发经济周期是实际物价与名义物价发生错误讯号,令资源错置所致,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扰动引发经济周期是价格信息不完全所致,货币供给的过度增加使一般物价上升;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看做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对总量生产函数因受到真实技术冲击发生变化而做出的有效反应的结果。(3)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把经济周期看作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暂时偏离,认为经济波动会降低社会福利;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经济波动视为自然率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本质是统一的。而且经济周期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经济的均衡状态,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
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与其他流派共同的差异性来看,作为其对立面的凯恩斯主义者、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原则上都同意以下几方面的共识:其一,经济周期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的某种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其二,经济周期对社会来说是不合意的,因为对经济长期趋势的偏离使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其三,冲击主要是对需求方面的冲击;其四,货币因素对于经济周期十分重要。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却认为:其一,经济周期并不是对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偏离,经济波动就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本身的波动;其二,经济周期的每一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都是理性预期主体面对冲击进行最优调整的结果;其三,冲击主要是对供给面的冲击;其四,对经济周期重要的不是货币这一名义变量因素,而是技术冲击这一真实因素。正是基于以上不同看法,使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也不同于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理论突破与影响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超越了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成为与新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最主要的新自由主义流派。它完全以正统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说明宏观经济波动,是对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巨大挑战。第一,通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一起,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经济周期研究的方向,并促使宏观经济学家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经济的供给面上。第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跨时间和动态的特点。第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用特定的模型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那些由于费用太高而无法在实际经济中进行实验的政策可以在这里以非常低的成本进行实验,从而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
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之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宏观经济有一个一致的描述:在长期,经济有一个平滑的稳定增长趋势,这可以由增长模型刻画;而在短期,经济围绕这个长期趋势波动,这可以用波动理论来解释。而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
如前所述,以往人们对经济波动的解释主要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总需求分析,Solow模型中的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只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对短期经济波动则没有任何作用。同时,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对总需求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Lucas通过著名的“卢卡斯批判”和理性预期理论,最早对此提出了挑战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试图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Finn Kydland和Edward Prescott提出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在“货币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技术进步和各种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的变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将相互割离的“凯恩斯主义”和“Solow模型”中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了综合的考虑。论证了技术进步等真实因素不仅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会产生短期经济波动。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的波动原因的理解,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进而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
就方法论而言,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模型接近于实际的情况,使得模式分析及经济机制变得更为现实。Kydland和Prescott最先使用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模型来解释经济波动,以微观经济主体的偏好、技术、禀赋等假设为基础,解释商业周期的变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修正,使经济学更加向现实靠拢。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还带来了方法论上的突破,用以Ramsey模型为代表的典型微观主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开创了新的研究途径。
从否定意见来看,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还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这都是对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根本性否定。同时,实际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但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然有悖于常识,然而,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这是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一根软肋。再者,RBC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也使得一些在实际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另外,有人认为,模型只分析了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其他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欠缺考虑。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要想对经济周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必须对Ramsey模型进行扩展。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可变的资本利用率、多重冲击和劳动的调整成本作为构成实际经济周期的基本要素。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领域还出现了一种新新古典综合派,它把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相融合,将新凯恩斯主义的不完全竞争和名义黏性融入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试图从方法论上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对经济周期等问题进行新的阐释。
可以说,Kydland和Prescott的理论工具对于解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样也是非常犀利、非常有用的。尽管有人认为当前中国对冲击的市场传导机制还不够灵敏,因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作用有限,但应当承认,将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无疑也十分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再者,探讨技术因素的作用和决定技术的因素对于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险峰,著.真实经济周期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杨玉生,著.现代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3][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主编,黄险峰等,译校,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反思[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英]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等,著.苏剑,朱泱等,译. 现代宏观经济学指南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美]小罗伯特・E・卢卡斯,著.姚志勇,等,译校.经济周期模型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篇3
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周期问题一直讳莫如深。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一课题才得以展开,我国经济周期的讨论才热烈地开展起来。改革开放,尤其是1985年以来,我国学者对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兴趣大增,取得了很多成果。
1984年和1985年,我国经济超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出现滑坡,乌家培和刘树成等人最早把社会主义经济增长有没有周期波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提了出来。刘树成首先论证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同时,杜辉也发表了论证前苏联社会经济增长的长波运动和短波运动的论文。宫著铭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方法,为我国建立了一个供给模型,测算了波动指数,较为系统地论证了我国的经济波动。这场始于1985年的理论大突破,为我国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研究经济周期,首先要明确我国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几个经济周期。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划分基本上是相同的。
施发启(2000)用转折点检验和自相关系数检验的方法对经过平滑的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证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率确实存在周期性波动,而且周期长度主要为四到五年。根据从波谷到波谷可以将我国GDP增长率划分为九个周期:1953—1957年,1958—1961年,1962—1968年,1969—1972年,1973—1976年,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
刘树成(2000)的划分除了最后一个周期是1991—1998年外,其余的与施发启完全相同。
刘恒和陈述云(2003)完全采纳了上述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
有一些学者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周期进行了划分。惠琦娜(1998)认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1976—1981年,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6年。黄桂田(199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4次经济周期: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和1991—1999年。
由此可见,学者们对建国后经济周期的划分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周期长度极不规则,但是有逐渐变长的趋势;周期发生频率高。我国经济周期的长度长短不一,长的达9年(1991—1998年),短的只有4年(1958—1961年,1973—1976年),平均长度5.2年,离差为1.7年。改革开放前,我国1955—1976年按照“谷—谷”法划分的5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为4.2年,改革开放后,我国4轮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约为6年。
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周期呈现收敛趋势。振幅最大的达到48.6%,最小的也有6.4%,平均振幅15.0%,离差为13.7%。
刘恒、陈述云(2003)认为,我国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为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没有出现绝对下降,而仅仅表现为增长率的下降。这说明,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是在相当显著的波动过程中展开的,1978年前的波动标准差达到10.48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开始变得平缓起来,1978年后的波动标准差为3.01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周期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古典型转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增长型,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增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和稀缺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为主要内容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进程,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我国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在削弱转轨型波动的同时使成熟的市场经济波动逐步表现出来。
从经济周期波动的波形看,我国经济周期实现了由非对称性周期向对称性周期转变。1996年之前,我国已经实现的经济周期大都是非对称性的,即经济周期中呈现出经济增长率的缓升陡降或者陡升缓降的非对称过程。这些非对称性表明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接近或者没有稳定在自然增长率水平附近,经济增长率变化的突发性较多,即出现过经济增长的“”和“急刹车”等奇异行为。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在1996年至2002年的经济周期当中,经济增长率基本保持水平的态势,这意味着经济周期的对称性正在逐步恢复,预示着未来经济周期将以稳定的增长速度进行对称性波动。
我国经济越来越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实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日益显现。张兵(2006)以我国经济周期的划分为标准,通过计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的方法,说明了中美两国1981—1986年、1986—1990年、1990—1995年以及2001—2005年的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同步性。中美经济出现同步性的原因是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贸易和直接投资联系是同步性的基本传导机制。秦宛顺、靳云汇和卜永祥(2002)采用HP滤波的方法对不变价格水平的美国、日本和我国季度GDP进行处理,计算了中美和中日周期波动之间的相关系数,得出的结果表明,中美经济周期的联系为弱相关关系,中日经济周期的关系为负相关。但是任志祥和宋玉华(2004)认为,由于我国经济的开放度较低、汇率机制实质上是固定汇率、资本帐户实行管制再加上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相对较小等因素,中国经济周期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美国)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仍然较弱。中美经济并不存在周期性的衰退和复苏的同步性。
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
(一)投资波动
梁军(2000)认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到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影响。在这三个因素中,投资又是最直接的因素。在我国,投资是国家控制社会的经济资源、指挥经济活动的最重要手段。比如,1977年,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达到4.65%,1978年达到21.96%,有力地拉动了当年的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随后,投资增速下降,1979年和1980年只有4.58%和6.65%,到了1981年跌入谷底,投资出现负增长。198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64%,经济增长加快,投资增速其后逐年回落,1983年是12.62%,直到1985年出现投资高峰,经济回升,投资增速高达39.39%。
刘金全(2003)利用我国199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数据,研究了我国投资波动性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三个基本结论:在水平值和波动成分上,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关系,但是它们的趋势成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格兰杰影响关系,这意味着投资和产出之间仍然存在长期的均衡联系,投资波动是诱导经济周期的重要原因;投资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存在方向上的差别,存量水平上的投资率增加并未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实际产出中的投资品成分也未明显膨胀;流量成分的投资需求增加作为GDP的统计成分形成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需求仍然是扩张总需求的主要对象;投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率“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最优投资路径应该具有一定的光滑性。如果频繁地扩张投资或者抑制投资,都会具有一定的社会成本。
李延军、金浩、王竞和高素英(2003)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经济波动的成因,认为从总体经济的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波动是造成经济波动的主导力量,从社会需求来看,最终需求的增长以投资拉动为主,因此投资波动是引起经济波动的最重要因素。
(二)制度冲击
胡鞍钢(1994)利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的冲击影响,其结论认为,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经济的扩张与历次党代会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与人代会也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杜婷、庞龙和杨灿(2006)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其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三)总需求冲击
施发启(2000)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波动的原因相同。改革开放前,由于物质产品短缺,我国经济增长波动主要取决于总需求的波动。总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构成。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一直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因此总需求的波动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的波动。改革开放后,虽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总需求波动,即总需求扩张导致经济增长加速,但是瓶颈产业和高通货膨胀的约束又使得经济被迫调整,经济增长回落。引起需求扩张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工业化阶段还未完成,并且需求扩张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
(四)我国经济周期的特征事实
简泽(2006)考察了1952—1999年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统计规律性,概括出我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事实:我国经济波动具有持续性,只是到了2—3年后才表现出回归趋势的倾向;所有的变量都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波动,但波动程度存在差异,消费、资本存量、就业和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小于产出波动,而投资、政府收入、政府支出、进口、出口和货币供应量的波动远远高于产出波动;总需求的组成部分、就业和全要素生产率与产出共变,并表现出强烈的顺周期性,资本存量领先于产出的变动,而是工资则滞后于产出的波动;货币供应量和一般价格水平是反周期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事实与其基本相似,只是我国周期波动的幅度大大高于西方发达国家。
篇4
一、引言
经济周期性波动与经济的长期趋势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波动对增长的影响结论对于政府部门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由此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化经济国家的大批实体企业停产和倒闭,这不仅降低了世界整体经济增长,同时也加剧了经济波动。面对高经济波动,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例如增加政府投资、降低商业银行利息,但是,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一定会减损经济的增长吗?时至今日,金融危机的阴霾并未彻底消去,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到底存在负面影响还是正面影响?这个问题在后危机时期再次引起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迄今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并无定论。
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即“二分法”)将经济发展中的周期波动和长期增长看作为两个独立的经济现象,然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模型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波动和增长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较为明显的有两种,首先是基于“干中学”理论,认为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基于Schumpeter的“毁灭性破坏”理论则认为波动对长期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主要源于“机会成本”和“清洁机理”的存在。
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方面,Ramey & Ramey(1995)运用国家层面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经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此后,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了关于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新见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考虑波动性质,如Blackburn & Pelloni(2004)发现长期增长与实际冲击引起的波动呈正相关,而与名义冲击引起的波动呈负相关。二是考虑了数据类型,一些学者从使用加总数据转向使用分解数据进行研究,如Imbs(2007)发现尽管基于整体加总数据得到的波动与增长关系为负,但基于行业分解数据得到的二者关系却显著为正;三是通过考察不同经济体制特征来研究波动与增长的关系,如Aghion et al.(2006)发现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的关系受金融(信贷)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会使得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同。
理论上对我国经济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张运峰(2008)通过构造随机增长模型证明随机冲击的增大不仅会使产出增长率的标准差(波动)增大,同时也使增长率均值(增长)减小,这导致了在数量上表现为增长与波动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更多的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到了不一致的结论(如李永友,2006;刘金全,2005;卢二坡和曾五一,2008;杜两省,2011)。但是,这些研究都将样本期间整体考虑,而未分波动的不同阶段进行观察,而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与波动的状态有关。一些理论研究表明低的经济波动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过高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即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随着波动的程度存在非线性,Nelson(2007)的美国经验也得到当人均GDP增长率的波动率水平低于5%时,波动对增长没有显著影响,而当波动率水平高于5%时,波动对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否随着波动程度的不同也存在非线性特征?此前有学者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波动出现了平缓特征,从而以1995或1996年为界限进行阶段划分,并分阶段考察二者的关系,但是这样的划分是较粗糙的,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的高经济波动也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不再合适,鉴于此,本文主要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判断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并在不同波动阶段,波动对增长有何影响。与现有国内文献仅使用国家层面数据或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不同,本文考察了我国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
二、模型的建立
1.模型和估计方法
注:(1)此处低波动与高波动期的划分选择波动率平均值;(2)东中西部的省份划分参照国家统计局2011年的标准,竞争性行业包括除了烟草制造和石油加工炼焦外的全部制造业,共26个行业,垄断性行业包括工业行业中非制造业和烟草制造、石油加工炼焦业,但不包括其它制造业,共11个行业。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解释
1.基于加总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
本文将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寻找门槛值,并估计波动低于门槛值和高于门槛值两个阶段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2是基于全国GDP和工业增加值二者增长率序列的门槛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1)和列(3)是条件波动时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是标准差波动时的估计结果。
表2结果显示,除了列(1)外,其余三个序列F检验对应的bootstrap概率水平p值均小于0.1,表明经济波动对增长影响的回归模型存在门槛效应,在条件波动下,模型结果中波动变量系数(β1和β2)均不显著,但在低于门槛值时,均为负;在标准差波动下,β1显著小于0,而β2大于0不显著,波动变量门槛值分别为3.71%和5.27%,说明在非条件波动下,当波动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而当波动水平高于门槛值时,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这和Nelson(2007)的研究结果不同。
2.基于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外一些研究指出在研究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同的数据类型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Imbs,2007),那么,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同样存在这种现象。表3和表4的估计结果对此进行了验证,由于面板数据不易得到条件波动,在此波动只取标准差形式,其中,表3是基于地区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表4是基于工业行业分解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结果。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总经济增长率时间序列数据和分地区和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重新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不同的波动状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从全国加总GDP和加总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数据看,在低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而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分不同地区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在不同性质工业行业下,在低于波动门槛值时,竞争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负面影响,而垄断性行业波动对增长有正面影响,在高波动时影响均不显著。导致低波动时期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相反的原因是二者企业对风险的投资偏好不同。由结果我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国家,预防性储蓄观点和创造性破坏理论在目前还不成立。因此,在经济受到冲击时,必要性的政府稳定性政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避免陷入严重的衰退。此外,结合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要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的经济调节政策,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杜两省,齐鹰飞,陈太明.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稳健性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1,第4期3-12页
[2]李永友.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减损效应:中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科学,2006,第7期8-15页
[3]刘金全,付一婷,王勇.我国经济增长趋势与经济周期波动性之间的作用机制检验[J].管理世界,2005,第4期5-12页
[4]刘志铭,郭惠武.创新、创造性破坏与内生经济变迁――熊彼特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J].财经研究,2008,第2期18-30页
[5]卢二坡,曾五一.转型期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第12期10-23页
[6]张运峰.波动与增长:基于随机增长模型的认识[J].统计与决策,2008,第22期23-25页
[7]Aghion P. et al.Volatility and Growth: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Enhancing Investment[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6, Cambridge NBER Working Paper,No.11349
[8]Blackburn K and Pelloni A.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owth and volatility[J]. Economics Letters,2004, (83):123-127
[9]Hansen B.E.Inference When a Nuisance Parameter Is Not Identified Under the Null Hypothesis[J]. Econometrica, 1996, 64(2):413-430
[10]Hansen B.E.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J] . Econometrica, ,2000, 68(3):575-603
[11]Imbs J. Growth and Volatility[J].Journal of Nonetary Economic,2007,(54):1848-1862
[12]Nelson R.Nonlinear Volatility Effects on Growth in Developing Economies[R].2007, Working Papers,No.16
篇5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制造业以及服务行业之间的融合,一些新型的服务行业不断涌现出来,生产业的出现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尤其是当前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对服务业的需求逐渐增大,从而促进了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融合。
一、服务业的概述及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一)服务业的基本概念及分类
服务业通常是指生产或者是提供服务的经济部门及企业,在我国被称为第三产业,一般包括建筑业、运输业、金融业、通讯业以及政府行政行业等。
服务业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服务业的性质可以将其分为生产业和消费业,其中生产业主要是指被商品生产者用作中间投入的服务,包括交通运输业、科学服务业、农业生产服务以及现代金融等9个行业。而消费业是指满足居民基本需求的服务行业,主要包括旅游业、餐饮业、文化产业、体育行业以及政府公共服务行业等10个行业。按照服务业兴起的时间以及发展的历史可以将其分为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新兴服务业三种类别。传统服务业是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的服务行业,主要使用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为人们提供服务;现代服务业是受到工程化进程加速的影响下形成的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一种服务行业,新兴服务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服务业出现大规模的消费,使得该行业的收入弹性发生改变。
(二)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贝尔理论
贝尔理论是针对后工业化时代提出的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工业化时代相比较,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首先是产品经济向着服务性经济的转变,其次是理论知识占据中心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发展成为社会的战略资源,最后是创造性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复杂问题的处理更加简单化,使后工业社会能够有效的规划社会发展。这些理论认识对于我们认识工业化发展以及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起到了一定的指导。
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概念出现的时间是1960年,这一概念的出现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直至20世纪末,出现了总成本原理,认为总成本是制造成本以及交易成本的总和。这一原理的出现说明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成本的降低以及经济效益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工业化的发展使得分工参与者之间的交易变得更加频繁,教育范围的扩展促进教育资源的应用更为广泛。服务业对于这种交易过程中的费用处理往往是以专业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因此说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时还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流通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我国服务业的在GDP中的比重为48.2%,高于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北上广和江浙等地的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均已超过50%,甚至个别地区达到60%以上,而以广西为代表中西部地区,其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却只有37.8%。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高达80%的比重。由此可以得知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是有着相当正面的影响的。
(一)服务投资对GDP增长率的影响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形势下,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加快以及GDP的增长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年来,虽然我国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表现为发展速度快、比重增加、结构优化等特征,但是服务投资还相对不足,我国服务投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首先是服务行业的投资效率比较低,其次是服务业特别是一些细分行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力度不足,最后一点是科研和教育作为服务行业中最有弹性的产业,投资比例还相对较小,这些因素严重阻碍了国家经济增长的步伐,因此,需要不断增加在这两个各方面的投资比例,才能够有效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
(二)服务业相关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就业扩大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了经济增长效率。服务业通过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的方式加快了我国第一产业以及第二产业的发展,然后通过自身的发展状况促进了社会结构的优化。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服务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就业的机会,同时,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推动就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二产业的劳动者逐渐向服务行业靠拢,从而使得中产阶段的比重进一步提升。最后,服务业通过延长产业链以及增加产业的附加值,使得行业本身的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对服务业的发展也会起到一种反作用力,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
(三)服务业对经济增长周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