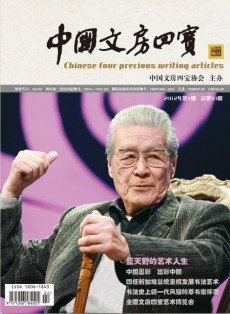雕刻艺术的意义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03 17:56:05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雕刻艺术的意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粤北客家民居梁架雕刻的布局大多由花草鸟雀、祥禽瑞兽和各种吉祥纹饰重复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排列形成了一种神秘的秩序感,这种秩序感的来源便是人们期望美好心愿可以不断延续的情感。例如 ,代表着吉祥寓意的祥云、回纹、牡丹等图案重复排列后便形成了一种富有深刻含意的形象符号,代表着粤北客家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然而,在很多民族的艺术中都有类似富有秩序的连续图案装饰,为何又能在梁架雕刻的图案中读到粤北客家人生生不息的情景呢?这又需要谈及秩序感的另一个方面。除了直观的图案连续排列,梁架雕刻还与粤北的自然风情、客家的生活习俗密切相关;那些琅琅上口的民间谚语也是促成秩序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梁架雕刻的历史发展中慢慢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审美符号,这种审美符号便是客家人内心情感相连的表达,同时也是人们对未来美好期望的精神寄托,如“连绵不绝”“事事如意”“好事不断”的美好寓意。此时,秩序感就同时产生在视觉感观上和语言表达上。客家民居梁架雕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方式所形成的秩序感不仅存在于建筑装饰中和客家人的生活中,还存在于客家人的审美趣味中。这一审美趣味如何通过雕刻手段和装饰手法传达给观众呢?这要从客家民居梁架雕刻的形态组合和构图方式来探索。比如,梁架中心位置主要是以植物茎叶或回纹等艺术元素依照横梁的直线形状组合而成,在一个特定的长形横梁中,植物的枝茎、叶片和花朵以及各种图案都需要一个恰当的组合形态,才能合理地布局在梁架上。就目前考证来看,梁架雕刻大多采用二方连续的布局组成构图。二方连续图案是一种富有条理性的排列形式,不断连续的一个元素或多个元素具有较强装饰效果,既增加了雕刻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又使得雕刻画面显得井然有序,整齐大方。此外,横梁的体积和形态本身也给雕刻带来了限制,而这种限制恰恰成就了梁架雕刻的艺术独特性,富有秩序感的二方连续构图也就成为最能突出表现其装饰内容和风格的重要造型手段。
综上所述,图案组成的二方连续结构形式是粤北客家民居梁架雕刻秩序感重要特征之一。梁架雕刻的图案是由一个或一组单位纹样向左右循环往复、无限延长的连续纹样构成,其组成形式大多是以波纹形、直线形等样式进行布局,使组成形式呈现出有规律的带状分布。这些以现实形态为基础而又超越现实的有序重复的带状组合,则恰恰是增添美感的有效方式,也正是梁架雕刻秩序感的重要表现。如在横梁的雕饰中,其图形要素是同时有几种图样组合构成,使得雕刻的纹样在一根横梁的有限空间内,形成了井然有序而又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里所说的秩序感特征不是指图案完全一致的重复和组合,而是指在多种规律关系中拥有适度变化的结构秩序。对于艺术构成形式来讲,只要求其呈现简明、秩序化的形态特征还远远不够,应在有秩序感的基础上再寻找丰富的变化,以满足更高的审美心理需求,客家民居梁架雕刻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各造型要素在相互对比和相互衬托的关系中展现出良好的组织性,使得看似繁乱复杂的组合形式,体现出丰富而又均衡有序的秩序感。由此可见,装饰图案中的多层次的秩序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丰富视觉感官的需要,更是建筑结构主体中装饰效果的需要。
二、雕刻形态的典型性
客家民居梁架雕刻既是建筑装饰,又是精神产物。梁架雕刻作为客家民居装饰的重要部分,它经过历史的洗礼而逐渐形成一种典型性,由古至今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感染力影响着居民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雕刻艺术的典型性包括题材的典型性、构图的典型性以及雕刻手法与色彩使用的典型性。
(一)题材的典型性
雕刻的题材如何体现梁架雕刻形态的典型性呢?梁架雕刻主题通常根据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和民居建筑的需要来确定。它既要符合客家宗族传统习俗,又要符合
建筑功能的要求。在内容上具有适用于粤北客家人民的相对普遍性和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寓意性;同时在表达上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取材的灵活性。例如:梁架雕刻中常常出现的由许多回纹相互连接、回环重复的图案,寓意家族存久留长、子孙生生不息;回纹中用盛开的梅花、牡丹、莲花等植物和枝叶相衬,更添长寿、富贵、康宁、好德等美好寓意,这些题材都集中反映了客家人追求家族兴旺发达、生活美满幸福的精神世界。又如:一度用于古代建筑屋脊正脊两端、有着辟邪镇火的寓意、同时也含有保佑民居安全纳福的吉祥意义的鸱吻(又称为“鸱尾”),常被客家人广泛用于梁架雕刻中。如此看来,梁架雕刻可谓客家人将民族文化与自身的生活习俗相互连接的一个典型艺术形态。
(二)构图的典型性
梁架雕刻的主题通过图案来体现,对图案元素的表现需要有高度概括、简练的雕刻手法。梁架属于特定的艺术载体,修长而狭窄 ,梁架雕刻需要在很小的范围里进行,因此,构图是否得当至关重要。要在有限的空间里表达丰富的内容,适形构图便是最恰当的表现方式。例如:在一根横梁上雕刻图案,最恰当的构图方式即直线式或波纹式二方连续的构图,在横梁的两端配以适合纹样的造型结构给予补充,方能使整个梁架雕刻看起来更加完整与端庄。总体来讲,在梁架设计过程中,艺匠们既要选料得当、因材施艺,又要因形附意、别出心裁;既要注重画面层次感,又要确保画面的饱满度和均衡感,突显构图的典型性。
(三)雕刻手法与色彩使用的典型性
客家民居梁架雕刻常用浮雕、透雕、阴刻、圆雕四种手法;刀法或精雕细刻,或大刀阔斧。雕刻出来的效果,或圆润如珠,或棱角分明、粗细得当。采地雕、镂雕技法交叉使用也是客家民居梁架雕刻最重要的手段,具有典型性。在色彩使用上,客家民居梁架雕刻或施彩,或描金,或重彩,或淡饰,使整个雕刻装饰效果显得庄严肃穆,富丽堂皇;同时还有利用木质天然纹理来表现的,简洁大方,朴素淡雅。客家人在雕刻装饰中所使用的颜色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在梁架上对颜色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红色和黑色在粤北客家民居建筑中是重要而广泛使用的色彩,红色表示富贵,黑色表示庄严。这表明客家人在建筑装饰中所使用的颜色不能随意而为之,尤其是红色和黑色都代表着客家人的礼节文化与民俗含意,可以直接反映出长久存在于客家宗族社会中封建的尊卑等级制度。这种特殊的意义更凸显了梁架雕刻形态装饰的典型性。
三、雕刻题材的人文精神
粤北客家民居的梁架雕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人类迁移过程中南北文化相互融合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承载着客家人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的文化精髓。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富含关怀人生、关照人的际遇处世及伦理道德,形成吟咏真诚质朴的人生情怀,表达了客家人对生活无比的热爱和期望。梁架雕刻的题材非常广泛,涉及岭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诸多方面,既有传统典故、历史神话,又有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雕刻题材与客家人生活幸福的祈求都有着直接的或必然的联系。例如,连绵不断的回纹,憨态可亲的福猪,活灵活现的鱼虾,都呈现出生活幸福连绵、温润祥和、繁荣昌盛的气氛,诉说着客家生活的温馨与吉祥,幸福和安康;又如,梁架两端的莲花和白鹭,反映了客家人盼望一路连科的美好愿望;再如,雕刻繁复、精致细腻的梅花曲梁,则显示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所有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客家人对生活与生存的热爱与追求。对这些题材的选择,客家人就是想借物抒情,寻求一种精神寄托,借助其中的隐喻激励着子孙后奋图强。通过在日常生活的传播与交流,他们已经把那些雕刻图案的耳熟能详的寓意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个励志的典故给人指向高远的人生目标,指引人们为了人生目标努力奋斗。从题材分析得知,粤北客家民居的梁架雕刻的主题表达主要为祝福人的一生平安、合家喜庆、升官发财、人丁兴旺、颐年长寿等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联系的愿望。即便是抽象的雕刻造型也被赋予了吉祥含意,这种丰富的含意体现了深刻的人文精神,隐含着极其深远的文化蕴涵,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
四、结语
梁架雕刻是粤北客家民居最具活力的建筑装饰艺术,它在岭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基础上,在客家民俗文化的充分浸染下,延续着极具特色的传统建筑装饰样式,体现出客家民居极具生命力和典型性的艺术特点。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文化,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眼下的今天,都体现出客家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梁架作为民居建筑的重要构件,其是粤北客家民居装饰艺术的缩影,也是民居建筑文化不可或缺的象征。
* 本文为广东省韶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始兴客家宗祠雕刻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项目编号:Z2014006)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廖晋雄.广东始兴客家古民居[M],香港:香港经纬印刷公司,2006.
2.
黄明秋.龙南关西客家民居门窗雕刻艺术初探[J],装饰, 2003(2).
3.
篇2
雕塑是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实用性与审美性相结合的艺术。建筑与雕塑艺术的交融,更多的是相互交叉和影响。雕塑作为一种再现艺术,决定着它具有美的独特性和表现性。它的美首先以形体的造型来反映生活、再现生活。它最宜于表现有崇高理想的正面形象,宜于观赏者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进行欣赏和领悟。雕塑对于观赏者来说,由于所处的位置、角度和远近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它能直接感染、陶冶和激发观赏者的心灵。因此,雕塑这种特有的最直接的表现性,决定了它的审美价值。雕塑具有可视形象以供欣赏的艺术,必然对建筑之美产生深远影响。
雕塑与建筑艺术
从题材来分,雕塑可分为纪念性雕塑、建筑装饰性雕塑、城市园林雕塑、宗教雕塑、陵墓雕塑、陈列工艺美术雕塑等。雕塑在表达思想情感时,要有概括性、凝练性和普遍性。
在早期的建筑装饰上,几乎随处可以见到雕塑的存在。建筑立面出现了龛的结构,里面可以安置雕塑。室内的壁面产生了浮雕,室外则出现了独立的雕塑。如今,随着建筑的形式回归到本体,雕塑的形式也发生了改变。雕塑不再与建筑的实体纠缠在一起,更多地被当作环境中的独立亮点来使用。这不仅使建筑的形式更加简洁,也使雕塑的地位更加突出、明朗。
在世界雕塑与艺术史上,中国古代雕塑可谓是整个东方雕塑艺术的代表,中国雕塑以其独有的艺术特色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数十种古老人类文明相继消失,而中国雕塑的艺术特色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旧保持了其自身的独特艺术内涵,这和中国雕塑的传承性是不无关系的。纵观整个中国雕塑的发展历程,艺术形式、风格特色的发展与变迁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特点和文化根源,朝代变迁、外来文化的融合,都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形式与风格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作品时,却发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秦汉短暂的朝代更替,雕塑艺术的形式与风格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很难找到其历史的承袭性,尤其是在秦汉时期的雕塑作品上,以秦代兵马俑和汉代霍去病墓石雕为例,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尤为突出。前者严谨写实,尽极人工之美;后者粗犷夸张,有如浑然天成。
历史文化名城泉州是建筑之乡,许多具有闽南风格的建筑成为中国古建筑的典范。特定的历史环境与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泉州古建筑的审美取向,同时也促进了其构件的艺术发展,从而形成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泉州建筑中的石雕、木雕文化。历史上泉州曾是东方第一大港,得益于海内外多元文化的吸收与交融,形成了包融、开放的文化性格。追溯其文化渊源,社会的发展与中原地区的步伐基本一致。尤其是自两晋到宋代,中原汉族人民先后有四次大规模的迁徙入闽,大部分成为福建的居民主体。而中原文化也随之传播到此,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不断地融合、撞击而呈现出独特的海洋文化。
自然人文的浸润,使泉州古建筑承载当地传统文化内涵,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沧桑历程,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而建筑中的雕刻艺术,则突显了泉州传统石雕艺术的美学风格。其中以我的家乡惠安地区的传统石雕为代表,其汲晋唐遗风、宋元神韵、明清风范之精华,逐步形成精雕细刻,纤巧灵动的南派造型艺术风格,与主体建筑交相辉映,一脉相承,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奇葩。泉州传统民居十分强调在精致的装饰处理中流露出一种灵秀、典雅的风范。例如被称为“闽南建筑大观园”的南安官桥蔡氏古大厝就是其中的代表。这首先表现在对泉州传统民居装饰构件的精雕细琢上,不仅在柱基上,而且在门、窗、匾、栏杆等地方的雕刻上也都强调了这一点。此外,门楣、门棂、隔屏木雕、插角木雕、斗拱木雕等等——整体雕刻技法娴熟,构思巧妙,线条细腻,朴素中透着灵气,无不让人赞叹建造者的巧夺天工和丰富的想象力。明清以来,泉州古民居上都镶有不同品类的石雕,这些雕刻精致的建筑饰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建筑物显得生机盎然、意境深邃,也突显出传统民居的典雅精美。
可见,雕塑艺术在建筑中,以其所蕴涵的大量传统文化信息而令世人关注。
雕塑与环境艺术
雕塑是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分担改造环境的重任。它在一种新的意义上介入环境。这种意义并不是说它会客观地构成一种环境,而是说它要以新的态势展示新的环境艺术观念,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
如今的环境,更需要雕塑的介入。人们久违了阳光、草木和新鲜的空气。污染、噪音、单调、沉闷等现实因素或心理感受无时不在搅扰着人们。这一切动摇和破环了人类建立于对抗自然之理性基础上的自信、乐观和幸福感。人们终于醒悟过来,他们不再迷恋和沉溺于完善的物质功能的享受。这标志着新观念的崛起,它要求校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主张人与自然亲和融合,这一切简而言之就是“回归自然”。
因而环境艺术家们(建筑师、园艺师、工业设计师、雕塑家和画家)肩负着更大的责任。雕塑作为环境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雕塑艺术介入环境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西方的一些雕塑家已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如卡得尔的活动雕塑,以自由运动的客体造成时空变幻的视觉效应,使审美主体产生丰富的体验和自由的联想;前苏联马马也夫高地的《祖国--母亲》,以群体空间的综合造成一种特殊的空间机制,令人产生身临其境的现实情感体验;史密斯的雕塑把造型要素抽象到最低限度,使它融合到自然中去;里伯曼的雕塑的空间形体构造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使审美主体在对自然性状的空间形态的观赏中产生愉快的心理效应。
篇3
[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66-03
一、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造型法则及哲学依据
中国大型陵墓雕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随墓主人陈列于地下,如秦兵马俑、唐昭陵六骏;另一类是陈列于地上墓周围的仪卫雕塑,如汉霍去病墓石刻群、南北朝和唐乾陵、顺陵等墓前的镇墓石兽。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代表了封建体制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雕刻艺术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它们皆具有纪念碑式的形态和雄浑的气势,大刀阔斧,取其大势,其整体意识是在充分尊重巨石的原始形态和在以气驭形的艺术方法中获得的。在中国古人看来,肉体形态的仿真是形而下的,没有生命力,是短暂的;而深藏于形体之内的灵魂,即内在精神才是形而上的,才具有生命力且代表永恒,中国艺术中的“制器者尚象”、“观物取象”以及后来的“离形取似”等法则皆源于此,中国古人把“形而上谓之道”中的“道”作为至高无上的终极追求。清代黄钺在其专著《二十四画品录》的《气韵篇》中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总结:“六法之难,气韵为最,意居笔先,妙在画外。如音栖弦,如烟成霭……读万卷书,庶几心会。”《沉雄篇》曰:“目极万里,心游大荒,魄力破地,天为之昂。”《苍润篇》曰:“气厚则苍,神和乃润,不丰不腴,不刻而俊……”王微在《叙画》里也说:“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变动者心也。灵无所见,故所托而不动,目有所极,故所见不周。于是乎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以判躯之状,尽寸眸之明。”可见中国古人的艺术创作过程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即所谓“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
艺术不仅是描摹出大自然一角的视野,还应抒发作者与大自然的心灵感应,也就是说艺术应当超越写实与实用的功能,作者的超拔人格精神应当在艺术对话中居于主导地位。实际上这是一种儒、释、道合流或者是儒、道合流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儒、道、释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皆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儒家敬鬼远神,天人感应;道家“不愁生死烦,但觉天地长”,[1]追求天地逍遥;佛家崇尚坚忍、因果报应和轮回思想。它们皆强调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均对大自然寄托了无限的皈依,这与西方国家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想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思想是建立在西方近代平等、博爱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其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本主义思想;而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却是建立在2000年前中国古人对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积极思索和远古人类在漫长的生命火花的延续中对大自然形成的依赖、信任、崇拜、敬畏的过程中,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有着深厚的思想沉淀和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强调人对自然的顺因和皈依,强调形神分离或神对形的超越和剥离,这些都无不长远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人的思维逻辑和艺术追求。使得艺术生命在最大程度地膨胀着人类精神的光辉,同时也努力彰显着大自然的神秘和威力。
二、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的寓巧于拙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对神韵的高超驾驭体现在其对寓巧于拙的把握。天人合一精神最直接的体现在于对大自然的尊重和敬畏,应物象形的雕刻手法、“塑容绘质”[2]的处理手段使汉霍去病墓石刻群的跃马(图1)、卧虎(图2)等作品造型凝练、沉稳。与西方写实雕刻相比,汉霍去病墓石刻群开创了一种典型的东方造型审美,创造了一种粗犷豪放而非精致柔和之美,并发展了道家“见素抱朴”的顺应精神,即在顺应石材天然外形的基础上,大刀阔斧地稍加刻画,充分显现出石头的材质机理,使作品浑然天成、大巧若拙。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道家就发展出中国的辩证思维:大音希声、大智若愚、大白若辱、大巧若拙、福祸相倚……这些思想在长年累月的历史岁月中锤炼出了中国古人动态的审美观,从而影响到他们在艺术审美中也将事物对立两级看成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过程,“巧”与“拙”、“动”与“静”等在中国古人看来已非单纯的对立两级,甚至根本就是同义词。这样一种动态的审美观直接而深刻地渗透于艺术创作中,使中国陵墓雕刻不仅寓巧于拙,而且寓动于静,甚至忽视了雕刻形体的空间和体块,而转向一种纪念碑似地浑朴、敦厚的艺术表现。
当然中国古代陵墓雕刻的寓巧于拙还与道家提倡的混沌思想状态有关。如老子就认为混沌状态犹如四肢还没有展开的婴孩,但哭声最洪亮而生命力也最顽强,而人的生命终结也归于无,这种“无”即一种混沌状态,正是生命和宇宙万物的起源。而物象雕塑形式的出现,也许象征着那些血洒沙场的将士将在混沌状态中重生。
除此之外,寓巧于拙的形式美还与儒家文化初期正义自强的阳刚美不可分割,这使得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呈现出山一样的脊梁、岩石一般的外轮廓,并发展出雄浑、厚重和静谧的艺术特质,在大刀阔斧“拙”的外形中辐射出一股阳刚美和正义的力量。这正是“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大自然与刚毅、顽强的人性力量在这种机缘巧合中迸出的神奇造化。也许它疏于乖巧的形式,也许质朴的外形使其远离其生理结构,也许混沌的外轮廓让人难以捉摸,也许蕴藏其中的天人合一精神呈现出一股飘渺、玄奇的深意,也许它们蓄意彰显的只是一块得天地精华,混元天成的璞石……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思想的出发点不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出于人类精神的张扬和升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种略显粗糙的表面下得到了尽情释放。中国古人的抗争精神和反抗意志从而在这种看似呆拙的造型中得以永生。
三、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的虚幻灵异与永恒精神
事实上,中国陵墓雕刻艺术在天人合一思想框架下随着时代的变迁有着多重表现形式。动荡300多年的南北朝是中国民族艺术个性形成的重要时期,并最终开启了隋唐艺术的鼎盛局面。
较之于霍去病墓石刻群,南北朝和唐顺陵石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夸张风格,帝陵墓前置麒麟、天禄,王侯墓前置辟邪、石狮等,或昂首挺胸,或张口吐舌,大都肋生双翅,颈有翎毛,有着强烈的慑人力量。中国古人云:“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处。”[3]中国长久以来保持着“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或曰“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因此,古代中国陵墓雕刻艺术是生前享乐精神在死后的延伸,也是原始自然崇拜在历史中的延续,只是这种艺术表现除了寓巧于拙、寓静于动,还往往被古人赋予了更多的虚幻和灵异的想象。如南朝“齐宣帝肖承之永安陵前的石天禄”(图3),头生角,双目如电,昂首张口,弓腰挺臀,后腿微曲,体侧双翼浅刻,体态呈明显的“S”形,作腾跃状,表现出强烈的动态效果。其身体排列的翎毛更加强了这种即将飞升的效果,天人合一精神赋予了这种灵兽似豹非豹、似虎非虎、似狮非狮的生理特征。大自然的造化与人类的创新精神的融合再一次见证了人类想象力的神奇,这种似是而非的灵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严格的形制,天人合一思想在这里推波助澜、如鱼得水、酣畅淋漓地把一种活生生的超自然力量通过象征主义手法表现了出来,仍是塑形绘质,但却有了王者之气,有了帝王之尊,这种象征主义手法让空间变得凝固,让体块融化于流畅的线条中,与其说是一尊雕刻艺术,不如说它是中国古人内心信仰的崇拜物――图腾的固态表现。
这种象征主义精神同样表现于唐顺陵石狮,只是各个朝代信仰的侧重和文化主流的起伏差异,因此在中国历史雕刻艺术作品上或更显敦实、厚重,或更显虚幻灵异,不外乎是思想律动的迁移创造了这种气魄。或厚德载物、静穆中和,或虚幻灵异、灵动飞升,或坚忍无我、色空两忘,中国文化虽博大精深、群星璀璨,但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却惊人地化为一种虔诚的信仰:或信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王道,或信仰佛教、道教,或信仰自然主义的祖先崇拜,以此作为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艺术敏感地捕捉到了人类的思想脉动,信仰则在天然材质中如饥似渴地寻求着永恒的宣泄。“永恒”在中国雕刻艺术中有太多的共鸣,它燃起了中国古人对永生的渴望,燃起了中国古人对超越尘寰、飞升九天的信念,燃起了中国古人对权力的不懈追求。唐顺陵石狮和南北朝镇墓石兽等皆很好地展示了各自时代的特征,不管是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的强盛时期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岁月,中国古人都坚定的守护着自己内心的信仰,它们在坚硬的石材中与自然共融,在历史进程中,智慧的古人以内心虔诚的信仰在陵墓周围建构了一个个永恒的神话。
四、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的特殊使命
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捍卫的是一种专制主义及等级森严的封建体制,其源于君权神授的天人合一思想。“天”在这里即神秘的自然界,“人”即人类一切创造性的社会行为。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大大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合法性,并理直气壮、高屋建瓴地诠释了王侯与生俱来的统治特权。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即是对这种合法性的艺术追求。因此,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是超越时空的思想与艺术杰作,空间在这里凝固以衬托这种不灭的永恒。雕刻艺术的纪念碑造型,以跨越时空的维度完成对这种天人合一思想信念的捍卫,不管是南北朝的辟邪、天禄,还是唐顺陵石狮、昭陵六骏等皆体现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捍卫精神和一往无前雄浑气魄。
“天人一体”赋予了人类更和谐的宇宙观和无比坚定的进取心,从而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具有更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古人进行艺术创作时,天人合一思想的理论指导又是不自觉的,这是因为这种思想方法的模糊性,这种思想是从人性苏醒中走来,随着人性的振作、自强,人性的伟大、浪漫、执著、偏狭、惰性、宽容、博大、深沉等都在中国意象雕塑中有了充分的展露。在这里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出来了它的深邃性,在艺术表现中它含蓄得像一首诗,从情感深处走来又向灵魂的更深层渗透,它表现出深沉、羞涩、从容而非直白浅陋的生命情怀。天人合一思想生存的土壤是人性的深处,不轻易示人,但在青山绿水、柳绿莺鸣、月明星稀的感染和启发下它所触动的往往是人类灵魂最深处。毋庸置疑,无数中国古代陵墓雕刻艺术杰作前赴后继的地世人昭示着其顽强守护人与自然永恒不变的殷殷依恋和娟娟缠绵。
[注释]
[1]翟文明:《探索发现系列•三教九流》,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2]黄宗贤、吴永强:《中西雕塑比较》,五洲传播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3]汉•王允:《论衡•四讳》,丘麓书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张如画. 从西北雕刻看中国古代艺术之精神[J]. 长春大学学报,2003,(4).
[2]王峰. 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文化学研究[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2) .
[3]吴为山. 我看中国雕塑艺术的风格特质[J].文艺研究,2005,(6).
篇4
自古以来,中国古代帝王“事死如事生”,他们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因而盛行厚葬。他们生前花巨资修建陵墓,不但在地下修筑了巨大的墓室,还在地上修建了豪华的建筑,并且在墓前设置了显示权威与地位的神道石像。石象作为帝王陵寝常用的石雕,烙下了不同时代的印记。
1中国大象的分布
象,是陆地上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多产在印度、非洲等热带地区。早在青铜时代,大象就广泛地分布在我国的土地上。但随着气候带的变化,大象的分布北界限逐渐出现南移,大象的活动范围逐渐缩小,唐朝时,大象只在我国南方地区生息繁衍。我国境内亚洲象现分布于云南省南部。①
2佛教中的大象
大象在佛教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与佛教的诞生之地印度是产象之国有很大关系。在佛教中,白象是佛主释迦牟尼的象征。释迦摩尼入母胎时,即化作白象形。大象除了是释迦摩尼的直接画身外,还被广泛用于菩萨的坐骑之中。普贤菩萨的座骑就是象。
3陵墓雕刻――象
早在西汉时,大象作为一种异域兽类同珠宝、皮毛、瓜果、马匹等一起传入中围。西汉茂陵汉武帝的陪葬墓霍去病墓是我国最早的陵前设置石兽的墓。霍去病是西汉时期卓越的青年军事家,多次率兵抗击匈奴入侵,为王朝的统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汉武帝在茂陵旁为霍去病修建了以他战斗过的祁连山为形状的大型墓冢,为纪念和表彰他的赫赫战功,但这与之后神道两旁陈列石人、石兽意义并不相同。墓冢周围列置多种巨石雕刻,跃马、卧马、卧虎、卧象、卧牛、卧猪、鱼、蟾、蛙、翁仲、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等石刻。其中卧象(长1.89米,高1.03 米, 宽0.58米)②,腹朝地,长鼻垂于左足上。石雕采用循石造型的手法,简略细节,着重表现轮廓和力,注重整体形似,以表现特征为度,省略细节,没有作过多的雕镂刻饰,风格质朴古拙。③鲁迅先生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石刻大有我国传统画的写实手法,使作品即浑厚有力,高度概括,惟妙惟肖,是我国古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辉煌杰作。东汉帝陵神道石象以洛阳东汉光武帝原陵为代表,现存一神道石象,高3.2米,身长3.4米,宽约1.1米,整个身体全身滚圆,呈现行走状。小眼机警地观察前方,清晰的眼睫毛线条,象牙伸出,夹着象鼻,两只大耳张开如扇面。颈部和后腿有质感很强的皱皮。下垂的象鼻和小尾残断。④东汉陵墓神道石雕在雕塑技法上继承和发展了霍去病墓石雕审石造型和形象概括的特点。魏晋时代由于废弃了陵寝制度,墓前不设石刻,没有石像生。北魏开始恢复陵寝制度,在墓前设置石刻,但数量不多。南朝帝王陵墓葬于南京及郊区,有石辟邪、石麒麟,没有石象。
唐代是中国古代帝陵石雕列置制度的确立时期。人臣神道石像生与帝陵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并截然不同。但均没有设置石象。宋陵石雕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陵墓造像群之一,是宋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宋陵石像生比唐陵多石象。宋陵神道出现石象、驯象人并且序位仅次于石柱,整个石像生排列顺序,同皇帝生前出行的仪仗行列基本相同。永熙陵的石象,褥的两端用浮雕手法雕有怪兽搏斗图。石象的面额有髻勒。永定陵的石象巨大,象座周围刻有牡丹缠枝花纹,底座正面缠枝牡丹花中雕有一对身似鹿, 头顶肉芝的瑞兽,这在宋陵雕刻中仅此唯一。永昭、永厚陵的石象,在莲花橙下都有一走兽。在雕刻技法上,宋陵石雕的形体多为圆雕。石象的带形边饰均采用“剔地起突”的雕镌手法。雕刻部位纹饰高高突起在石面上,参差错落,雕刻最高点不在一个平面上。雕刻的各部位有空间感和立体感,有突出、有交叠。这种方法现代称为高浮雕或半圆雕。还有一种“压地隐起”的雕刻手法,类似于现代的浅浮雕。这种雕刻纹饰突起少,深浅相差小,比较平均,有一定的深度感,隐约间会有圆润的立体花纹。永熙、永厚陵石象象背鞯褥上的怪兽和小熊就采用这中手法。⑤宋陵石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每个陵的石雕各有特色。早期宋陵石雕继承了唐代气魄雄伟,刀法简练,又受到了佛教雕塑和绘画的影响,简中求精,实中有虚,在意整体也注重局部,注重形神兼备。⑥中期是由早期向晚期的过渡,也是宋陵石雕风格的形成时期。 晚期雕刻艺术完全趋于成熟。永裕陵,永泰陵石雕是宋陵石雕最为突出的艺术精品。这个时期的动物雕刻,除了以前的注意动势与细部刻划以外,也注意到神韵、风韵的表达。永泰陵石象眼眶的皱纹等细节刻划都非常细腻,连辔勒形成的皮肤凹陷都有生动的表现,使大象温驯朴厚的性情更为突出。南宋时期,因为“权宜择地攒殡”暂寄的措意,加上南宋的国势比之北宋更加萎靡不振,所以,南宋六陵的建制均草率简陋,既没有高崇的陵台,也没有神道的石像生 。到了元朝,蒙古贵族以其强悍的军事力量统一了中国,但是他们的社会生产方式还留有蒙古游牧部族的特征,古贵族实行秘密潜埋习俗,因此根本没有列置石象。明承宋制,在陵前仍列置石象,不同的是象侧不置驯象人,象身也无披饰,采用了写实的手法。明孝陵神道石象生中,石象的雕琢是最具功力。石象完全模仿其自然状态,采用立体圆雕手法,栩栩如生,朴实无华。明孝陵石雕群体现的是雄大浑厚,体积丰硕而富有感染力,反映出明初中国统一以后,所具有的博大坚实的气魄和朴素洗练的艺术特点。明十三陵石象从石雕的技法来看略显华而不实,缺乏内在的精神活力,远不及孝陵石刻的神韵。清人入关之前所建的盛京三陵之一的清昭陵动物种类和姿态来源仍源自于明孝陵。立象由白色石料雕成。象高大威严,性情温和,是天下太平祥和的象征。寓意有广有顺民,江山稳固的意思。
注释:①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的中国野象分布[J].思想战线,1990 (5):8691.
②刘丹龙,孙平燕.汉霍去病墓石雕艺术探微[J].文博,2004(06):89.
③窦志强.唐陵石雕的考古学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07:11.
④=4\*GB3宫万琳.东汉帝陵神道石象与刻铭“天禄”“辟邪”[J].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01:69.
⑤=5\*GB3孟凡人.北宋帝陵石像生研究 [J].考古学报,2010:328.
⑥=6\*GB3卫琪.略谈宋陵神道石刻艺术[J].中原文物,2005(05):80.
参考文献:
[1] 许晶.以唐代社会为背景的大象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1.
[2] 马海舰,郭瑞.唐太宗昭陵石刻瑰宝[M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
[3] 曹砚农.古代帝王陵寝实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7.
[4]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刘丹龙,孙平燕.汉霍去病墓石雕艺术探微[J].文博,2004(06):8891.
篇5
中图分类号:J3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1-0031-01
一、寿山石与寿山石雕刻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一种艺术之所以称之为“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绘画为什么是绘画而不是雕塑?雕塑为什么是雕塑而不是文学?一种艺术门类总是存在着某种基本的规定,使得它成为“这一种”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艺术。
对于任何艺术门类而言,不同的工具和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不同的时空形式,而这正是艺术创作的基点。寿山石雕刻也有它自己的工具和材料之间的相互关系。它的工具就是刻刀,而物质材料便是寿山石。本文便是从作为物质材料的寿山石与艺术家手中刻刀之间的关系入手,探讨作为稀缺资源的寿山石与寿山石雕刻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作为稀缺资源的寿山石
众所周知,寿山石因产于福建省福州市北郊的寿山乡寿山村而得名。其历史悠久,闻名中外,是中国文化艺术瑰宝之一。素有“天遣瑰宝”之美誉,又因其柔而易攻的特性,成为上乘的雕刻材料。在中国国石候选中,寿山石以列为国石候选石之首。
与此同时, 寿山石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随着近些年寿山石的价值被人们广泛认识,寿山石的开采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局面。因此,“福州市政府在2000年初实施了《福州市寿山石资源保护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寿山石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或破坏寿山石资源。对寿山石矿的开发和利用,实行保护性开采,禁止乱采滥挖及其他破坏性开采。
三、寿山石雕刻艺术过程中的资源保护
因此,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寿山石进行艺术加工和创新,也必须考虑在创作中保护“原石”这个问题。首先,“相石”构思十分重要。寿山石雕刻艺术家要发自对石头的钟爱,然后深人领悟,对面前的石头展开想象的翅膀,树立赋石头以生命的理念,以艺术的高度思维和激情,萌发创作灵感。寿山石有时可以利用原石完整的外形创作,采用“以少胜多、虚实相生,以写实与抽象相结合”是极其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法。一般而言,遇上一块上好的原料,对于一个艺术家是件欣喜若狂的幸事,是缘分。作品《灵螭》所选用的材料是寿山石品种中的名贵品种田黄石,原石重量约为20克,在创作过程中除去一些表皮才发现是田黄石中更为稀有的品种红田黄石,如何既能最大限度地不浪费和不伤害原石,又能出色地完成这件作品也是让笔者费劲了一番思量。最后笔者选择以古代神兽“螭”作为表现对象,最终成品后重约19克。这种机遇不会很多。特别是高档次的田黄石、各种冻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