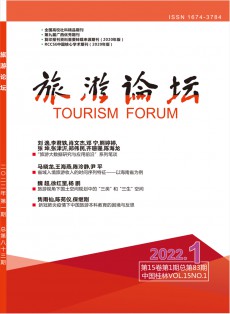旅游资源的定义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04 11:48:41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旅游资源的定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437项中,中原经济区所辖的30个地市共有101项(如表1所示),占7.03%。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品位价值、为旅游开发提供了高价值、高品位的基础,使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拥有巨大的开发价值。
类型全,名气大
在中原经济区的10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涵盖了10个大类中的9项,除了传统医药这个类型没有。如图1所示。但在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河南有5个传统医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中原经济区的文化旅游具有了切实的可行性。资源的多样性也必然会带来开发的多样化和综合化。
历史悠,底蕴深
中原经济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中原经济区的非物质文化在远古时代就有呈现。如以“河图”、“洛书”、“周易”为代表的中国“易文化”,以少林拳、太极拳等为代表的中国武术文化,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最早的文字文化等,都能在中原找到它的印迹。中原经济区非物质文化所体现的根源性,说明中原文化既是民族之根,又是文化之源。
篇2
作为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和旅游产业赖以发展的核心要素,旅游资源也是构建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根基,对“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定义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稳固性,以及对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然而,在当今的旅游学界中,对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认知还存在着很大分歧。因此,对旅游资源进行科学地界定,是当前旅游学术界以及旅游实践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本文回顾了过去40年中对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已及对旅游资源概念研究的相关文献,以期发现旅游资源概念研究的进展,归纳和总结前人研究中的共识以及存在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文献回顾
在我国旅游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历史中,对于“旅游资源”这一概念的界定是长期以来持续争论的焦点。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利益背景的主体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资源”给予了界定,可以说众说纷纭。笔者收集了47种来自不同书籍、论文以及文件中对“旅游资源”概念的定义,目前社会及学术领域主要的定义已经基本涵盖在了其中。从本文所收集的定义中可见,在对“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上,不同主体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理由,也各自存在合理性。所以,至今仍是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在旅游学术界,也已有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张凌云(1999)列举了当时代表性的16种“旅游资源”的定义,并将所有定义划分为三大类观点,认为“旅游资源等于旅游吸引物与旅游产品的交集”的观点,是最符合旅游业发展实际的,最后结合自身认识对其给出了解释;宋子千和黄远水(2000)在分析不同的旅游资源概念和相关论述后,提出了旅游资源概念应坚持的四点共识;张力生(2003)分析了已有的旅游资源概念及其属性,并从广义和侠义两个角度给出了旅游资源的概念;宋瑞(2005)也对我国现有旅游资源的概念进行了分类,并提出了现有旅游资源概念中的分歧与争论,最后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对旅游资源的定义及其划分标准;俞金国和王丽华(2010)在归纳总结现有关于旅游资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资源的几个本质特征并基于此提出了对旅游资源分类的方法;崔莹(2014)针对目前的4种对旅游资源有代表性的概念,对旅游资源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与探讨,认为在旅游资源的界定中“旅游业利用观”是更为科学的,并倡导以国标为标准,不应再对“旅游资源”继续争议。遗憾的是,虽然各个学者提出的见解都各有其长处,对于这一旅游核心概念的界定,我国的旅游理论研究至今并没有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致认可的解释。
三、研究发现
通过分析本文所收集的所有旅游资源概念及前人的研究观点,发现“吸引力”是“旅游资源”的基础这一共识已经达成。
吸引游客的功能和价值是旅游资源必须具有的前提条件。即不管是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还是实际的旅游行为,某一资源之所以能够称作旅游资源,前提一定是它的吸引力。正如李天元和王连义(1991)在所述“吸引力因素是旅游资源的理论核心”。在本文所收集和回顾的47种旅游资源概念中,就有26种明确的将“对旅游者具有/产生/构成吸引力”或者“吸引旅游者”“吸引力”等直接纳入了对“旅游资源”定义的语言中,另外还有10种用到“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及类似短语。可见“吸引力”作为“旅游资源”的核心和基础,在社会和学术领域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无可争议。
但是,在旅游资源这一概念上,更多的是存在争论性的问题。以下便是作者在研究现有旅游资源概念及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的最主要的几类分歧。
第一,旅游资源到底是为旅游者所用还是旅游业所用。在本文所收集的旅游资源概念中,宋瑞(2005)、孙尚清等(1990)、孙文昌(1986)、刑道隆(1990)、杨贵华(2010)、张凌云(1988)都明确表示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业所利用”,崔莹(2014)也认为在旅游资源的界定中“旅游业利用观”更科学。然而,陈传康和刘振礼(1990)、甘枝茂和马耀峰等(2000)、苏文才(1998)、杨贵华(2010)、郑本法(1994)则将“旅游资源”定义为能够“为旅游者(产生/进行/实施)旅游活动”的。这两种观点的不同,首先源于对“旅游资源”这个词语中“旅游”二字的理解不同。如果将其理解为“旅游者的旅游”那么就会赞成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者所利用的观点,倘若将其理解为“旅游业”,则会赞成“旅游资源”是为旅游业所利用的观点。作者认为,旅游资源必须“为旅游业所利用”的定义,似乎将“旅游资源”与“旅游业资源”等同了。因此,作者认为旅游资源应该“为旅游者所利用”的观点更加适合,即旅游资源应是可以用于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因为在旅游业存在前,旅游活动就已经存在,只是并未像当今社会这样规模化和商业化,若只有用于旅游业的资源才属于旅游资源,那么就等于说没有旅游业便没有旅游资源了。而且,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很多确实被旅游者用以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比如某些未被开发的海域、沙滩、森林以及一些不需要开发可以直接利用的博物馆、民俗村落等。这些资源没有旅游业的介入,或未被旅游业所利用,但对于旅游者来说,就是他们开展旅游活动的资源。所以说,将旅游资源视为被旅游业所用,这样的理解显然与事实是不相符的。但是,上诉两种观点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其实,被旅游者所用的旅游资源通常都是可以被旅游业所利用的,即便现在并未被旅游业所开发利用,也存在以后被旅游业所介入的可能。因为,某一资源既然能够供旅游者开展旅游活动,那么就拥有被旅游业所利用的价值和潜力。
第二,旅游资源是否是已经被开发的。一类观点认为,旅游资源是必须经过开发的资源。如保继刚和楚义芳等(1993)以及杨东升(2005)都将旅游资源定义为“人工创造物”。既是人工创造物,必然是经过开发的。朱玉槐等(1993)也认为旅游资源是经过人们开发,并在特定时空范围内被利用的。而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旅游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源,如黄回实等(1985)、朱玉槐等(1993)认为旅游资源必须经过开发才能成为旅游吸引物;杨时进(1998)则认为旅游资源是有可能被用来规划、开发的诸多要素。谢彦君(2001)定义旅游资源是可供旅游产业加以开发的潜在财富形态;杨桂华和陶梨(1999)认为旅游资源是可以为旅游开发和利用的资源。这一系列对旅游资源的表诉都说明旅游资源是处于目前尚未被开发状态的资源。但是旅游资源是否一定要经过开发,作者认为,旅游资源是未被开发或者不需要被开发的。首先,如本文在上一个段落的讨论中所说,某些自然存在的事物,并未被旅游业所开发,但确实已经成为了被旅游者用于旅游活动的旅游资源。还有一些资源是并不需要被开发而直接可以供我们使用的,如拥有秀丽风光的景区有些是天然存在而并不需要开发或加工就可以直接使用的。正如陈传康,刘振礼(1990)所说,在现实条件下,能够吸引人们产生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活动的各种因素都是旅游资源。
其次,在对旅游资源的界定中,对“资源”本质的认识至关重要,“资源”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是“资财的来源,一般指天然的财源。”“天然的”,即“未经开发的”。如某些矿产、石油资源,开发前,我们称其为资源,开发后就成了所谓的钢铁、石油、天然气等等,我们不再将其称为资源。而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前我们将其称作“旅游资源,开发后,我们则为“旅游产品”。因此,作者的观点是,旅游资源是未被开发或并不需要被开发的可供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资源,重点在于该旅游资源是否用于进行旅游活动。
第三,劳务或者人力资源是否属于旅游资源。一些学者,如郭来喜(1982)及唐学斌(1982)都将“劳务”纳入了旅游资源定义中。王大悟和魏小安(1998)、杨开忠和吴必虎(1998)也认为旅游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朱孔山(1998)将旅游资源划分为四个部分,包括了“旅游业人力资源”。然而,另一部分学者则持反对态度。认为人力资源或者劳务不属于旅游资源,只是在旅游活动中起到媒介作用(杨东升,2005)。将人力资源或者劳务纳入旅游资源的这种看法脱离了旅游资源最本质的属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宋子千,黄远水,2000)。作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劳务或者人力资源并不构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并未刺激旅游者产生旅游的需求或实际旅游行为。虽然我们在某些景区能够看到的演员的各类表演,甚至吸引旅游者前去旅游,但这很容易造成误导,使我们将这些人力资源及其提供的劳务,作为旅游资源。然而,实际吸引旅游者的并非这些劳动(表演)。如在迪斯尼乐园中,穿成各式迪斯尼卡通形象的劳动者,并不是旅游资源,真正的旅游资源在于通过他们而呈现出来的迪斯尼卡通文化。人力资源只是作为载体,将艺术、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无形的旅游资源呈现了出来。所以真正吸引旅游者旅游的并非是这些人,劳务和人力资源自然也就不应称作旅游资源了。
第四,服务、基础设施等是否属于旅游资源。一类观点如杨振之(1997)认为“旅游资源是旅游地资源、服务及其设施、旅游客源市场三大要素相互吸引、相互制约的有机系统。”王大悟和魏小安(1998)定义广义旅游资源涉及旅游活动的商品、设施、服务;朱孔山(1998)将旅游资源划分的四个部分中,“旅游设施资源”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宋子千和黄远水(2000)及宋瑞(2005)都认为,虽然交通条件、基础设施、旅游服务对旅游者旅游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不是旅游者前往一地旅游的主要目的,并不直接构成旅游吸引因素。作者的观点是,服务、基础设施等不属于旅游资源。排除旅游活动,这些服务、基础设施等在旅游客源地就存在。即便某些景区是人造的,也不能代表这些事物属于旅游资源,因为真正的旅游资源是通过这些人造设施设备所体现出来的对旅游者构成吸引力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而服务及设施只是其载体或媒介。另一方面,某些服务和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等,虽然不构成旅游资源,却影响到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或某一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如交通条件就可能影响到旅游者对于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的可到达性,旅游服务条件太差会减弱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
篇3
旅游界的一大部分学者对旅游学的基本概念旅游吸引物和旅游资源相互混淆,并有把两者等同起来[旅游吸
引物(Tourist Attractions)是国外旅游界通用语,其意义相当于我国旅游界常用术语旅游资源(Tourist Resources)。把能为旅游业所利用的旅游资源以及旅游业的相关的服务设施等统称为旅游吸引物,所以文中所用旅游吸引物是一个比旅游资源更为广泛的概念]的观点存在,并对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旅游资源和旅游业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对旅游研究的顺利开展十分不利。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旅游业、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等的综合的旅游吸引物系统框架,通过来整合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力求使这些关系更加明晰,促进旅游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旅游资源和旅游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
陈才,王海利,贾鸿通过旅游吸引物和旅游产品、旅游资源之间构建了关系分析体系,把旅游吸引物进行细分,可以派生出旅游对象、旅游媒介物、旅游标识物3个子概念,构成一个概念体系。《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对象的解释为:名词,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是事物,如革命的对象,研究对象;特指恋爱的对方。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解释前者。对象(object)是一件事、一个实体、一个名词,可以获得的东西,可以想象有自己的标识的任何东西。对象是的实例化。一些对象是活的,一些对象不是。如这辆汽车、这个人、这间房子。概括来说就是:万物皆对象。把旅游吸引物细分为一种广泛的旅游对象概念,在逻辑上似乎有点欠妥。陈才等认为,旅游标识物是指各种提示人们前往某地旅游的旅游信息,如各种广告、旅游宣传品等,甚至包括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此时,旅游者起到了某种示范作用),这些信息的功能主要是唤起人们去某地旅游的欲望。既然旅游标识物是一种信息,那它是否属于一种旅游媒介物?旅游信息的提供是否为旅游业的一部分?这值得我们思考。
鉴于此,笔者一方面考虑到涉及旅游活动的旅游者(主体)、旅游资源(客体)、旅游业(媒体)的3要素理论,另一方面考虑到旅游吸引物是一个比旅游资源更为宽泛的概念,提出了各个概念的关系的分析框架(见图1)。其具体的要点有:旅游吸引物是一种能吸引旅游者的综合体,它不仅包括了旅游活动的客体――旅游资源以及以此为中心开发出来的核心旅游产品,还包括了旅游活动的媒体――旅游业以及与核心旅游产品一起构成的组合旅游产品;旅游产品是指可以通过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而形成(旅游资源依托型旅游产品)或是不通过旅游资源的开发直接在某一地域上形成(旅游资源脱离型旅游产品),并由旅游业这一媒介提供给旅游市场,用于满足旅游需求或是旅游者需求;旅游产品从构成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是为了满足旅游需求而形成的核心旅游产品;二是围绕核心旅游产品进行利益追加以满足旅游者需求而形成的组合旅游产品。
保继刚、楚义芳认为“旅游吸引物通常指促进人们前往某地旅游的所有因素的总和,它包括了旅游资源、适宜的接待设施和优良的服务,甚至还包括快速舒适的旅游交通条件,与之相对立的概念被称为旅游排斥物,即对旅游者去某地旅游决策起消极作用的因素,并且认为旅游吸引物通常情况下是旅游资源的代名词。”可以说,这一旅游吸引物概念体系已经基本涵盖了旅游吸引物的所有的系统要素,至于“旅游吸引物通常情况下是旅游资源的代名词”这一观点,是从狭义的角度说明了旅游资源作为核心旅游吸引物,以吸引旅游者的关键作用。为了加深对旅游吸引物研究的深度,有必要对旅游吸引物进行分解,同时要加以整合各个要素,便于理清各个要素的关系。鉴于此,笔者按旅游吸引力的来源及其作用把旅游吸引物划分为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和旅游业3大部分。
二、旅游资源
杨桂华从狭义的角度,把旅游资源的定义为: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能够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活动,为旅游业所利用并能产生旅游、经济、社会和生态4大效益的客体。所谓的狭义的角度是从旅游者的角度,这种定义方式已经基本涵盖了旅游资源的要点:吸引功能、为旅游业所利用、产生综合效益。至于产生旅游效益问题,从旅游的起源来看,旅游就是一种社会现象,从现代的大众旅游和旅游业角度来看,旅游是一种经济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旅游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现象,经济条件只是其外部支持条件,旅游产生的效益已经包括在经济效益或是社会效益的范畴之内。谢颜君认为: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存在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愉悦价值而使旅游者为之向往的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或社会现象。旅游资源应该是直接用于欣赏、消遣等的因素,能满足旅游者愉悦的目的,而不包括为了达到目的所必须使用的纯粹接待因素(所以类似饭店等媒介性因素,就不构成旅游资源)。笔者比较认同上面的两种较狭义的定义,这样更容易区分旅游资源和旅游业资源的概念,否则许多的关于旅游资源的概念不断泛化的趋向,如朱孔山(1998)认为:凡能吸引旅游者,满足旅游需求,能为旅游业开发利用的一切自然和人文要素的总和,统称为旅游资源;它可分为旅游对象资源、旅游设施资源、旅游购物品资源和旅游业人力资源4类。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一切可用于旅游开发的条件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业的资源,包括通常所说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旅游景观资源、旅游管理资源、旅游人力和市场因素,当然也包括旅游资源在内。
资源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这种解释似乎有些过时,因为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如“人力资源”、“网络资源”已超越了传统资源的天然性。旅游资源要针对旅游者,也要针对旅游经营者或是开发者,是旅游活动的客体,这就要求必须强调为旅游业所用,其产生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根据对旅游资源吸引力的认识和开发程度,可以对旅游资源分为潜在的旅游资源、现实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有吸引力,但旅游业还未认识其吸引价值的,成为潜在的旅游资源,可以说潜在旅游资源只是一种资源,一种准旅游资源;有吸引力、其吸引价值已经被认识、但还未开发的旅游资源是现实的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则是已经开发、为旅游业所利用的旅游资源(本文提及的旅游资源依托型旅游产品)。
综上所述,旅游资源是旅游吸引物的核心部分,旅游资源基本可以表述为“客观地存在于某一地域空间,吸引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活得愉悦价值,能为旅游业所利用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旅游吸引物的核心部分”。旅游资源本体存在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的意志只能决定这种资源何时作为或视为旅游资源。
三、旅游产品及旅游业
林南枝、陶汉军在其合著《旅游经济学》一书中,从旅游目的地的角度和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分别定义了旅游产品。“从旅游目的地的角度出发,旅游产品是指旅游经营者凭借着旅游吸引物、交通和旅游设施,向旅游者提供的用以满足其旅游活动需求的全部服务”,“从旅游者角度出发,旅游产品就是指旅游者花费了一定的时间、费用和精力所换取的一段经历”。谢彦君认为:此种定义方式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视角,也意味着旅游产品是一个行业产物,而不是一个企业产物,并从狭义而且单一的视角,其定义为:旅游产品是指为满足旅游者的愉悦需要而在一定地域上被生产或开发出来以供销售的物象与劳务的总和。
产品是生产出来的物品,如农产品、畜产品等,是一种劳动创造物,而商品则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社会里,产品和商品两个概念是有所差别的,商品包括在产品之内,而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所有的产品的生产都出于交换的目的,产品就是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没有实质性的差异,而在我国旅游学界通常把实际中的旅游购物品作为我们的旅游商品值得商榷。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旅游产品从构成上来看,可以分为核心旅游产品和组合旅游产品。核心旅游产品是旅游产品的最为原始的状态,是具有能满足旅游者愉悦需要的效用和价值;组合旅游产品是旅游产品的终极状态,是旅游企业或旅游相关企业围绕旅游产品的核心价值而做的多重价值的追加。此追加可以发生在生产领域也可以发生在流通领域,通过追加,旅游产品甚至具有满足旅游者旅游期间一切需要的效用与价值。通过这样一个构成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核心旅游产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游产品,因为它是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满足愉悦的根本动力之所在,而组合旅游产品是在以核心旅游产品为内核,追加交通、餐饮、住宿、购物等等的利益,形成了一种大旅游产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产品。
通过对旅游产品从构成上进行分类,与之对应的旅游业也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进行分类,狭义上旅游业,即按核心旅游产品来定义,就是由各个提供核心旅游产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的旅游企业所构成的集合;广义上的旅游业,即按组合旅游产品来定义,就是一种十分综合的产业,是由各种提供能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产品的企业所构成的集合。在我们的通常的操作中,我们更趋向与把旅游业视为广义的旅游业,是旅游活动的媒体部分,它满足了旅游者从事旅游活动中一切的效用和价值,包括了食、住、行、游、购、娱旅游活动的6大要素,其中游和娱是核心之所在。
综上所述,旅游吸引物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缺乏相关的经济学上的规定性,在语言或逻辑上也缺少相关的界定,而旅游资源是具有自在性的概念,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旅游企业只能对其开发利用,而不能生产;旅游产品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它的主要目的是用于交换;旅游业是旅游活动的媒体,通过旅游产品把旅游者(主体)和旅游资源(客体)充分连接起来。总体概括起来,包括了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业的旅游吸引物,把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有机的联系起来,一起构成了旅游吸引物系统。
参考文献:
1、陈才,王海利,贾鸿.对旅游吸引物、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关系的思考[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2、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3、杨桂华.旅游资源学[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篇4
对市场具有吸引力是旅游资源概念的本质特征
关于旅游资源的定义有很多,但“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吸引性)是众多定义达成的一个共识,这一共识也是大家认识旅游资源的基础。从旅游资源的吸引性共识不难看出,旅游资源是从需求出发的定义,这和大多数其它资源定义构成本质的区别。一般来说,石油、土地、矿产等资源可以从其本身的物理属性上来进行界定,如词典上对石油的解释是“液体矿物,是具有不同结构的碳氢化合物的混合物,可以燃烧,一般呈褐色、暗绿色或黑色,渗透在岩石的空隙中”,可见尽管石油是对人们有用的资源,但是石油的定义可以完全抛开人类利用的性质。实际上,旅游资源这一词语的构成和其它资源就有差别,如石油资源,“石油”本身是资源的一种,石油资源说的就是“石油”这种资源,而旅游资源显然说的不是“旅游”这种资源。
除了吸引性之外,有的旅游资源定义还强调了经济性。如根据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的界定,旅游资源(tourism resources)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在“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之外,又附加了“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条件。严格说来,经济性和吸引性并不是并列的条件,虽然具有吸引性未必具有经济性,但缺乏吸引性必然缺乏经济性,对市场具有吸引力是由旅游资源概念内在规定的。
对市场的吸引力是旅游资源评价根本依据
既然旅游资源概念的本质特征是对市场具有吸引力,那么从逻辑上说,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也必须以对市场的吸引力为依据。遗憾的是,在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评价中,对市场的吸引力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以上面提到的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为例,虽然该标准关于旅游资源的定义坚持了“吸引性”的共识,但是该标准的旅游资源评价体系却主要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属性进行设计的。该标准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包括“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等,虽然也有“观赏游憩使用价值”、“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项,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的吸引力考虑并不充分。从事物本身属性出发制定标准,从可操作性来考虑是较好的选择,而且“珍稀奇特程度”等指标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旅游资源的一些认识,因而有其合理的一面,在我国旅游业发展的早期对于摸清资源家底、选择开发项目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这种脱离市场吸引力基础的评价体系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混淆了旅游资源和文物资源、科考资源等专业资源的差别。在理论和实践中都不乏将事物的文物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同于旅游价值,将专业资源等同于旅游资源的例子。一些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门可罗雀,但是在旅游资源评价中,它们无一例外地可以得到较高的分数。
比如,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境内周口店镇的北京人遗址,距北京市区仅50公里,是世界上发现和保存古人类化石最丰富的遗址,特别是北京人头盖骨和大量用火证据的发掘,为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生动有力的实证。1961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与长城、故宫、秦陵、敦煌一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其文物价值不可谓不高,区位交通条件不可谓不好,但是近年来每年接待人数不过三五万人,甚至还远不及同在房山区、同是人文景观,且距市区较周口店远20多公里的云居寺。人们可以从管理体制、项目开发等方面找很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北京人遗址本身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太小,特别是在休闲度假日益成为旅游者出游主要动机的时代更是如此。
针对现有资源评价体系的不足,有研究者提出,鉴于体验价值已成为旅游产品能否热销的重要指标,因此,在进行旅游资源评价时,应充分考虑各项评价指标的体验价值。增加体验系数确实可以对评价结果起到一些矫正作用,比如该学者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评价,在增加体验系数后,其旅游资源等级明显降低了。不过,在笔者看来,增加体验系数只是一种改良方法,还未能坚持彻底的旅游资源市场观。彻底的从市场出发的旅游资源评价应该就是吸引力评价,主要就是4个方面:一是吸引力的广度。如在空间范围上,是吸引本地居民、周边市场,还是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在人口特征方面,是老少适宜,还是只适合年轻人等。二是吸引力的强度,反映对特定市场吸引力的大小。三是吸引力指向的市场结构。也就是吸引人群的差别,如大众或专业、城市或农村、沿海或内陆、中老年或年轻人、男性或女性、白领或蓝领等。四是吸引力的可持续性,即重复性和将来的发展如何。
在旅游规划界有所谓的“资源派”和“市场派”,但是如上所述,旅游资源本身就具有市场依赖特征,真正的资源派也就应该是市场导向的,因此做出所谓的“资源派”和“市场派”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假命题。当然,有一种所谓的资源派,做规划主要依据是按照国家标准的条条框框,对资源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这其实是一种教条主义,而不应该是“资源”的罪过。旅游资源的教条主义不仅在资源派学者中存在,在市场派、形象派、产品派乃至所谓的综合派等学者中也普遍存在。
基于市场化评价对旅游资源的重新认识
当将旅游资源评价从事物本身属性转向事物对旅游市场的吸引力时,关于旅游资源的认识也就大大拓展了。特别是旅游市场一直在发展变化,只有密切跟踪市场需要,才能准确地把握一些新型旅游资源。
(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旅游资源才是好资源
旅游资源必须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而吸引力往往又是由比较产生的。单独看某项旅游资源本身,也许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并且有开发为旅游产品的潜力;但是,在考虑到周边的竞争下,这些旅游资源就未必能够成为旅游资源,至少是难以成为好的旅游资源。如山东省邹城市是亚圣孟子的故里,有文物点295处,其中国家级2处,省级6处,并有省级风景名胜区1处,旅游资源的数量、品位可谓一流,但旅游事业却一直不够景气,究其根本原因,是邹城邻近曲阜仅23km,并与曲阜的旅游资源雷同(“三孟”孟庙、孟府、孟林雷同于“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位于曲阜这个热点旅游区的影子里。因此,除非是对儒家文化、古代建筑特有兴趣的专家、学者,绝大多数游人是不可能看了“三孔”再来看“三孟”的。虽然“三孟”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国家级或省级,但其旅游价值在阴影区内也只能是地区级或县级。这种“减值效应”致使邹城的旅游事业难以有大的发展。
(二)环境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早期,观光旅游是最主要的旅游活动形态,因而人们认识到的旅游资源主要也是观光旅游资源,如文物古建、奇峰怪石等。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界定的8主类31亚类155基本类型的旅游资源,几乎都属于观光类型,其对于旅游资源的评价,也多是围绕观光旅游的开发利用进行的。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一些新的旅游活动形态如休闲娱乐、度假运动、修学考察等逐渐成长起来,即使是观光旅游,也出现了休闲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主要基于观光旅游制定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也就显现出种种不合时宜来。海南三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笔者曾就三亚最吸引人的旅游资源做过一次简单的调查,结果大多数人都回答说是海滩、阳光,而很少有人说是南山、大小洞天、天涯海角、鹿回头这些具体的景点。在三亚官方网站对三亚旅游名胜的介绍中,也明确指出三亚的十大旅游资源有阳光、海水、沙滩、气候、森林、温泉、动物、岩洞、田园、风情,并且特别强调了三亚的环境优势,“三亚年均气温25℃,长夏无冬,空气清新,水质纯净,大气质量居世界第二,中国第一,被誉为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显然,诸如气温、水质、大气质量这类资源,是很难用“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来评价的。
(三)差异构成旅游资源
当前旅游消费总的趋势是追求更丰富、更深刻的体验。观光也是一种体验,但是体验不局限于观光,它的范围要比观光广泛得多。今天所说的体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体验,今天的观光也是深层次的观光,包含文化体验的观光。从传统观光的眼光来看,很多事物未必是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它们对于旅游者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事物,和旅游者惯常环境中的事物相比具有差异性,因而可以构成体验旅游资源。譬如,乡村老太太身上的大襟褂子,老头手中的大烟袋,光屁股的小娃娃,村姑羞涩的脸蛋,手中的鞋底子,村里人好奇的目光,以及他们的行为习惯、房舍服饰、居住饮食等,对城里人来说都是旅游资源,都可以转化成旅游产品,但是长期以来,这些社会事物并没有被列入旅游资源的行列。西部影视城也是一个成功利用差异性资源的典型例子。西部影视城距宁夏银川市仅20公里,又称为镇北堡影视城。与大江南北五花八门的“电影城”相比,可谓荒凉之至,寒碜之至,只能算是一片荒漠。然而正是因为这种荒凉,西部影视城才让人感到新鲜和神秘。从20世纪80年代初迄今,在这两座废墟中已拍摄了电影数十部。在此摄制影片之多,升起明星之多,获得国际、国内影视大奖之多,皆为中国各地影视城之冠,故被誉为“中国一绝”,正如其标语所说“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正因为它的神奇和众多影视的传播,镇北堡成了游客到宁夏必看的景点。
结论
从旅游资源的内涵来看,它就是一个从市场需求出发进行界定的概念。但是在以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为代表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中,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忽视了旅游资源这一本质特征,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而是从作为供给的事物本身属性出发来认识旅游资源,因而导致对旅游资源的大量误解。一些被认为价值很高的旅游资源可能得不到市场认可,而一些通常没有纳入旅游资源范畴的事物则对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近年来休闲度假性质的旅游快速发展,“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等指标对于衡量这类旅游资源的价值更加不适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研究者提出在旅游资源评价中增加体验系数,还有研究者提出非传统旅游资源的概念,但是从根本上说,只有坚持以吸引力作为评价的依据才是彻底的从市场出发的旅游资源评价。旅游资源的市场化评价,通过将评价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从而使得这种评价能够及时反映市场需求的动态变化特征,深化和拓展对旅游资源及其价值的认识,更好地指导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市场化评价的理念出发,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只有具有竞争力的资源才是好资源、环境成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差异构成旅游资源等结论。当然,市场的复杂性以及评价主体对市场的了解程度可能会导致旅游资源市场化评价结果的不一致,但这种不一致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得到检验,对于旅游资源配置的优化其实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篇5
一、引言
我国对旅游资源质量等级的评价依据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和“旅游资源共有因子综合评价系统”。通过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等项目进行评价,根据对旅游资源单体的评价,得出了该单体旅游资源共有综合因子评价赋分值。目前学界研究的重点都是知名度高、评分赋值大的“特品”旅游资源及旅游目的地开发,对不属于传统观念中“优质”旅游资源及目的地的开发与保护研究较少。然而,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我国众多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目的而正在积极进行旅游开发。那些相对来说旅游资源价值较低、尚未被开发或只是“浅开发”的旅游目的地开发对缓解珍稀自然、文化遗产遭受的旅游压力,丰富旅游产品品种,为旅游者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服务,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概述
随着对旅游目的地开发和演变规律研究的深入,旅游资源次优区研究也得到了学界的重视。国内主要研究成果是“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及其相关研究。许春晓在我国较早提出“旅游资源非优区”概念,探讨其演变规律和开发策略,指出旅游资源非优区的补偿类型、性质、突变概念和依附式开发理论,以期指导区域旅游业开发。罗艳菊对旅游资源非优区开发的影响因素、非优区的优化机制及理论依据等进行研究,提出开发的盈利模式。唐文跃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主要特征和开发的优弱势,探讨了非优区旅游开发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非优区旅游发展道路。隆学文讨论了旅游非优区的概念和开发非优区旅游资源的意义,从资源区位、经济区位、客源区位、交通区位、文化区位、认知区位等角度分析了旅游非优区的区位特征。李东和以合肥市为例说明实施旅游业空间拓展战略是旅游资源非优大城市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彭华从需求驱动角度研究城市郊区与周边小城镇的旅游开发成功之道。……但现有研究成果均未涉及旅游资源次优区内人文旅游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分布不均衡、丰欠程度不一、价值禀赋不等这些现象。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对旅游地的生命周期现象的研究,如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旅游地演化过程、预测旅游地的发展和指导旅游地的市场营销、规划提供了理论框架。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巴特勒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提出旅游地演化经过6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Chris Ryan对巴特勒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完善,指出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对目的地复兴的作用,以及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者热衷寻求“新的”、“未开发的”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下,缺乏“名气”也可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成功开发和促销亮点。
本文认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基础是拥有优质或较为优秀的旅游资源。“非”在汉语中主要是否定的意思,而“次”在汉语中则含有差于、第二的意思。参考经济学,“次优”的含义是未达最佳标准的,不最理想的,不最适宜的,不最满意的,因此本文使用“旅游资源次优区”的提法是较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