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文
发布时间:2024-01-07 16:28:43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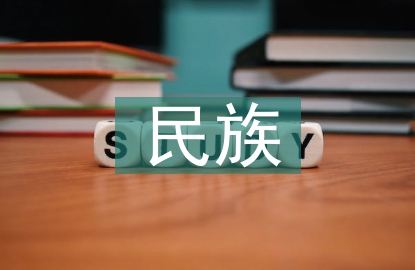
篇1
关键词:民族旅游 族群记忆 保护 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篇2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篇3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1.彭恒礼.论壮族的族群记忆—体化实践与刻写实践[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篇4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着习俗以及土着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篇5
【作 者】邓思胜,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C95;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16-005
Study On the Stalin’s “national” Definition Affect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Deng Sisheng, Wang Ju
Abstract :Stalin’s“national”definition have affected China’s nation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5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nrecognizing ethnic identity and dividing ethnic groups. However, we have to rethink this issue dur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Stalin;nationality;national recognition;reflection
民族识别,这项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影响中国民族政治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会影响到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政治运行和国家安定。时隔五十年以后,众多的学者(包括当时参与民族识别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民族识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当时实行“民族识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边疆地区,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如我国西南的滇贵川桂地区,过去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族群缺乏长期、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识别他们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他们现时社会组织发展形态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使他们逐步整合进入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条件。二是1949年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逐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族群优惠政策。”①“在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中国当时民族状况不清、族群认同混乱的现实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明确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进行民族识别问题研究的任务……当时提出民族识别任务的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②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与民族意愿。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作出“民族识别”政策和依据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定义民族理论研究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是斯大林的原名,他关于民族的研究论著有《社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曾在1913年发表的《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什么?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④他认为民族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这个概念和定义是斯大林在研究分析欧洲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这一民族概念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四个特征。“共同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和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族群的文化标识之一。“共同地域”,是一个共同体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具有各种联系的空间条件,从而能让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为地缘关系,“语言界限和自然疆界所决定的地域范围,无疑是推动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础。”⑥为民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共同的经济生活”,族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把民族中的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机制。这四者的总合构成了民族。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指导作用具有权威性。其民族思想主要表现在:(1)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三个演进阶段;(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伴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形成的共同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族”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3)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旧式的“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出现了新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它更具有“全民性”;(4)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前资本主义部落、部族,他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下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构成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5)在苏联各个共和国中存在着脱离了其民族母体而同其它民族掺杂在一起的移民性群体,称为少数民族。……⑦斯大林所论证的民族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所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也就是不分部落、不分种族的全体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
二、“民族识别”中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运用
从上分析来看,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是他在对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就现代民族而言的。但是并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提出一个科学的总结。而中国当时的民族情况是,还有许多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所以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四大特征,而且情况还更为复杂。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中认为:“在当时的民族识别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的情况;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交错杂居的特点。但是不同的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大多是清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但联系却很密切,因此很难具备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济中心,但却没有消除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心理素质在形成和维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族性的、表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它民族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掌握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⑧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民族这个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甚至有的族体正处于“分而未化”或“融而未合”的过渡阶段,这样他们就会在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对在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出来的显著共同性,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同时,民族特征正是相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在把各个民族特征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所以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每个特征,而是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把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属性。⑨
“民族学家们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民族作比较研究,既从斯大林的民族特征出发,又考虑了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形;没有照搬四个特征,在许多民族的识别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特征,并且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做法;充分考虑各民族族体群众的意愿,也就是注意了群众的群体意识。”⑩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民族意愿”,具体又分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两个部分。B11民族意识是族体成员对本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感;而民族愿望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的主观愿望。根据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观点,“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各民族决定应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和归属。”B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由代表性人物正确识别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B13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所遵循和依据的识别标准主要就是所谓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两个标准。这是为了实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目标而对各族群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划属进行的重要举措。自“民族识别”以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人群被划归于56个族体当中,各族体身份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制度化的结果。
三、民族识别=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其已形成的民族格局和政治制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在识别的过程中和过程后所带给我们的反思: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特点:
1、根据马戎的研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并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地的重视。B14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学者根据各族体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因为“尽管许多学者意识到应当尊重本民族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则是更高利益,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从事调查研究者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出现了对族群认同注意和分析不足的现象。如将不同支系并在一起,用人们对其中一部分族群的他称作为统合各支系的族称,往往会产生某些支系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国家确定的族属的现象;过早地由政府规定还没有发展出更高认同的“民族”,引起一些族群的不满;操之过急,对族群的认同,或者说心理素质似乎考虑不够。”B15
这样一来,表面上所遵循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的原则只是部分地、并不彻底地遵照和执行着。民族识别仿佛成为了政府和学者的事,各族群的人们对自己的族体归属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而已,因为对自己所属族体的族称是由各学者从客位的角度最终确定的;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民族识别只是整个民族政策制定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整个识别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再加上各族群精英的意识成为了确定各族体名称归属的主要因素……而且,整个民族识别中,并没有采用客观的科学依据,如各族群的体质特征的测量和鉴定等等。所以,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2、教条化和片面性的特点。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片面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教条地运用经典理论来套用于具体的民族族属的确定问题;片面强调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族源等文化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片面地将同一民族因为识别的行政区划不同、识别的时间不同而划为不同的民族等等……这些无疑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下了许多问题。
3、固定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确立下来的56个民族身份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56个民族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B16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确立下来的民族身份,似乎成为了民族自我的界定和归属,而且仿佛是不能改变的。
(二)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是同一的吗?民族理论研究
在上述的民族识别的特点中,我们对民族识别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民族识别应该是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应该称为族群。在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族群区分的最重要的特征包括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所以文化只不过是用来表明他们族属不同的标志而已,而不能作为族界划分的依据。
结合中国的民族识别来看族群认同,我们可以发现:(1)民族识别的确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中的一个构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在中央、地方、基层、民众之间加以运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个案。因为,从民族识别的目的来看便是为了国家今后的较好运作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当然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从族名的收集、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到族籍的最后确定都是政府在起着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就算有珍重民族意愿的原则作指导,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举措无不烙下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2)民族识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标识而客位地确定各族体的族称的举措。识别开始的时候试图以一种族群的原生情感来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识别的进行,而识别结束后又力图以一种国家公民情感来替代各族群的原生情感。(3)民族识别使全国各族群民众在个人感情、实际需要、共同利益和面临的义务等等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仿佛是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这种“民族团结的取得越来越不是通过诉诸血缘与地缘,而是通过诉诸含糊地、间断性的也是规范化的对公民国家(civil state)的忠诚,这种忠诚或多或少由政府运用警察力量与意识形态规劝予以加强。”B17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以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而实现的一项政治举措。族群认同,在族群内部是更倾向于文化性的,而民族识别是在族群认同之外更倾向于政治性的。而且不可否认,民族识别从外部更强化了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国家政府认可的范围内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强调、对自身族群优惠利益的争取、对自身族群文化的彰显等等……但是,在识别过程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或者根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认同的族群意识增强以后会否定或部分否定民族识别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族群认同和民族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在由国家划定了民族身份以后,是否获得民族身份的各族群就会实现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呢?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主要是通过认同意识而表现出来的。而民族认同意识主要有两种:
第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既有通过抽象的、不可触摸的“民族精神”、国民性、行为与思维方式等来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艺术文学作品、习惯、礼仪、制度等具象性的文化项目来表现的场合。两者不是相互排他的,后者有时可作为前者的具象化之物来理解。……第二,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被社会整体共有时,既有通过某种文化特性而整体论式地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社会的各种制度而制度论式表现的场合。以上第一分类与第二分类,如抽象的=整体论式的、具象的=制度论式的那样,是相互密切关联的。B18
一方面,获得国家认可的民族以自己族体具象性的文化事象和文化特征来归一着本族成员的认同感,在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双重的张扬中,促成了被划定的民族人群的认同,同时也逐渐培养起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竭力推进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等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群的发展现状镶嵌在了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事业中,各族群成为了国家公民性的载体而部分实现着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外在的强加在族群认同之上的高于个体、族群集体的一种在现代国家中对国家实体的认同,这是族群向政治化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虽然在民族识别后,一些族群对自己的族称划属的认同仍有分歧,但是在国家认同的方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族群认同并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也并不能确定族群认同就没有问题。
注释:
①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9―90.
②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③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1.
④ 华辛芝、陈东.斯大林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2.
⑤ 《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1.
⑥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5.
⑦ 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C].引自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0―111.
⑧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⑨ 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⑩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7.
B1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2.
B12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B13 .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B1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
B1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