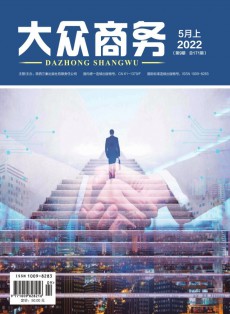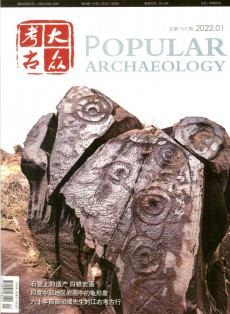大众传播概念范文
发布时间:2024-03-19 15:03:30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大众传播概念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依据普通逻辑学的两分法,信息可划分为大众信息和非大众信息,新闻可划分为大众新闻和非大众新闻。
大众信息是指已经由大众媒体报道出去并被大众接受(非单纯接收)的那部分非大众信息。大众新闻是指已经由大众媒体报道出去并被大众接受(非单纯接收)的非大众新闻。非大众信息包括自我传播的信息、人际传播的信息、群体传播的信息和组织传播的信息。“非大众新闻” 包括自我传播的新闻、人际传播的新闻、群体传播的新闻和组织传播的新闻。大众新闻是由非大众新闻转化而来的。
二
新闻和信息可以是实体概念,也可以是属性概念。在收听新闻中,新闻是实体概念。在收听新闻信息中,信息是实体概念,如果其中的新闻信息是语法上的偏正结构,那么,该新闻就是属性概念;如果其中的新闻信息是语法上的联合结构,那么,该新闻也可是实体概念。信息是新闻的邻近的属概念。
新闻事实是“我的主观世界”以外的客观存在,包括客体物质世界和来源于客体物质世界的其他主体精神世界的内容和形式。客观事实的属性在“我的主观世界”中被反映为属性信息,通过“我”的认知而产生的信息就是“我的主观世界”所产生的一种思想。信息表达的内容属于思想和观点的范畴。观点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经济的、文学的、物理的、数学的,等等。通过“我”的认知而产生的信息是主观存在。“我”以外的“他(她)”通过认知而产生的信息对“我”来说则是客观存在。客观存在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
在电视新闻等以影像为形式的报道中,除了传者向受众传达的以语言和文字所负载的信息之外,动态和静态的现场画面也包涵着新闻事实的属性,这种属性反映在受众的头脑中也会产生信息。传者对现场事实的属性进行反映而产生的信息一般包含在报道过程的语言文字之中。受众对报道中的现场画面的反映,如同对报道中的语言文字所传达的信息的反映,可以与传者传播的信息相同或不相同。传者传播的信息和受众对传播的内容进行反映而获得的信息可以用各种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肢体语言来表达。信息是人脑对于客观存在的主观思维的结果,属于意识的范畴。观点也是信息。新闻事实具有新闻属性,但新闻属性并不简单地等于新闻信息,人对于客观事实的新闻属性的反映才是新闻信息。如果人对于客观事实的新闻属性没有进行反映,那么就没有相应的新闻信息,但客观事实的新闻属性依然存在,这是毫无疑问的。新闻属性都是客观的、真实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反映新闻属性的新闻信息是主观的,不一定符合客观真实或不一定完全符合客观真实。世界(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是可知的。新闻事实也是可知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的信息与其反映的事实的属性具有同一性。
三
新闻报道与报道新闻在一定的逻辑环境中是全同的概念,它们的内涵之一就是让非大众新闻或非大众新闻信息通过大众传播而成为大众新闻或大众新闻信息,就是报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等传媒机构通过报纸、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向不特定的广大受众传播那些来源于非大众新闻事实的非大众新闻信息和非大众新闻现场画面,使其成为大众新闻事实和大众新闻信息。
在上述传播过程中,非大众新闻事实的非大众新闻信息和非大众新闻现场画面在完全被受众接收的情况下将通过受众的思维加工和解读而产生三种传播效果:一是全部非大众新闻信息完全被受众接受而成为大众新闻,这种效果完全实现了传者的目的。二是全部非大众新闻中的部分新闻被大众接受而转化为大众新闻,其余部分则通过受众的解读而转化为不属于大众新闻范畴的“受众的个人新闻”,所以仅被受众接收而未被受众接受,这种效果实现了传者传播的部分目的。三是全部非大众新闻均未被受众接受,因而都没有成为大众新闻,这种情况又会产生两种效果:一是通过受众解读使“全部新闻”均转化为“受众的个人新闻”,二是虽然经过受众解读,但“全部新闻”未被受众认可而又未产生“受众的个人新闻”,这两种效果让传者的传播目的完全落空。
传者进行大众传播的目的就是要让大众接收并接受其所传播、报道的新闻信息。传者把新闻事实转化为新闻语言、新闻文字、新闻影像和新闻图片,然后通过大众媒体进行传播,受众则通过对这些传播内容的解读把传者传播的新闻信息再转化为自己思想中的新闻事实,这是一个认知系统的两个相反的转化过程。这些过程体现了存在决定意识、事实决定信息和意识对存在、信息对事实具有能动反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传者知晓的新闻事实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受众通过对传者传播的新闻信息的解读而知晓、接受和理解的新闻事实则一律是间接的。传者和受众在对直接的和间接的新闻事实的属性进行反映时,可以产生关于该新闻事实的直接和间接的信息,同时,这种信息也可以引导传者和受众能动地认知新闻事实,准确地把握新闻事实,正确地理解新闻事实,积极地对待新闻事实,勇敢地干预新闻事实,大胆地进行新闻实践,坚定不移地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
因为媒体的“新闻报道”,非大众新闻才有可能被受众知晓并接受而转化为大众新闻。非大众新闻是新闻报道的内容。大众新闻是媒体对非大众新闻进行大众传播和报道的一种结果。真实的新闻是传者对新闻事实的真实反映。大众传播、报道和事实都不是新闻的属概念。大众传播和报道是一种把信息告知受众的方式和手段,利用这种方式和手段就可以把非大众新闻告知受众而使其有可能成为大众新闻。新闻事实是新闻反映的对象,报道所传播的内容只能是对事实或事实的属性的反映,而不能是事实或事实的属性本身。传者决不可能通过大众传媒把某个有形的物品传递给受众,也不可能使这个物品所具有的属性与这个物品分离而传递给受众。报道所传播的内容只能是关于事实的某种思想,这种思想反映的是某种事实或某种事实的属性。事实的本身不经过传者的反映是无法让受众知晓的。
此外,大众传播和报道是两个具有全同逻辑关系的概念,它们的外延全部相同,但是大众传播和报道这两个概念所表达的感彩是有些区别的:大众传播较为突出受众在信息报道过程中的地位,报道则较为突出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大众传媒。
篇2
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瑞士现代语言学之父费迪南索绪尔,他说:"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②他称符号为"概念与音响形象的结合,并用所指与能指分别代替概念与音响形象"。"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换言之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的诞生是任意的,不确定的,是约定俗成的。如对于"树木"这同一概念,中文是shu mu?熏而英语却是tree。然而索绪尔没有解决符号的所指与能指对应关系被固定之后的问题,因而被称为封闭的静态符号观。索绪尔割裂了符号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哲学家皮尔士在这一点上与索绪尔分道扬镳,他认为符号是世界与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皮尔士提出了"指称对象"的概念,他对符号定义是:"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者关系上代表某物的东西。"③这里包含了三个要素,认知主体--指称对象--解释。由于指称对象的提出,使符号的生产得以动态不断发展。能指与所指固定下来的旧符号,也可以成为指称对象,经过认知主体的重新阐释,可以发展成为新的符号,使符号不断丰富多样。皮尔士根据符号与指称对象的不同关系,分为类象符号、指示符号、抽象符号。类象符号通过写实或者模仿来表征对象,它们在形状或者色彩上与指称对象的某些特征相同;指示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是模拟,而是与指称对象构成某种因果或者时空的连接关系;抽象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约定俗成的。根据皮尔士的思路,我们基本可以认为符号产生有三种模式:一是写实、模仿、模拟;二是因果、连接,如红绿灯、球场上的哨声等;三是约定俗成,如树木、小鸟、微波炉等。但是无论是何种产生模式,符号的形成离不开传播,而且符号的功能一旦形成,最能经历时间的考验,它是恒久的,深入人心的,难以改变的。正是由于符号的这种特性,考察符号是由谁生产,如何生产,这是关系到话语权的重大问题。
二、大众传播语境下符号的生产
传播的形式大约可以分为自身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种模式。"大众传播"的概念首次出现于1945年11月在伦敦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西方学者常常引用杰诺维茨1968年提出的大众传播的定义:大众传播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这些技术(如报纸、广播、电影等等)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的内容。④因此大众传播至少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传播主体是一群有组织的群体;传播的媒体是机械,信息可以大量复制;受众广泛。
机器的发明及应用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崩溃,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崛起,缔造了宏大的工业文明。大众传播媒体时代的来临,符号的生产与流通脱离原先零散、单个的生产,转变为有组织、有规模的大生产,大量的符号被设计、生产、流通。人际传播中,首先是个人或者组织提出符号与指称对象的意义阐释、意义指向,但此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确定的、模糊的,只有在人际传播中经过不断的抗争、剔除、讨价还价、妥协并最后认同,才能成为符号。大众传播的来临将这一切改写:首先符号的生产由有组织的群体代替个人。波德里亚说:"记者和广告商都是神奇的操纵者:他们导演、虚构物品或事件。他们对其进行'重新诠释后才发货--在此范围内,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建构。"⑤在大众传播语境下,以记者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体组织,与广告商合谋共同主宰了大众传播媒体的符号生产与传播。大众传播媒体通过把关、议程设置,决定哪些符号可以传播流通,而哪些不能。"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广告从不讳言:我们是在贩卖观点和想法。中国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升空,航空界为纪念这个伟大的创举,用汉语拼音与英语拼造出"Taikonaut"表达太空人的概念,经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反复传播、重复,"Taikonaut"符号就迅速被认同了。其次大众传播的符号暴力代替人际传播中的讨价还价,大众传播媒体符号暴力来源于它的无限复制。如同我们在世界任何一家麦当劳餐厅都可以吃到一样的汉堡包,大众传播中符号的生产是社会化大规模生产。《骇客帝国Ⅲ》全球同步公开放映,人们收看到的都是同质的、"原汁原味"的《骇客帝国Ⅲ》;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听麦当娜的《阿根廷,别为我哭泣》。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们通过这个延伸认识世界,感知世界。面对大众传播媒体排山倒海输出的各种符号、意义,大众只知道咀嚼那些残留的意义,却浑然不觉那些没有传播的符号的沉默甚至消失。
①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②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篇3
中图分类号:G2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10406在学术上似乎不应当有什么天经地义,不容怀疑的定论,然而在传播学的语境里,大众传播这个概念及其在传播学科中的地位似乎是个例外。仿佛传播学讨论的生来就是大众传播,而且大众传播就是传播学研究本身或起码是最主要的范式。然而,正是这个铁板钉钉的结论,遮蔽了我们正确看待传播现象的视线,它不仅遮蔽了我们正确看待日常交流的方式,而且吊诡的是,它对于大众传播的努力突出也遮蔽了我们正确看待大众传播的方式。
如果要真正理解大众传播,我们就应当重新将大众传播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对象物加以研究,研究它的成因与它在传播学结构中的特定位置。而解释大众传播的最好方法,是将它放在它与其对立面——日常交流的关系中去考察它,而不是从它的内部去寻找意义。如果这样做,我们将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众传播和一种全新的传播学视野。
一、传播研究的对象生来就是大众传播?人们往往忽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拉斯韦尔和他的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提出这个概念的1939年之前,在李普曼已经感受到这个概念内涵的1922年之前,研究日常生活交流的传统已经在大西洋两岸蔚然成风。也就是说,传播研究的主要对象并非天生就是大众传播。以修辞和言语为代表的日常交流研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美国就已经进入了大学,而且从事这类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们还成立了规模庞大的学会。“到了20世纪,大学还没有传播系,但是演讲、文学作品表演、辩论和说服等方面的课程已经以‘言语’的名义经常地在英语系或戏剧系中得到讲授。20世纪上半叶,两种主要的言语研究方法出现了。康奈尔学院有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从人文的角度来涉足言语研究。中西部学院的学者们则认为,研究言语的最好方法是从科学基础出发。这些学派构成了修辞和言语的两条主要路径,也正是这些学者后来组建了与英语系及戏剧系相分离的言语系。”\[1\](P2-3)
所以很显然,大众传播的研究范式是在1939年之后才渐渐取日常交流研究而代之的。而耐人寻味的是,几乎没有一部专门的传播学术史著作提及这个问题。尽管像罗杰斯这样传播学社会科学传统的卫道士公然声明,他在《传播学史》一书中“没有囊括传播学的众多人文主义的起源”\[2\](P6),但他仍然在一些细节中流露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范式的存在,如修辞学和语义学:“伊利诺伊大学的传播单位中的著名的、但没有指派给施拉姆管理的单位是言语系。这个系力求成为一个人文学科,而不是一门社会科学,致力于人类传播,强调一种修辞的视野。……尽管已经和系里的老师讨论了加入施拉姆的传播系的可能性,但言语系决定维持原样,留在文学、艺术和科学学院。这个由系里作出的走自己独立道路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它导致了后来传播学领域之分为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分支学科。”\[2\](P474-475)所以,天生之说并不成立。
篇4
——马歇尔.麦克卢汉
西方著名的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其于1964年出版的论著《人的延伸:理解媒介》中富有创见地提出了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地球村”概念。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借助飞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媒介地球上的信息正在实现着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正在被大众传播活动消除,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弹丸之地。由于大众传播的同步化性质,整个人类社会已经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的、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联系的互动的小社区。简言之,大众传播的日益发展已经使地球进入到了一个“村落化”时代。
正是由于大众传播制造的这个互动的“地球村”以及大众传播带来的人的全面延伸,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内爆,而这种内爆又引发了社会结构、知识本质和文化形态的深刻调整——调整来自世界的每一处角落和每一个个体。我们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在不断制造着人类社会的当下流行神话,在这些富于爆发力的流行神话耀眼的光影之下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另外一个主题——大众文化。
究竟大众传播是如何诱发了文化体系从结构到形态的种种嬗变呢?而人类又如何来评价和界定这些变化呢?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将来之间会存在什么样的文化路径呢?我们可以找到并通过最佳的设定路径以达到我们所希求的目标吗?
概念认定及论证准备
在展开对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其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一定的认定和说明。
〔大众〕大众传播,英语对译词为mass communication,其中的限定词mass可以译为“大众”或者“大量”,这是一个特定语境下的语词,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人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大众社会,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作为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旧有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稳定的价值体系被打破,社会成员丧失了选择和行动的统一的参照系,而成为了独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个体,即所谓的“大众”。这里“大众”(mass)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群,它的主要特点有:(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无组织性(5)流动性(6)同构型。简单地说,大众是大面积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具有不同社会归属但有着相同的行为倾向的易受外界刺激和动员的流动的特殊社群。大众是一个传播概念,不同于其它诸如“公众”、“群众”等的政治概念。
〔大众传播〕在大众传播发展的不同亚阶段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ao)有着不同的定义界定,这个概念有着很不稳定的认定过程。针对本文的论证范围和论证体制,援引如下定义——“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外延上应该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活动以及电影、流行音乐、广告等。
〔大众文化〕基于以上对“大众”的界定,我试图把握“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这个概念,但是很无奈。因为“文化”这个概念实在令人无从着手,从亚里斯多德、柏拉图到福柯、马尔库塞,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思想者都试图对“文化”进行一个结论性的定义,但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够圆满地完成概念的认定。所以我只能在一个武断的人为设定的平台上加以一定的说明。雷蒙.威廉士曾经指出,“关于文化的(当代)用法,常见的大致上有三个”:(1)用来“描述知识、精神和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用于指涉“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团体或整体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3)用作象征“知识尤其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及其成品”。本文着重讨论的领域是基于第二、第三种关于“文化”的用法而设定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种用法中,文化在当代语境中应该扩充到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和娱乐以及大众媒介。
大众传播工厂的神话
传播,无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从传播史来看。我们会得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结论性认识:传播的发展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它对文化复合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广义的传播媒介包括了时间性媒介和空间性媒介。时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信息处理和传播功能的媒介体系,如书籍、报纸、广播、电影、电视等;而空间性媒介主要指的是担负运输和交通功能的媒介体系,如车辆、舟船、飞行器等。在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之前,尤其是在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在人类传播活动中是主导媒介,对人类传播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力较时间性媒介更为显著(我并不否认时间性媒介在整个传播史上的主体意义和影响力)。在空间性媒介居于主导地位的机械时代,空间性媒介工具和技术的每一次革命都带来了人类社会以及附着在社会肌体上的文化形态的调整和变动。古代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为人类实现海上远航创造了条件,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正是在指南针的指引下在曾经遥不可及的海外开辟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和贸易市场,使世界成为一体,打破了人类千百年来不同大陆不同人群的相对隔绝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扩大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提高了人类的活动能力,由此人类社会旧有的结构体系被打破,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构成也相应地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革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断兴起、上升;并且,由于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和延展,人类信息传播的要求相应提高,在此情况下刺激了人类信息传播从技术到结构形态的革命,而传播体系的革命也势必造成文化领域的震动和重组。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开始海外市场的占领之后,报纸成为了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而在此之前,报纸只是一种影响人群较窄、影响力较小的媒介。报纸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文化领域也开始不断酝酿和引发革命,对于这种革命我们可以在文学、艺术、教育等领域找到很充分的证据。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带来了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的削减,这在火车、轮船和飞机出现以后表现得异常明显,人类的同步化显著增强,于是就要求信息传播进一步强化。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无线电技术和各种电子媒介得以飞速发展。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人类的文化复合肌体在信息量不断增大、信息传播日益迅疾、传播内容不断扩展的情况下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调整和嬗变。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时间性媒介开始成为主导媒介,它开始表现出爆炸式的影响力,并且爆炸的当量不断增大,这时的人类传播已经进入到大众传播时展期。体现在文化领域,时间性媒介造成了人类社会的交织景象: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种群、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治话语系统、不同的文化传承体系在信息需求和信息技术可能性的影响之下,频繁接触、沟通、交流,并互相影响、作用和激战。文化的斗争在传播领域进行得如火如荼,而在这种需求性的斗争中,各种文化类型发生着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期的各种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体系的不断颠覆和不断建构。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人类进入到了一个癫狂的时代。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西方人从读书识字的技术中获取了采取行动而不必立即作出反应的能力,机械时代反应和行动是割裂的、延迟的;但是机械时代消退之后,大众传播时代中人类生活在一个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里,人们用电子时代之前的陈旧的、支离破碎的时间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这个新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背景了。经过超过3000年的专业分工的爆炸之后,人在肢体的技术性延伸中经过3000年日益加重的专业化和异化之后,世界戏剧性地逆向变化并收缩变小。在某种意义上,电子使地球缩小成为了一个村落。人类已经并且还在以电的速度发生某种内爆,在这种内爆因素的作用之下人类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来自于人的政治性,人的责任意识提高到了很高的程度,人们必须承担义务并参与行动,个人观点相对淡化,人变得不安起来。我们看到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使人类从个体到社群都发生着激荡的震动,不管有人认为这种影响表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还是有人认为它使人的异化程度深化、使人成为了流行噪音的癫狂化的工具,但都说明了大众传播对于人类文化体系的全面介入和全面改组,尤其表现在大众传播机器制造了人类文化史上最独特的类型——大众文化。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大多数的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中,人们总是狭隘地将目光集中在了雷蒙.威廉士对于当代“文化”用法的第三种形态的延伸部分(即流行文化和娱乐以及大众传播的一般行为),其实,大众传播对于知识领域的调整则更为隐蔽而意义深远。随着传播工具和传播技术的革命,人类社会在知识领域发生深刻的调整,这无疑是传播与文化关系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尤其是在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到来之后,这种调整更加显著。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所谓尖端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言是传播体系中最为复杂而关键的问题),如音位学与语言学理论、交流问题与控制论、现代代数与信息学、计算机与计算机语言、语言翻译问题与机器语言兼容性研究、存储问题与数据库、通信学与“智能”终端的建立、悖论学等等。这些信息传播科技都对知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的影响来自与知识的一个主要功能——传递。由于各种传播工具和仪器的标准化、微型化和商品化,知识的获取、整理、支配、利用等操作在今天都已经发生了变化。法国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曾经指出:“信息机器的增多正在影响并将继续影响知识的传播,就像早先人类交通方式(运输)的发展和后来音像流通方式(传媒)的发展曾经做的一样。”知识在大众传播时代以及已经到来的网络时代背景之下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知识为了出售而被生产,为了在新的生产中增殖而被消费;它不再仅仅以自身为目的,它的“使用价值”正在淡化,交换成为主要的目的。知识的本质以及知识的外壳都在大众传播和信息时代的技术背景之下发生了改变,知识作为文化的关键元素,这种改变正反映了大众传播对当下的大众文化的介入是深刻的;同时,大众社会境域下的知识的重新整合是大众传播体制对大众文化极具本质意义的影响。
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文化在传播机制的巨大影响下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颠覆和建构。传播学的各个学派以及其它领域的学者都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广泛而又卓有建树的研究,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为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热情讴歌,还是大声怒斥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这些理论都证明了大众传播对于大众文化的影响力是存在的,并且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大众文化的欢歌和悲曲
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20世纪人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上个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电视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进入到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并且电视媒介使得大众传播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以复加地被抛入了大众传播的旋涡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开始思考大众传播尤其是电视媒介给人类带来的种种影响,在这些学说中,既有对大众传播的赞歌,也有对大众传播的申诉,还有针对大众传播体制内部不同传播类型的对比批判。尤其在西方,媒介批判成为了传播学和文化学的重要领域,这其中不乏一些尖锐而偏激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建构在西方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基础上的思维成果无疑都为我们思考现代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参照。
西方主流的传播学者(以经验学派为典型代表)认为大众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积极作用是以往任何时代背景下任何类型的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在他们的学术理论体系中,极度宣扬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活动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建构性影响。
德国人古登堡对于印刷技术的革新是传播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对于现代传播的意义十分重大。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中说,“从技术角度说,古登堡所做的以及自从他的时代以后的大众传播媒介所做的,就是把一架机器放进传播过程,复制信息,几乎无限地扩大一个人的分享信息的能力。”人类正是在这种能够大量复制信息的机器作用之下由传统的口述文化进入到了一个媒介文化的社会状态中,人类分享信息能力的极大增强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个边远的山村看到一台收音机或者电视带给一个村庄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人们通过一种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工具获取了异常丰富的信息,这些信息内容涉及与这个山村相隔几万甚至几十万公里的地方,这种信息的介入无疑给山村原有的生活处境带来了一种催化剂。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可以用于实现变革和突破的信息,而不再是故步自封和一成不变地维系旧有的生活体制。新的观念和想象在大众传播的渠道中萌动起来并借助传播的信道开始行动。我们认为,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选择,而大众传播的介入正是选择的必要条件,因为它为选择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变化,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标准和价值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同时我们看到人的知识获取、娱乐方式、时间分配等文化的体制都在发生着变化,西方主流学者认为这种变化是大众传播带来的积极效果——大众传播为人们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帮助人们在行动前获得足够的选择信息,这样人可以更加自由和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其中包括了选择自己的文化体制。基于突出人的存在和平权主义,西方主流学者提出种种学术性的叙述,主要的观点集中在大众传播造就和支持人的回归和人的独立,使人成为全面发展和自由选择的自我的人。确实,现代报纸的出现扩大了阅读的人群,从而改变了原有的精英文化体系,建构了一个平民化的文化体系;广播、电影、电视的出现,更使信息传播的受众要求降低,从而更加突出了社会参与的广度,社会成员更广泛地参与了社会的选择和文化的建构。在这种条件之下产生的大众文化无疑是一个众神欢歌的文化,它的广度是以往的文化类型难以企及的,因此大众文化常常以“人民的文化”自居。
但是就在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充满热情甚至开始癫狂起来的时候,开始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出现和活跃为传播与文化又提出了更为深入的课题。这些学派有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意识形态“霸权”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等。这些学派和理论相比主流的经验学派来说更加具有破坏力,同时也更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之下建构起来的。在这些学派和理论中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向,一是关注传播的宏观影响,其批判话语指涉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文化构成;二是关注传播过程中人的个体化行为和感受以及发展,话语指涉的是作为人的个体的存在与可能。
西方社会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不断加剧,这种独占现象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控制下的文化生产和流通,而大众传播活动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和统治权力。大众传播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独立性。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部分: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在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媒介通过象征事物的选择和加工,将社会事物加以“符号化”和“赋予意义”;在文化产品的消费过程中,受众接触媒介讯息,进行符号解读。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促进现存不平等关系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又有推动人们接受不平等、安居较低社会地位的“从属性”价值体系,还有不满足于阶级支配现状、号召社会变革的“激进的”价值体系。大众传播的符号化活动,在本质上是按照支配阶级的价值体系为事物的“赋予意义”的。因此,我们看到的日益丰富的西方大众传播产品,实际上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系统中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的垄断资本的价值体系下的文化体制的产品,它自然担负着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任务,而并非像主流经验学派所强调的那样,大众传播是人民性的、平权化的大众文化的缔造者。同时,受众在符号的解读过程中,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接受的,由于符号的多义性和受众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S.霍尔认为,受众对媒介讯息有三种解读形态,一是同向解读或“优先式解读”,即按照媒介赋予意义来理解讯息;二是妥协性解读,即部分基于媒介提示的意义、部分基于自己的社会背景来理解讯息;三是反向解读或“对抗式解读”,即对媒介提示的讯息意义作出完全相反的理解。霍尔认为,大众传媒的符号化和受众的符号解读过程,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各种从属性文化之间支配、妥协和反抗的关系,体现了“意义空间中的阶级斗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活动繁荣的景观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权力机器,尽管它标榜自己是平民的、反体制的和自由的,但是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的一个组件,它只是资本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运作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浮华文化的工厂。同时从受众角度看,受众也不是充满愉悦地接受着大众传播机器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肌体的亲近,其中的反抗、争斗正在日益激烈。
T.W.阿多诺则从微观上对大众传播造就的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他很犀利地将“大众文化”的提法推翻,并代之以“文化工业”,为了“消除一种误会,即防止人们望文生义,认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特点是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业实质上是在向消费者兜售商品化的信息,并且通过不断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大众传播机器不停地运转,不停地制造出光怪陆离的文化产品,这些产品无论是一般信息还是娱乐活动,都如同宗教说教一般是某种意义的装腔作势的空谈,并以此来控制受众的感官、选择和行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形态的文化,同时是一种技术化的文化,它通过传播机器大量地被制造出来,因为传播机器的规格化、标准化和体制化,所以我们看到的大众文化产品都被贴上了标签,因而大众文化也被打上了某种规格色彩。借助阿多诺的分析,我们进一步透视大众文化,会发现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商品化、技术化和齐一化特点使得大众文化成为了一种数量上极大丰富的、感官刺激巨大的但实质上却是冷漠的、物化的、没有温度的文化工厂。在大众传播歇斯底里的叫卖声里,个体的分散性和无组织性而导致的脆弱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对于在大众文化景色里生活的人,H.马尔库塞用悲天悯人的话语到处了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罪恶。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传播把艺术、政治、宗教、哲学同商业和谐地混合在一起,它们在文化领域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商品形式,“发自心灵的音乐可以是充当推销术的音乐。”马尔库塞指出现代大众文化中受到最严格保护的价值标准之一,就是生产率。技术社会的操作原则和标准使得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人性化内容不断地降低,在这个文化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正在成为这个文化的基础的权力结构造成的牺牲品。大众文化是一个肯定性文化、压抑性文化、单面性文化。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介的深刻介入,人类虽然在文化生活中可以享受丰富的信息服务,但是在这样的高速、大量、虚幻的大众传播语境中,人们的自主性不断降低,经验派所说的自由选择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谎言,人们在发达工业化社会的大众传播背景下已经在逐渐丧失个体的独立性。更加突出的是,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技术化,导致人类工业革命以后最剧烈的异化,艺术等文化形式的体制化前所未有地加深,人成为传播工具控制下的孤独的迷惘的存在,并且这种存在正在和艺术一同消亡,因为灵魂在异化过程中不断地迷失。
中国当下大众媒介与文化批判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有着和西方发达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质。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传播领域,中国近20年来的发展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在中国传播事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众文化开始成长起来。应该说,西方的大众传播实践和大众文化现象对于中国当下的传播和文化是有一定的借鉴和反思意义的。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信息以各种各样的形态铺天盖地而来,从清晨到日暮,街头叫卖报纸的喊声、不停播放的电视节目、不断出现的广告牌……人们生活在一个被信息包围的环境里,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入到了大众传播的癫狂状态,相比西方来得要快,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的传播发展和由此而来文化冲突要比西方更显著。所以思考当下中国的传播和文化问题是必要而紧迫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媒介批判领域的成果相对的偏狭,大都局限在媒介的社会责任上,而忽视了更为深入的相关文化研究和心理研究。
20年来,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巨大的,当我们为社会信息体系的建立和由此带来的信息畅通以及人们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感到欣慰的时候,应该看到,由电视建立起来的媒介文化是一个强势的、干预性的媒介文化,人们在其中被迫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人在电视文化中被动地选择着某种文化人性,电视的视听文化特点决定了人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变得庸懒和无聊,没有满足的视听欲望控制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信息的商品化和电视的传播体系都造成了一个现实:电视造就了一种庸懒的被动的但很舒适的阅读方式和娱乐方式,思考成为了按动遥控器时的躁动和无助,电视很大程度上在扮演着一种勾引者的角色,被勾引的往往是青少年。我不是在鼓吹媒介的社会责任论,因为文化是一个社会镜像,传播并不是仅仅由媒介构成,所以这种文化困境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商品化的辐射作用,这种辐射的非理性状态伤害到了整个文化肌体,责任不应该仅仅由媒介来承担。如何有效地监控这种商品化的非理性辐射作用关系到文化整体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监控体系。同时,电子媒介的强势作用还表现为,当下中国人的角色错乱和自我缺失造成的价值标准的混乱。种类繁多品格各异的影视娱乐文化成为了人的物化生活情景之外的一个虚幻的生活情景,人在现实世界中的种种角色之外又开始有了种种虚幻的角色,并且这种新的不稳定的角色不断涌入现实生活,并干预着人的真实角色和行为。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模仿各类的媒介形象并产生了一些过激的体制外的反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很多隐性的社会文化问题从大众传播活动的诱发之下产生。
可以说,如何建构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文化体系对于中国的传播机制和其他功能部门都是一个很棘手但迫切的问题。 霸权话语的狂乱
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益发展的今天,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拥有自主选择自己的文化制度、道德和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的权利。文化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冷战结束后,在经济日趋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在借助于最先进的信息技术的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在文化交往发展到空前规模的情况下,文化交汇和冲突都异常显现和突出出来,并且正在改变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在对于文化与传播的思考中,一种叫做“文化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
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是在20世纪60年代反对“新帝国主义”的国际环境中诞生的。战后许多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手段相应进行了战略调整,由军事手段和直接的殖民统治为主转向了以经济手段和文化控制为主。新帝国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政策就表现为“文化帝国主义”。我们看到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相对完备的传播体系在世界范围内扮演说话者的角色,从好莱坞电影到迪斯尼的动画城,从香槟到美女,从哈佛到畅销小说,话语的权利被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体系把持,作为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只能更多地充当听者的角色。在疯狂的叫卖声中,强势文化主体尽情地扩张,并达到倾销商品的目的,以此实现着对世界的文化支配。在文化扩张中,大众传播媒介是其最有力的制度化的手段和工具。英国学者J.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对充当着文化帝国主义主体的媒介帝国主义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尽管他的学说带着为帝国主义辩护的色彩,但是他对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强大的具有全球活动能力的传播体系推销美国式的大众文化这一事实也是承认的。走在中国某个省会城市的街头,你可以看到可口可乐、麦当劳、《美国大美人》、比尔.盖茨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着,就像60、70年代猫王、披头士风靡全球一样。在这样的话语霸权严重干预着发展中国家和弱势文化民族的生活和文化的情况下,我们在思考,跨文化传播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在强势的高度垄断的发达传播体制的掠夺性的扩张下,发展中国家防守的最后底线是什么,有什么防御措施可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维护自己信息和文化主权?垄断的“传媒寡头”正在地球的上空游荡,你抬头就能看见他的脸,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吗?也许,我们能做些什么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同时,也在为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充满人性的国际信息新秩序而努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间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化传播体制,并通过各种形式来加强彼此的文化和传播合作,以此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并逐步突破发达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传播的强大包围圈。
结语
流行神话是大众传播一手制造的,我们还很难对它神秘的身体作出明确的可固定化的判断,因为它还在光影中不断变化。我们听见它的歌唱,看见它在起舞,也听见它在嚎叫,看见它在施暴。我们能做什么呢?观望当然是不够的。
参考文献
1《人的延伸:理解媒介》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 著
2《社会水泥——论大众文化》
陈学明、吴松、远东
著
3《传播学概论》
〔美〕威尔伯.施拉姆 著
4《传播学教程》
郭庆光 著
5《文化帝国主义》
〔英〕J.汤林森 著
6《世纪晚钟》
高小康 著
7《科学的历程》
篇5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肖像的概念
1.一般意义上的肖像概念
肖像一词最初是作为艺术的一个概念而出现和使用的。肖像,通俗地说就是“比照人物而制成的与人物相似的形象”。《辞海》下的定义是:“图像以肖其人者,谓之肖像。即将其人之姿态、容貌、表情等特征,精确表出之也。如绘画、雕刻、塑像、摄影、刺绣等为表出之方法。”《现代汉语词典》对肖像的解释是“以某一个人为主体的画像或相片(多指没有风景陪衬的大幅相片)。由此可见,肖像是以图像之形式表现人的容貌等特征;而图像的表示方法,可以有多种形式:绘画、雕刻、塑像、刺绣、摄影等等形式。
英文中,与肖像对应的词有portrait,image等。portrait作为名词指以绘制、雕刻、摄影等方式展现出的个人形象,尤以面部为主(a painting,drawing,sculpture,photograph,orother likeness 0f an individual,esp of the face或a verbaldescription 0r picture,csp 0f a person’s character);作为形容词是[ptinting](0f a publication 0r an illustration in apublication)of greater height than width―Compare landscape。
从经济学上说,肖像已经成为是一种能够带来利益的资源;从法学上说,肖像既是一种与人身密切相关的人格利益,又是一种财产利益。肖像所承载的利益呈现多元化。“此种标记和表彰方式更演进为权利能力外在形式。这种外在形式,最原初。最方便和最普遍的是姓名,到了近代,随着摄影术的商业化,又有了摄影肖像,这是仅次于姓名的普遍化标表方式。”。肖像作为自然人最主要的标识之一,逐渐演化为权利能力,并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
2.法律意义上的肖像概念
在法律上使用肖像的概念,最早是在著作权中出现。见于1876年德国颁布的《美术著作之著作权法》和《不法模仿之照相保护法》,随后肖像的概念逐步完善和发展。1896年,柏林高等法院法官克思奈出版《论肖像权》一书,提出了肖像权法律保护的新观念。1907年,德国立法机关颁布了新的《美术作品著作权法》,确认肖像作为法律概念,其意义在于确认了一个具体的肖像作品同时体现两方面的权益,一方面是肖像作品的著作权所有人所享有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是肖像人就肖像所享有的人格利益。就同一肖像而言,这两方面的利益无疑是冲突的,法律调整的正是这种冲突关系。
在我国,学者对于肖像的法律定义有不同的理解。从描述肖像人的外貌特征的角度定义的有:“肖像是公民人身真实形象及特征的再现”,“肖像是公民形象的客观再现,表现着一个人的形象,是公民的神采风貌的真实写照”,所谓肖像,是指自然人的外在形象通过特定的客观载体得以再现的视觉形象”,肖像是特定自然人外貌形象的固定形态(fixation)”……等等。从肖像的制作角度出发,偏重于肖像的艺术创作特征来定义的有:“肖像是采用摄影或造型艺术手段反映自然人包括在内的形象的作品”,肖像者,人之容姿之模写也,分绘画、照像、雕刻等类”,肖像是自然人外貌形象的再现,就是用照片、录像、画像、雕塑等方式把特定人的外貌形象再现出来……肖像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就是面部容貌”,肖像是公民个人形象通过绘画、照像、雕刻、录像、电影等艺术形式,使公民外貌在物质载体上再现的视觉形象”,等等。以上定义或偏重于肖像的艺术创作特征,或偏重于描述肖像所具有的人的外貌特征等角度,无法完全阐述肖像含有的全部意义,因此,本文综合以上各位学者的定义,将肖像定义为:肖像是自然人外貌形象通过物质载体固定再现的视觉形象。之所以如此定义,主要认为此定义能够表达出肖像的主要特点。能够包含下面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肖像必须是真实自然人的外貌形象;二是肖像必须通过物质载体再现,这个载体可以是木、石、泥、纸张、胶片、数据(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显示)等;三是肖像必须是一种固定的再现。崮定的手段可以是通过人工的绘画、雕刻等,也可以是通过机械方法的摄影、录制等,固定的表现形式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
二、肖像在大众传播中兴起
丹尼尔・贝尔断言:“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正处在一个由语言文字主导的时代走向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而在这样一种变化中,肖像作为图像、信息、符号,在大众传播中兴起具有一种必然性。
1.大众传播媒介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为肖像的兴起提供了条件
1839年人类发明了摄影术,可以把肖像定型化并逼真地再现出来。印刷术在发明网点印刷技术后,可以把照片印在书刊上,印刷媒介使得肖像的传播面更深更广。随着广播电视媒介的出现,使得动态的肖像可以被广泛的传播。图像在电视上的大量传播,占据了人们的视线,从而加剧了视觉文化的盛行,加剧了对肖像的视觉消费。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个人的肖像可以简单、快捷地输入计算机,再现的形式既可以是静态(static station)的图片,也可以是动态(dynamic station)的影像等。肖像的载体不断变化,方式也从有形到无形,即从有形的大规模纸张传播到无形的网络传播的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改变了肖像的传统载体及传播方式。
2.肖像作为一种图像符号具有自身的优势
(1)肖像作为传播信息的方式,古而有之
语言尚未形成时,人们便开始在洞壁内刻上图案或图画了。后来,图像成为一种传播信息的方式。图像早于文字等语言符号传播。文字发明以后,文字传播由于诉诸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对它的接受必然结合对一定语词的理解、组织、选择而进行。但是图像性内容则不需要文字的中间媒介,它直接诉诸人的视觉系统。不同民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士,大致都可以理解画面的含义。
(2)与语言比较,图像具有诸多优势
由于语言的不统一,对于不同语系的人士来说,经常会在沟通上产生困难。肖像作为一种图像,具有传播方式的形象直观性,图像是通用的非语言符号,无论长幼无论国别。人人均能读懂看懂。
3.从传播主体的角度分析
早在报业发展之初,媒体就采用图片来丰富报刊的版面。1845年6月28日,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以木刻形式报道前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葬礼,使得这天的报纸成为史上最著名的头版之一。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现代的报纸、杂志包括电视网络媒体等都不惜花费大量的版面和时间
刊登肖像。《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之一,其影响力逐渐波及全球。“封面人物”已成为《时代》周刊最重要的特色品牌之一。电视本身固有的传播特性更加剧了肖像的广泛传播;电视的传真性使大量精彩的肖像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电视的覆盖性,可以广泛地传播同一信息而毫不费力地到达受众端。
大众传播媒介不仅在新闻图片中大量使用肖像,在媒体的广告中、影视剧中更是大量使用静态的动态的肖像,以或展示或证明或表演的形式出现。 4,从受众角度分析 视觉图像以直观、感性的优势,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逼真地“再现”现实。理解也较直接,人们从中不仅仅获取信息,而且得到视觉冲击、审美愉悦。图像最具特征的是其可览的,何况是视觉所见到的肖像就是自己或自己的同类?含有肖像的图像更容易被受众接受。肖像作为一种图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高深精微的哲学思考到大众传播媒介的生产”,从新闻报道、广告到电影电视剧中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大众传播的发展使大量的肖像不断地传播,冲击人们的视野、观念及其他。
三、大众传播中的肖像利益
“利益”这一概念,有多种学说的定义:“需求说”认为,“利益是人们受客观规律制约的,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产生的,对于一定对象的各种需求;”‘需求满足说”认为,“利益就是好处,或者说是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主客体关系说”认为,“利益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作用于主体而产生的不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措施,反映着人与其周围世界中对其发展有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积极关系,它使人与世界的关系具有了月的性,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主体关系说”认为,“所谓利益,就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肖像,作为人的形象的抽象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人,能够成就人的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基于肖像由此产生各种利益。在大众传播中,使用肖像能够传递信息,人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的肖像得以满足娱乐、欣赏等需求,肖像上蕴含有满足社会需要的社会利益。对于个人而言,肖像上产生的利益,不仅涉及肖像人的利益,还涉及肖像制作人的利益。肖像利用除了会涉及财产利益外。还会影响相关人的人格利益或者尊严。
1.社会利益
大众传播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许多利益主体:作为大众传播相对方的社会公众,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大众传播媒介机构,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等等。在复杂的大众传播的过程中,这些不同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同的。作为大众传播接受者的社会公众的主要利益诉求是表达权和知情权;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机构有完成公民的委托,履行社会公众和大众传播媒介机构的政治契约,实现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义务。它还有为了自身发展谋求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等等。社会公众需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的知情权,肖像作为一种信息传递的方式,能够满足社会公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实现表达自由(知情权),从大众传播中获取娱乐,以获得自己的满足。肖像作为一种容易理解的图像信息,不管是用于新闻报道还是广告,肖像不断地向受众传递某种信息。肖像在大众传播中使用和传播,不仅对于本人意义重大,同时对于他人乃至全社会都具有价值,存在社会利益。
2.肖像人的利益
(1)人格利益
肖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肖像人的不可替代性,使一个人与他人相区别。一旦肖像表现明晰,具有了明确的指向,往往和特定人的人格利益联系。我国学者认为肖像所体现出的人格利益所体现的正是公民的人格,其保护的范围包含多个方面:公民对部分个人信息处于私密状态时,享有自己肖像不愿公之于众的权利;有权禁止他人非法毁损、恶意玷污自己的肖像等。国外有学者称之为“尊严性利益”,并认为在法律文献中无法找到对“尊严性利益”这一术语的现成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尊严性利益可能被视为与前述的、最广义界定的“人格利益”相毗邻。并归纳为如下三种:名誉上的利益(interest in reputation)、个人隐私上的利益(interestin personal privacy)和免受精神痛苦的利益(interest infreedom from mental distress)。
(2)财产利益
这里的财产利益,也可称为经济利益或商业利益。肖像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品,能够满足大众审美需要,肖像或肖像作品不但能够让人赏心悦目,而且能够给肖像人带来正面评价。从而产生一定的附加经济利益,派生出商品利用价值。公民可以基于肖像获得财产上的利益。如今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名人通过许可合同允许自己肖像被他人用于商业目的,如商业广告活其他商业宣传,使用者为此向肖像人支付报酬(使用费)。这样的许可利用,尤其是商业性使用实践表明,肖像具有财产价值,能带来财产利益。
3.肖像制作人的利益
肖像的制作、产生,一般还要涉及到制作人。而肖像制作人的利益不仅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在此意义上的利益与肖像人的利益有所不同,一般由著作权法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