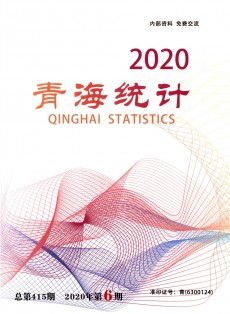统计学归因分析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2 10:39:17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统计学归因分析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 G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7(b)-0155-02
儿童是在活动中发展起来的。拥有成长自觉性的儿童,活动前渴望发展,活动中积极行动,活动后反思超越。然而,现实的校园生活中儿童的自觉性、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和释放,生命的成长是被动的、外发的,是缺少内在的欢乐体验的。通过问卷调查、个别访谈、集体访谈和实地观察发现,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虽说学校的管理工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这些变化还不够全面和深入,与新课改的理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对儿童的成长自觉性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本文尝试对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现有水平进行归因分析。
1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调研现状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的成长自觉性从11个维度进行考察,结果显示:在自我概念及评价方面,水平中等;在开放性指标上,水平中等偏下;在乐观向上指标上,水平中等;在成就动机上,表现较强;在能动性方面,表现较弱;创造性方面表现比能动性更弱;有较强的自主性;自律能力接近中等水平;能够较好地进行自我勉励;在反思性方面,水平较弱;在超越性方面,水平中等。一方面,儿童已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求知欲旺盛,成就动机强,渴望自主,在考试失败时也会反省,有一定的超越意识。但同时在创造性、能动性、自治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欠缺,不能很好地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目标模糊,不善于探究式学习,不太愿意主动参加学校或班级活动,不善于自我总结。
2 小学中高年级儿童成长自觉性现状的归因分析
2.1 同化:消失在集体中的个人
尽管新课改的理念对学校的各项工作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但是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为功能性取向和行为改变取向的专制型学生管理,侧重计划和规范,追求整齐划一,追求秩序,偏重行为的控制和纪律的维持。在这样的管理理念下,制定出严格的、周详的学生管理的规章制度,而在这制度背后的理念是同化,而不是尊重差异,尊重个性。从理论上说,儿童个人的权力优先于教育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从现有的一些学校的校规来看,其要求细致入微,对学生在校期间的所有活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其内容结构上明显失衡,没有学生权利的告知,只是义务的“独白”。学生在校规的制定中没有发言权,教师成了学生利益的代表者,按照成人的认识制定校规,并把成人的价值观念系统地灌输给学生。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规章制度的遵守要不就是被迫地接受,要不就是无意识地违反,很难形成学生的自律、自主、自治。
从现在学校管理中的部分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来看,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有的学校管理对群体利益和秩序的维护,追求整齐统一的管理效果,使学生丰富多彩的个性逐渐淹没在群体的共性中,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在这种群体价值至上的校规约束下,学生无法正确认识自身的价值,易形成盲目从众心理,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真实想法,压抑自己的个性,甚至产生对自己个性化需要的怀疑和否定。使得学生会逐渐失去对自我的认同和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这样的孩子长期以往,必将会形成被动的习惯和行事方式,缺少成长自觉。
2.2 负担:消失在压力中的求知乐趣
课堂是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教师和学生学校生活的基本场所。通过实地的观察和访谈,的确看到在校学生的课堂中仍然存在着对生命意识的淡漠和忽视的现象。使学生成为无生命色彩的认知体,而不是具体的有个性的生命主体;同样,教师也仅仅只是一个知识的“储户”,一个中介人、传递者,没有创造的激情和自由,享受不到职业生命的乐趣。
过关斩将:缩水的课间十分钟
在我所蹲点的学校班级里,一般每堂课结束前的十分钟,教师会布置一些需要完成上交的作业给学生做,学生在下课前做好了就可以出去玩会儿,没做好的学生就会一直在教室里做老师布置的作业,直到下堂课开始。
说到课间十分钟的休息时,班主任Z老师说,课间十分钟其实是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十分钟,对于中上的学生可能有五分钟,中下的学生可能只有一个上厕所的时间,因为每堂课最后十分钟是过关的,好学生可以很快过关,出去玩耍,一般的学生还要在那完成未完成的作业。
Z老师说,有些家庭作业不做的会形成恶性循环,上课补家庭作业,课堂作业又完成不了,听课效率也不好。
繁重的课业负担和纯知识教育让学生失去自由的空间和时间,失去求知的乐趣,背负沉重的包袱。缩水的课间十分钟是对生命需求的忽视,“过关斩将”给儿童增加额外的压力。在极端的状况下,学生只是被当成了一个需要被装满的知识容器,他似乎没有生命,没有情感。教师要做的就是如何把知识倒进这个容器。即使承认学生有生命、有情感等等,他也只是被当成是达成知识灌输、填入的手段,当成是达成高效率地实现知识灌输、填入的手段。一个好教师和一个差教师的区别只是灌输、填入的效率的高低。那声声“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从‘知识课堂’到‘生命课堂’”的呐喊,也将成为孤独的声音,越来越弱。
2.3 失谐:消失在控制中的尊重与理解
从交往实践观的角度审视课堂教学,课堂教学就是一种交往。真正的课堂往往应该是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下进行,是建立在师生、生生平等对话、自由、尊重、共享知识的基础上的,体现对人的独立性的尊重,对人的自由、自主、平等的主体性的认可。但在实际的小学课堂教学中,消失在惩罚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师生之间处于一种失谐的状态。没有和谐也就没有了双方积极主动产生的正向的合力。相反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和能量,以下的访谈也从另一侧面验证了这一点。
叛逆:滋生于惩罚中的不满
访谈对象:
(F老师 某小学四年级语文老师 大队辅导员)
(C老师 某区乡镇小学的语文老师,大队辅导员)
(Y老师 某区乡镇小学的数学教师,中层干部)
研究者:课堂上你要是碰到不认真听讲的学生,怎么办?
F老师:班上有好些不听话的,这肯定影响上课,老师要是不理他一堂课就会顺利结束。但是不行,你上课看着心里就不舒服,“给我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看你敢不听。”他回答不出来。一开始我就讲了,听清楚F老师的原则:课堂上回答不出来问题的,你就给我站着,我提下一个问题,你如果想回答的,立刻举手,回答对了,立刻给我坐下去。以前的学生,一旦课堂上站起来了,下一个问题,他肯定会想尽办法来回答,他们一举手,我肯定会让他们优先回答,因为他站着呀。回答对了,坐下去。毕竟嘛,课堂上站着,感觉是一种体罚,毕竟现在讲了这个,心里也有点那个。但是不对他采取一定的方法,心里面又生气。
研究者:那学生情绪上有没有问题?
F老师:以前的孩子,老师讲过以后他立刻意识到,哎呀,我刚才没注意听,他绝对怪自己,现在的孩子,他无所谓。去年我教的那个班,有学生从开头她就不回答,一直站着。我也想让她自己坐下来呀,我说这个问题你回答,回答对了坐下去,她也不回答,一句话也不说。
研究者:课堂上有没有可能让孩子更自由一些?
Y老师:你可以不要抱臂坐好,但是你的自由一定要是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不然课上不下去的。
研究者:这种自由的度应该怎么把握?
C老师:我呢,不是这样,你首先先按我的要求来做,然后我才会给你自由。我就是跟孩子这么讲,你必须要按我的,我是老师,你得听我的。听我的之后,好,你做好了,你跟老师讲,你想干什么?我再给你自由,否则的话,那不就颠倒了嘛。
以上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在很多老师的教学实践中,还是以教师为中心的,他们把自己当做是学生的权威,重在控制,而不是激发。过于注重课堂控制和通过奖惩制度达到纠正学生消极行为的目的,而忽略了对学生积极行为的引导和激发。久而久之,课堂没有了灵性,没有了学生的声音,充满规训化色彩。
2.4 苍白:消失在师本中的自我体验
学校里的儿童在自主参与、自我体验方面究竟如何呢?在现实的学校生活中,笔者所看到的情况更多的是儿童根据老师的要求,实现老师的目标。教师是导演,学生是演员,甚至只是道具。这一现象究其深层原因在于对教育对象——学生缺乏正确认识。教育的设计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在这种师本教育模式中,教育工作的中心,未能真正落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主动自觉的全面发展上。
其实,学生既是艺术品又是艺术家,她不是任由雕塑家随意把玩的石头,她不只是道具。而生命只有在体验中才能快乐地成长。因为“体验”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只能自己去体验。体验中的孩子是主动积极的,她有内心的参与和感悟。这样,才能刻骨铭心,才能把她所感悟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内化成自身素质的一部分,才能外显为一种自觉的习惯,这样才能知行统一,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而且这样的教学管理也会增加老师们不少的负担,损失不少的乐趣。剥夺了学生自主体验的机会和快乐,带来学生对生活现状的不满;善于接受,却不善于问为什么;目标模糊,对未来没有目标和规划。教师的越俎代庖,一方面加重了老师自己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学生体验参与的机会。这恰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现在班级管理存在的问题——重认知轻育人,重效果轻过程,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班级管理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缺乏民主,班级的事情一切都由教师说了算,学生仅仅作为被管理者;管理机制成人化、僵化,很少考虑到每一个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和需要;班级管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秩序,严重忽视学生发展的需要。因而,班集体缺乏个性和活力,学生在班级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自主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
2.5 迷茫:消失在框框中的成长自觉和生活热情
新课程倡导学生评价是一种发展性评价,它以评价对象为主体,注重评价对象的个人价值,重视提高评价对象的参与意识和主体意识,发挥其积极性。然而在现实的学校管理中,仍然存在着以学生考分成绩等为主要方式的量化考评,重结果不重过程,在评价时忽视了评价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学生发展的宗旨。
调查中很多教师坦言:评优、考核的主要依据甚至唯一依据是学生的学习成绩,且有只重视最终成绩,不重视平时表现的现象。这样做的后果是:学习好的同学的缺点被忽视,学习不太好的同学的优点得不到重视,最终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而且有些管理者看到有些班级考得好,不是说他们方法掌握得好,而是说人家时间花得多。教师就会在这样的导向压力下,对学生死糗、压制。采用应试教育的老一套,让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和自觉。这就势必会使孩子失去学习的乐趣,作为管理者的大多数教师也会屈服于固定的条条框框,在框框、要求中失去自觉和热情。
总之,教育的本质在于唤醒和激发,一旦学生的内在机制被调动起来,内部产生了从无序到有序的自动力,也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成长自觉,此时,学生的平行教育能力、学习规划能力、人生规划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张扬,同样,教师的教育机智、教育智慧也会经常充满生机和活力,班级也会在主体、民主的管理观中充满生长气息,从而给学生带来更大的成长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刘次林著:《幸福教育论》,南京师范大学(学位论文)1999年.
[2] 周韫玉著:《自我教育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版.
[3] 弗洛姆著:《占有或存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4] 马凤岐著:《教育:在自由与限制之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
篇2
【中图分类号】 G 442 R 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07)02-0127-02
Con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of a Private Middle School/ SONG Guang-wen, XU Xue-hua.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273165),Shandong Province,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students in Grade three of a private middle school, and to provide the evidence for the practical education.MethodsA total of 236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the scale for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examination. ResultsSuccess or failure was the main factor, sex and birthplace played little role. Students applied selfish attribution bias and had learned helplessness. Anticipation after failure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success situation, and believed the failure could be changed and worked harder for that.Conclusion The influence of sentiment and personality on attribution of success or failure should be explored.
【Key words】 Educational measurement;Factor analysis,statistical;Students;Private practice
【作者简介】 宋广文(1960- ),男,山东滕州人,硕士生导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及教育社会学等。
【作者单位】 曲阜师范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山东 273165。
随着我国办学主体的多元化,私立学校成为一支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对私立学校学生心理的研究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三学生面临毕业,且私立学校学生有不同于公办学校学生的特点,对他们的考试归因进行研究,以期对学生考试心理辅导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某私立学校初三毕业生236名,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12份。其中男生121人,女生91人;农村生源105人,城镇生源107人。
1.2 测量工具 中小学生考试成败归因量表,该量表的再测信度系数为0.62 (P<0.01),效标效度系数为0.46(P<0.01),经适当修改后用于此次研究。量表由成功和失败2个分量表组成,两者在内容上相反,采用从完全符合到完全不符合的5点记分。
1.3 方法 月考后分班级团体施测,成功问卷和失败问卷间隔1周进行。所有数据由SPSS 10.0软件统计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私立初三学生考试成败归因 私立初三学生对考试成功原因知觉的排序为运气、能力、心境、任务难度、持久努力、他人帮助、临时努力、教学质量,其中运气、能力和心境是主要原因,临时努力和教学质量是非主要原因。对考试失败原因知觉的排序为教学质量、他人帮助、持久努力、任务难度、临时努力、能力、运气、心境,其中教学质量、他人帮助和持久努力是主要原因,运气、能力和心境是非主要原因。见表1。
2.2 私立初三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方差分析 以性别、生源地为自变量,分别对学业成败的8种控制源倾向作多因素方差分析,见表2。
对各因素的主效应分析表明:(1)无论成功还是失败,私立初三学生学业成就归因都不存在性别和生源地差异。(2)成败因素在8项归因上都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而且学业失败时8项归因的得分都比成功时高。
在交互作用方面:(1)性别和成败的交互作用在他人帮助、能力和心境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男女生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缺少他人帮助(P<0.01)、能力低(P<0.01)和心境差(P<0.05),但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成败和生源地的交互作用在教学质量和任务难度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在教学质量归因方面,农村和城镇生源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教学质量差(P<0.01),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任务难度归因方面,对学业成功城镇学生比农村学生归因较高(F=-2.256,P=0.025),而对学业失败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890,P=0.375),即农村和城镇学生都将学业失败归因于任务难度大(P<0.01)。(3)性别、成败和生源地的3次交互作用在心境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对于学业成功,农村女生比农村男生得分较高(F=-2.707,P=0.008),农村女生比城镇女生得分也高(F=1.871,P=0.05),城镇男女生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370,P=0.712),农村和城镇男生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F=-1.233,P=0.220)。对于学业失败,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归因与期望变化 私立初三学生对考试结果期望变化的多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成败”因素在“能否改变”和“是否愿努力”归因上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检验表明:(1)学业失败的学生比成功的学生更认为考试结果是可以改变的 (F=-2.273,P=0.024)。(2)学业失败的学生比成功的学生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F=-3.966,P=0.000)。
3 讨论
同公立学校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一样,私立学校学生在学业归因中存在自利性归因倾向[1-2]。在本研究中,学生将学业成功归因于能力高、心境好等内部原因;而将学业失败归因于教学质量差、缺少他人帮助和运气差等外部原因。这是为了保护自尊心、消除焦虑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自我防御机制,也是建立在动机需要基础上的一种归因偏差。这种归因偏差在交往范围内同样存在[3]。
私立学校生源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学生的学业以失败居多。频繁的学业失败严重威胁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能力不强,即使努力学习也无法获得良好的学业成绩,从而产生“习得性无助感”(学生对学业失败归因的得分全部高于对学业成功归因的得分;对考试成功原因的知觉排序中运气和任务难度等外在归因,排在了能力和持久努力等内部归因之前)。提示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尽量减少因考试失败或简单排序带来的“自卑感”,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归因训练,改变其消极的归因方式。
期望是指个体对自己将来活动结果的预先性认知。原因的稳定性归因与成功的期望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学生将考试结果归因于稳定的原因,期望改变就小;而归因于不稳定的原因,则期望改变大。本研究发现,学业失败的学生比学业成功的学生更加认为考试结果是可以改变的,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这种归因方式对今后奋发学习具有激励作用,也是对学习有责任心的具体表现。
此外,成败因素在原因知觉和期望变化上全部达到显著水平,是影响私立学校学生归因的主要因素;性别和生源地因素在两者上的作用均不显著,是影响私立学校学生归因的非主要因素。今后需探讨影响私立学校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其他因素,如家庭因素、个性特征等。
4 参考文献
[1] 韩仁生.中小学生考试成败归因的研究.心理学报,1996,28(2):140-147.
篇3
【关键词】
精神障碍;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LU Yongyan, WANG Zhengwu, YAN Tao.
The Anding Hospital of Tianjin City,Tianjin 30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was selected from the psychiaitric hospital, there were 48 inpatients and the 48 patients with brain damage without mental disorder from the general hospital 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ll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were discussed and decided by the experts group. Results There were altogether 6 factors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Mental disorder;Brain damage;Risk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作者单位:300022天津市安定医院(陆永艳 王正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脑系科(阎涛)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导致伤残是指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经治疗后仍遗留长期的精神障碍,症状及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对固定,永久地存在生活、社会功能受损,且此精神障碍与损伤事件相关性一致[1]。随着现代社会各种意外伤害出现的越来越频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本研究旨在调查脑外伤的患者出现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预防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出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组被试均来自是我院自2005年以来的门诊和住院治疗的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纳入排除标准包括:①符合CCMD3中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②调查时间为脑外伤后3~6个月;③患者不伴随有其他躯体疾病及癫痫、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④患者智能未受影响,能够独立完成问卷;⑤患者首次脑外伤急救时保留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以及CT或核磁等影像学资料;⑥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配合调查的。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共48例,其中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37.56±12.3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的26例,高中以下文化的22例;48例患者中,脑外伤早期均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属于精神分裂型。对照组选自天津市某综合医院神经科的脑外伤的随访患者48例,其纳入标准包括:①有明确的脑外伤史;②脑外伤后1年以上未出现精神障碍;③年龄与性别构成与研究组一致。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既往史;③脑卒中史及再发脑创伤史。④脑外伤后持续昏迷或植物人状态患者。平均年龄(35.26±11.42)岁,性别:男28例,女20例。
1.2 研究方法 在患者家属的配合下获取患者的一般情况以及脑外伤的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时间以及临床特征。具体内容有:①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共有运动、语言和睁眼3大部分,将3部分得分相加,即得到GCS评分。②意识障碍时间。③CT阳性发现:包括血肿量、中线移位等异常表现,损伤范围以及有无脑干损伤等。此外还对患者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归因方式问卷。
1.3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内容均由2名精神科主任医师和1名神经科主任医师组成的专家组讨论所得,包括的调查因素为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以是否出现精神障碍作为因变量。问卷调查由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经过12学时的培训后进行(kappa=0.85)。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所的资料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涉及的统计学方法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P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基本资料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个单项比较的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纳入研究的因素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项研究因素比较
比较内容研究组对照组统计量值P值
颅内血肿21例(48例)15例(48例)χ2=4.680.03
脑干损伤12例(48例)8例(48例)χ2=4.350.04
损伤范围*单22/双15/三11单27/双12/三9χ2=12.620.00
GCS评分7.24±2.179.85±2.56t=7.520.00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EPQ评分36.24±8.4727.29±9.02t=8.640.00
归因方式50.26±12.2641.42±10.18t=6.590.00
注:*:“单”是指单个脑叶,“双”是累及两个脑叶,“三”是指累及三个脑叶或以上
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作为阳性和阴性结果设置为因变量,分别引入人格、脑损伤范围、颅内血肿、格拉斯哥分度量表评分(GCS)、脑干损伤及归因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及logistic回归详见表23。
表2
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变量变量名称变量赋值
X1颅内血肿0=无,1=有
X2脑损伤范围1=一个脑叶,2=两个脑叶;3=3个以及上
X3脑干损伤0=无,1=有
X4GCS评分实际评分
X5EPQ评分实际评分
X6归因方式评分实际评分
Y精神障碍0=未见精神障碍,1=出现精神障碍
表3
经过3步迭代后进入方程的变量
变量变量名称BS EWalddfsig.Exp(B)
X4GCS评分1.0080.2198.32510.0022.078
X5EPQ评分0.8630.0876.54810.0011.983
X6归因方式1.2680.2539.64110.0002.154
注:根据表3可知Y=1.008×X4+0.863×X5+1.268×X6+10.329.
3 讨论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十分丰富,其中以智力损伤为主,还包括躁狂表现、抑郁表现、神经症样改变、精神分裂表现以及人格改变等,其中脑外伤所致精神病性症状者占34.3%,其中以感知觉障碍、思维形式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多见[2]。本研究仅关注精神分裂型的患者,目的是避免混杂有其他症状表现,使影响因素发生改变。专家组选取的被选因素是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对于经过Meta分析证实有意义的单个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看其在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发病过程当中的相对贡献和整体作用。经过表1可知这些独立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在研究组和对照组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张登科等[4]曾经对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理论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脑损伤会累及相应的脑部区域,最终导致心理理论障碍。其实质就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成分。归因方式体现在被试对于引起焦虑情境的认知评价,与心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引起适应不良行为的认知因素的评价,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和对照组对于自己和境况的归因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详见表1),在预测方程当中可以见到归因方式的权重也最大,可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不单纯是生物学损害的结果,还与患者的认知方式有关。
篇4
2结果
分娩方式对比:观察组产妇中顺产88例,剖宫产48例,顺产率64.7%;对照组产妇中顺产28例,产道助产5例,剖宫产37例,顺产率40.0%。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良妊娠结局对比: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10.3%,显著低于对照组的45.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护理满意度对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9.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7.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篇5
Effects of the Attributional Training on Delivery of the Primiparas with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Chen Xiangli, Yang Zhaoning, Zhang Le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P.R.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attributionaltraining on delivery of the primiparas with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Methods The cases who fit for the standard admitted were randomly asigned to the trial group(n=26) and the compared group(n=26). The compared group received the routine labour service, while the trial group received the same care, together with attributional training before labour. Two groups were assessed with HAD and compared on the time of one month before entering hospital andentering hospital. Results There is no remarkab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ial group' score and the compared group' before entering hospital. However, The primiparas' score in trial group (7.36±1.63, 6.45±1.39) were remarkab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mpared group (9.51±1.89, 9.19±2.04) on HAD on the time of delivery (P
【Key words】 Attributional training; Negative attributional mode; Primiparas
面对分娩这一应激源易使孕妇产生不良情绪,有研究证明:归因为外控的个体越易于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1]。倘若使孕妇能对分娩顺利与否能有正确合理的归因,形成积极的归因模式(即分娩顺利归为自己身体能力强;分娩不顺归为缺乏准备、努力),可能将减少孕妇对分娩的消极预期,从而提高分娩质量。在已有研究[2]证明,归因训练对抑郁有明显影响基础上,本研究对具有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进行归因训练,试图探讨归因训练是否能降低其产前焦虑和抑郁、提高分娩质量,以期为消极归因的初产妇围产期护理提供一种新的临床心理护理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5年12月~2006年10月在向其陈述研究目的,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对临产1个月前左右入曲阜市中医院做B超检查的正常头位初产妇97例使用自编的产妇分娩归因问卷进行归因模式评定。据此筛选出消极归因模式(即分娩顺利归为运气好;分娩不顺归为缺乏能力)61人。入院临产时,实际选出孕周为37~42周,年龄22~30岁,身高155~170cm,均为头位单胎。经内诊头盆相称,宫颈条件好,妊娠无合并症与并发症,准备试行顺产的初产妇52例。然后按来院分娩先后顺序让对象进行抽签随机化分组,抽单号签者为实验组(26例),抽双号签者为对照组(26例)。为确保实验组与对照组条件均衡、具有可比性,对两组对象一般资料,包括孕周、年龄、身高、胎儿大小、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进行χ2或t检验,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工具与方法 (1)测量工具:产妇分娩归因问卷。该问卷根据Lefcourt等人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量表改编而成。将情景分成分娩顺利、不顺2种情景。每个分量表分4个维度,即努力、能力、背景、运气,其中,在可控性维度上,将努力归为可控,能力、背景、运气归为不可控;内外控维度上,能力、努力归为内控,将背景运气归为外控;稳定性维度上,将能力、背景归为稳定因素,将努力、运气归为不稳定因素。问卷的每个情景共12个题,每题从不同意到同意,依次计0~5分。每个情景下得分高的维度,表明被试认为情景产生原因主要由此维度决定。焦虑、抑郁测量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HAD)情绪测定表[3]。分A值、D值计分,A值表示焦虑,D值表示抑郁。判断标准:A值、D值各项之和≤9分为正常,>9分为阳性,可分别确诊为焦虑和抑郁情绪。(2)测量方法:对临产一月前左右入我院做B超检查孕妇进行归因模式测评同时,采用综合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初次评定其焦虑、抑郁状况。在归因训练后于临产入院时再测孕妇的焦虑/抑郁值。(3)归因训练方法:归因模式测评后确定出的实验组孕妇,在其同意配合情况下就开始心理干预。心理干预者由2名经过心理培训的医生担任。在建立了良好医患关系基础上,实施3天一次的归因训练,每次20~30分钟,干预让孕妇实现认知重建,形成对分娩的积极归因模式。咨询过程中建立孕妇心理咨询档案、记录每次干预效果。干预分入院前期和临产入院期两个阶段,前期以纠正信念为主,后期以培养和矫正行为为主。具体内容包括:①说明:向孕妇说明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和行为,若对分娩有不正确看法可能产生消极情绪并影响正常分娩。②讨论:了解孕妇存在的心理问题,然后确立如何说服孕妇的方案。关键是讨论分析自己主观努力的作用,加深对自己潜力、信心、努力重要性的认识。通过以上帮助,使孕妇改变不合理的消极归因模式。③示范:专门制作了录像,让拥有积极归因模式、顺产不久的产妇现身说法。④强化矫正和行为训练:针对患者自己对生产过程的正确看法,及时强化,对仍存在错误看法、做法予以矫正。进行生产行为训练,让孕妇掌握一定生产技能。⑤个别再干预:对效果不明显孕妇,实施针对个性弱点的再沟通。⑥产中的反馈强化:进入产程后一阵阵宫缩疼痛,让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易产生无助,甚至放弃自然分娩,要求剖宫产。此时,反馈很重要,使用积极的话语及时反馈给产妇。(在此过程中,医护人员要进行准确的医学评估,针对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不能一味强求自然分娩)。通过上述过程增加实验组产妇的自信心、努力。对照组26例消极归因模式孕妇只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不进行归因训练。(4)统计学方法:按来院分娩时间,将被试数据资料整理好,用χ2检验或t检验检查实验、对照分组是否有差异。HAD测量所得数据,输入计算机,使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同时考察两组产程、分娩顺产率、新生儿窒息率的差异性。新生儿窒息诊断标准为新生儿出生时无呼吸或呼吸抑制,或出生时无窒息而数分钟后出现呼吸抑制者亦属新生儿窒息。
2 结 果
2.1 两组的HAD评分比较 见表1。
由表1可见,进行干预前两组的焦虑、抑郁评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组在心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有非常显著的统计学意义(P
2.2 心理干预对产程的影响 见表2。
由表2可得,实验组较对照组第一产程、第二产程明显缩短(P
2.3 两组初产妇的分娩顺产率、新生儿窒息率比较 见表3。
由表3得出,实验组顺产率高于对照组,达显著水平;新生儿窒息率差异不显著。
3 讨 论
通过对消极归因模式的初产妇进行心理干预、调整其归因模式发现:实验组心理干预后的焦虑、抑郁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非常显著(P
综上所述,产前对消极归因模式初产妇进行归因训练能有效干预其不良情绪、有助于分娩质量的提高。
(致谢:感谢王晓辉、李玉红两位医生,在心理干预中付出大量的努力!衷心感谢曲阜市中医院妇科的全体医护人员,在实验数据的收集中给与大力协助!)
4 参考文献
[1]Moore D, Schultz NR. Loneliness at adolescence: Correlates, attributions, and coping.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 scence,1983,12(2):96-100
[2]王纯,张宁.抑郁的归因理论与归因训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4,18(6):423-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