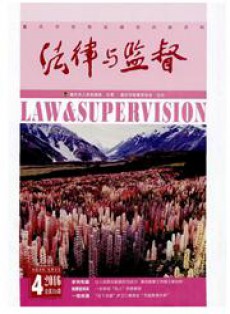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1:0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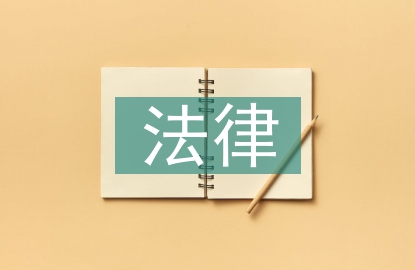
篇1
政府采购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及承担的行政责任
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商、采购机构等。
导致政府采购当事人行政责任产生的行为
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应当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单位或个人对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不进行招标,或者将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人和方式规避招标的。
招标机构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利益的。
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歧视潜在投标人或者强制要求投标人组成联合体投标、限制投标人之间的竞争的。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招标人向他人透露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或者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或者泄露标底的。
投标人互相串通投标或者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采购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违法与投标人就投标价格、投标方案等实质性内容进行谈判的。
评标委员会成员接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的,从而透露对招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招标人在评标委员会依法推荐的中标人以外确定中标人的。
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他人的,或者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或者违法将中标项目的部分主体、关键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
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或者招标人、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限制或者排斥本地区、本系统以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加投标的,或者为招标人指定招标机构的。
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而擅自采用其他方式采购的。
擅自提高采购标准的。
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业务资格的机构办理采购事务的。
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
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定采购合同的。
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
集中采购机构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考核中,虚报业绩、隐瞒真实情况的。
政府采购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
根据《政府采购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政府采购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行政处罚责任和非行政处罚责任。
行政处罚责任。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行政处罚的种类主要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停止按预算向其支付资金、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吊销营业执照、取消相关业务资格和资格、通报批评等。
非行政处罚责任。非行政处罚责任是一种补救性责任。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强制性措施等职权手段,要求政府采购当事人对违法状态消除或继续履行法定义务。根据《政府采购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其主要方式有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返还权益或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承认错误等。
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及承担的行政责任
行政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国家权力,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管理,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法律后果的组织。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政府采购行政管理机关主要有财政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同时,各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除工勤人员以外,都是《政府采购法》承担行政责任的公务员。《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民事活动中因民事违法给国家造成损失的,除承担民事责任外,也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指依据法律、法规授权而行使特定行政职能的非国家机关组织。《政府采购法》第十六条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级政府采购项目组织集中采购的需要设立集中采购机构。集中采购机构是非营利事业法人。
>!
的行为
政府采购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的业绩考核,有虚假陈述、隐瞒真实情况的,或者不作定期考核和公布考核结果的。
任何单位和个人阻挠和限制供应商进入本地区或本行业政府采购市场的。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供应商的投诉逾期未作处理的。
对招标投标活动依法负有行政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尚不构成犯罪的。
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的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职责。监督不力将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监察机关应当加强对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国家机关、国家公务员及其他人员实施监察,监察不力将依据《行政监察法》承担行政责任。审计机关应对政府采购进行审计监督,审计不力将依据《审计法》承担责任。
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
1、行政主体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
根据《政府采购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行政主体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有行政赔偿责任和非赔偿责任两种。
(1)行政赔偿责任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如某供应商并没有违反《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及其他法律规定,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错误地认为该供应商违反了第七十七条的规定,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对其进行了罚款和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后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确认,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属行政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应返还罚款,并赔偿吊销营业执照(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
(2)非赔偿性责任
主要方式有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履行职责、纠正或变更不当行政行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如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对集中采购机构业绩的考核,有虚假陈述、隐瞒真实情况的,或者不作定期考核和公布考核结果的,应当及时纠正。
2、作人员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
篇2
法律责任规范是以法律权利规范和法律义务规范为生成条件的,任何法律责任规范,如果不与权利规范、义务规范相匹配,那么,势必造成法律规范的制度缺失,其结果是直接影响法律的运行效果。
近期我国颁布的《社会保险法》是一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法律。每位公民在这部法律中,能找到自己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怎样依法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部法律是我国宪法赋予国家的政策性义务的体现,这种义务不像给付义务那样直接提供物质利益或者与利益相为的服务,而主要是要求国家制定法律。而制定《社会保险法》对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明确参保人的权利义务、保障公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有着重大意义。
一、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仍然延续20世记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除特殊工种外,退休年龄一般为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根据《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根据我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我国对退休年龄是强制性的,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必须终止劳动合同。但是许多身体健康、具有专业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劳动者到了法定退休年龄后被单位反聘或继续工作。
二、现行退休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0%,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15年和2020年,这一比例将分别达到15%和18%。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势在必行,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制度有如下缺陷:一、导致增加众多退休人口的赡养压力,社会很难承受这么重的养老负担。据报道上海养老金缺口高达人民币一百多亿。二、人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延长,就业起始年龄就相应推迟,如果退休年龄不相应延长,劳动力的就业年限即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期将会缩短,从而导致人力资本的浪费。三、人们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据统计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又延长了一岁,但退休年龄没有随之延长。四、退休后边拿退休金边再就业,有违养老金制度设计的初衷,造成本来紧缺的养老金被不恰当的使用。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居民退休后再就业率高达33%,退休后大规模地再就业,退休者边工作边拿退休金,使得退休金演变成一种工作以外的额外福利。五、妇女界要求男女同龄退休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退休年龄,劳动者、用人单位都无权选择。从法律角度来说,这种退休制度属于“义务模式”。目前我国经济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退休年龄制度也有必要进行模式转化。
三、从法定退休制度“义务模式”向柔性退休“权利模式”转移
有必要对现行的退休制度进行改革,从现有法定退休制度的“义务模式”向柔性延长退休年龄的“权利模式”转移。允许劳动者在退休年龄,退休方式和退休收入方面具有某种弹性,成为较为灵活的退休制度。国家可以设定一个退休年龄的最高线,即最高退休年龄线。劳动者一旦达到这个年龄,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强制性退休。在这个框架下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人身体情况、个人意愿制定柔性退休年龄。这样不但可以缓解社保支付压力,还可以更好的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上海于2010年10月开始试行《企业各类人才柔性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的试行意见》,试行企业人才延迟退休制度,对退休年龄实行以政策的形式、 针对不同人群进行柔性调整,被称为 “柔性退休”模式。他们提出,延迟退休年龄男性一般不超过65岁,女性一般不超过60岁。并将本市各类人才纳入柔性延迟申请领养老金的范畴内。其它城市也有部分人到了法定退休年龄,根据本人提出申请可以延长退休年龄。体现了由义务规模向权利模式的转化的开始,即将退休设定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就是在国家制定的退休制度的框架下,具体什么时候退休的问题交由市场决定。
篇3
中图分类号:D915.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18
关于宪法权威的认识一般都认为包括三个层面上的权威:法律上的权威、道义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权威[1]。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宪法权威是其他法律法规制定的根据,也是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从传统的法理观念看来,宪法权威的形成是基于宪法自身的至上性和强制性的法律属性,法律规则的规范性基础来源于其强制性,然而宪法权威的形成不必然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或宪法自身赋予的至上性,公民内心对于宪法的认知和认同状态对于宪法权威的形成应当同样重要,并且是宪法权威形成的关键因素。
一、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默示的认同
在传统的法治理念和规范视野内,在法律规则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法律规范有着明确的认识,并确定应当遵守法律,法律规范作为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其正当性来源于法律的规范强制性,而由法律规则所构建的规范秩序则是立足于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和强制心理效果,在分析法学的视野中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制裁或者强权,法律的本质是靠强制制裁执行的者的命令[2]。法律的强制性是其成为社会基本规范的原因,社会秩序的建立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社会的其他事务和制度的建构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参考并在法律的轨道内有序运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被确认为最为优化的社会治理方案,支撑法治社会秩序存在和发展的是法律的形式和规范,并以国家对法律的保障和法律规则的强制性为基础。
法律规范的存在使得社会秩序的形成更具稳定性,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由美国所确立的政体成为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的模式,宪法自此被认为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最基本的法律,美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使得秩序成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蓝图。然而在秩序的图式中必然有着对基本法律即宪法的形式强化,形式上的宪法规范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形成,法治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因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以强制力保障其内容得以实现,而具备了成为维护和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因素。在现代国家,由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宪法,因而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人们对于宪法的认知基础上的,基本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则是来源于人们对宪法的认可。麦考密克在其Institutions of Law一书中所例举的“排队”例子说明了规范性秩序的产生基础,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在于一种非正式的规范性实践,而这种非规范性实践进一步构成了正式的法律秩序的基础,麦考密克认为人们之所以自觉地排队,正是因为这些行动者具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并“相信”别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于是一种依赖于共同信念的规范秩序得以形成[3]。
在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理论看来,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规范性来源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不成文的T例,一种对规范相互期待的信念,以此共同信念的实践就形成了一种默示的规范。与传统的社会秩序形成理念不同的是,制度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不在于者的命令或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而是来自于社会成员对于规范相互期待的认同意识,支撑社会秩序得以存在的是一种默示的规范和对此的默示的认同[4]32,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其所欲形成的秩序的基础应当是公民对于宪法规范的一种默示的认同。
二、立足于默示认同基础上的宪法权威
一般认为宪法权威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5],还有人认为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6]。从此种观念看来,宪法权威应当通过其在实践中的切实运行予以体现,同时在具体的宪法实施中体现其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地位,从而彰显其权威性。然而宪法权威之所以能获得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公民对于宪法规范的默示的认同,这种默示的共同观念构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得以成立的基础,此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有些许类似,但不同于社会契约的理论假设前提的自然状态的描述和公民让渡权利组成政府实现个体的联合[7]。立足于默示认同基础上的宪法权威是一种观念即公民共同接受“政府有权进行管理,公民应该服从政府和政府制定的法律”的共同观念,公民与政府共同的认同意识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默示的惯例,建立在默示认同基础上的惯例取得了对宪法和政府管理的承认,由此宪法才获得了其构建社会秩序、在社会的实践运行中取得最高的地位和法律效力。
法律规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公民的默认认同意识,基于此,宪法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核心,其所确立的秩序必然也是以公民对于宪法规范所具有的默示认同的心理,建立在默示的认同之上的惯例对宪法予以承认,宪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都依赖于此种简单的认同观念:足够多的公民相信其他公民也会像自己一样认同宪法的观念。从这个方面来看,宪法权威应当是以公民对于宪法自觉形成的依附感,并将其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本准则,由此也成为整个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基础。
默示的认同是一种内化于心的信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国家以强制力作为后盾而推行的法律规范,基于默示的认同而渐进式养成的惯例或规则在压迫式的服从方面的阻力是较小的,公民个体对于规则或是事物的认知与赞同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公民个体会自觉在规则的指引下进行行为,并不会逾越规则的限度,个体的自由意志是行为的前提,默示的认同将个体的自由意志统一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内,进而使得一个区域内的共同体有了较为合理的依靠和支撑。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律规则,基于社会契约而形成的权力与义务规则对于一定区域内共同体的公民都是普遍适用的,而宪法的有效性适用则依赖于共同体内的公民对于该规范的认同,其权威性的基础应当是共同体内公民对其内化于心的默示的认同。
三、宪法权威得以形成的因素
制度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性的来源或是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是不同于凯尔森的实证分析法学抽象假设――“规范性基础”,也不同于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而是一种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默示的认同,基于相互期待和如何行为的“规范”,默示的规范成为了法律秩序的最终来源[4]4749。宪法同样如此,立足于默示的认同的宪法权威是在公民对于其他公民默认同样会和自己一样行为的前提之下形成的,宪法权威的形成也意味着宪法所欲构建的法治社会的秩序的确立,然而以默示的认同为基础的宪法权威是不同于主流法学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而是通过把庞杂的法律规则内化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并在此之上构建法治秩序。因此宪法权威的形成必然是另外一种路径,宪法权威的形成应当是其内生因素的使然,包括时间上的累积和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性“遗忘”。
(一)时间的累积――内生因素
以规范为核心的法律理论看来,法治的形成和实现必须依靠民众对法律规范的了解和认知,并应当将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而被信仰,国家的法律的核心地位是个体经过“理性的反思”而建立的,建立于法律之上的秩序因而具有个体理性建构的色彩[8]。宪法权威同样应当是以公民对宪法规范的认知和了解为前提,通过个体理性认知到规范秩序乃至法治秩序的形成,宪法权威在此过程中也自然得以形成。与此理性化的秩序假设不同的制度法学理论认为,秩序的形成包括宪法权威的形成以非理性为基础,但是同样要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公民对于规范的认可并进而转化为个人行动,遵守宪法规范所确立的秩序,但是这一认识是非理性的,是公民自觉的过程。
无论是主流法学理论还是制度法学理论,其都认为法治秩序的形成包括宪法权威的形成且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无论是主流法律理论认为的从对规范的认知到做出相应的行为的过程,还是制度法学理论认为的从规范到默示认同的惯例的转变,法治秩序的形成都依赖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法律和秩序的形成马克思也指出:“只要作为现状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9]所以法律的形成或是秩序的构建无疑都是一个长时间的社会交往的产物,时间是法律的内生变量之一,同时也是宪法权威的内生因素。
因此宪法权威的形成必然需要时间的积累,时间的内生因素决定着宪法权威和宪法所欲确立的法治秩序的稳定性,法律在社会中被使用的时间越长,其被知晓的可能性就越大,个体的认知也就成为可能,无论是从社会风俗到法律规范或是直接的习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性都会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
(二)社会性的实践――外生因素
制度法学理论认为规则并不是始终以规则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被公民个体所意识到,规则会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使用,在此过程中有些会逐渐转化为个体的习惯,而规则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会与社会性的实践相结合,与宪法权威形成的实践内生因素不同的是,这一社会性的实践是宪法权威形成的外生因素,其通过将规则外化为个体的习惯并形成稳定的内心认同感。
法律必须处于社会生活之中才会展现其规范性的一面,并使其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因素更为明显,相对于时间的内生变量,社会性的实践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通过社会生活将宪法规则在社会中的生命力彰显,以实现法律规则本身存在的目的,法律规则融入公民生活之中,融入公民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中,会使得社会个体对法律规则或法律制度更容易承认和接受,而离开了日常生活中公民的行为实践和态度的支撑,宪法权威将会是被架空和边缘化的概念而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4]7275。因此,作为宪法权威形成的外生因素,社会性的实践会使规则更加成为自然,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的习惯,将宪法规则乃至法律规则嵌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习惯之中形成对于宪法的认同,宪法权威也就自然得以形成。
四、超越规则之治――从规则到习惯
(一)规则之上的习惯
从法的起源观念看来,法律最初的状态为习惯,其次则是社会风俗和惯例,者下达的一般性命令即俗称为法律[10],从成文法到不成文法,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演变为法律,通过法律规则实现规则之治成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法律规则源自习惯,在法律取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之后,遵守法律则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法律规则的权威性也因社会成员的认同而愈加巩固。
法律规则从习惯中衍生而来,此种习惯是社会成员个体或大多数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并被固定化而成为特定群体共同认可的行为模式,这时的习惯是规则之前的习惯,而在规则之后的习惯则是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公民对于规则熟悉的基础上,在面对现实实践时无意识或下意识而作出反应的行为,这是公民对规则经过内化之后形成的一种默示的认同习惯。所以在制度法W理论看来,社会秩序乃至法治秩序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就是对规则内化之后的习惯,公民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了解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公民已经将法律规则内化为自身的习惯,出于个人的习惯性思维和意识而做出相应的行为。法律规则只是公民学会守法的工具,一旦公民学会了如何正常行为,就不会去思考是法律规则让他们如此行为,当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形时,他们就会进行无意识的处理,而不会再去考虑法律规则是如何规定的,规则在此时甚至被“遗忘”,最终依靠习惯形成了社会秩序,此时的习惯超越了法律规则,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规则之上的习惯比规则之前的习惯更具有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宪法秩序或法治秩序因而更加稳固,而宪法权威也自然形成并获得公民对于宪法的尊重。
(二)个人习惯与宪法权威
人们对并非出于设计的规则和惯例的遵守,亦即对传统规则和习俗的遵循,乃是自由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11]。惯例或习惯的确立使得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更为自由,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的结果,在规则之上的习惯为社会个体所习得并成为公民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个人习惯的确立和增长对于宪法的合法性的确立和法治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主流法学理论对于个体对规则理性认知的假设过于理想化,公民不可能认知全部的法律规则,也不会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法律规则。所以个人习惯的获得是公民对于宪法乃至法律规则体系的非理性认知过程,这一从规则到习惯的转变的前提就是公民已经认同了整个法律体系的合法性,由此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对社会秩序的构建超越了“规则――行为――秩序”的简单模式,从规则到习惯的内化过程使得个人习惯成为公民行动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而规则又具有了习惯的特征,习惯化了的规则构建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对于习惯化了的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则,不加思索地按照规则去行为,毫无疑问,这样的宪法秩序是非常坚固的。
法律规则的存在是为了影响公民个体的行为并由此而形成法治秩序,而习惯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补充,但是规则之上的习惯却不仅仅是规范社会秩序的补充,经过了从规则到习惯的转变,个人习惯成为了公民无意识的行为思维方式,规则已经内化为公民的思维意识之中,宪法的至上性和最高性已成为一种信念,基于默示的认同而形成的宪法权威使得公民更加遵守宪法,宪法秩序的形成也水到渠成。个体习惯“取代”规则的同时也赋予了规则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在公民无意识的思维并行为的过程中“规则”被遗忘,以个人习惯为特征的宪法秩序是稳定的法治秩序,而宪法权威也在此基础上更加稳固。
五、结语
宪法权威的形成与树立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树立宪法权威。法治秩序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法秩序的形成过程,实现法律规则之治并不仅仅是依靠法律背后的国家者的命令抑或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也包括公民对于规则或宪法的一种默示的认同,基于公民内心对于宪法的信念形成的一种认同,由此使得宪法权威得以确立,默示的认同过程是一个从规则到习惯转变的过程,具有个人习惯性的规则才是“活法”,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实现法律规则本身存在的目的,在以个人习惯为特征的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中,法律规则之治亦自然形成,而宪法权威则愈加稳定。
[参考文献]
[1]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90.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5.
[3]Neil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An Essay in Legal Theory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6.
[4]李锦辉.规范与认同:―制度法学理论研究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5]胡维翊.宪法修改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M]∥S崇德.宪法与民主政治.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56.
[6]何华辉,李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234.
[7]卢梭.社会契约论 [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72.
[8]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3.
篇4
现代社会的高度复杂性促使法学理论的创新;法律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便应运而生。“自创生”最初是由生物学家提出,用以描述活体细胞的自我维持和自我生产。德国学者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用这个概念来比拟社会系统,进而开创了法律自创生理论。
法律自创生理论认为:法律是现代社会功能分化所产生的社会子系统,通过“合法/非法”的分辨来维持自身系统的运行和生产,因此“法律的合法性来自于法律本身”;系统之外(包括其它社会子系统)称为“环境”,法律系统对于社会环境“在规范上是封闭的,在认知上是开放的”;法律系统与其它社会子系统(如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等)是“结构耦合”。的关系,法律“通过调节自身来对社会进行调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法律自创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除卢曼外,还有德国法学家图依布纳 (guntherteubner,1944-)。
由于法律自创生理论对于解决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问题有独到之处,因此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但自创生理论的“后现代语境”又似乎与当下的“现代化”有听抵牾。其实,若将法律自创生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法学谱系中考察,则会发现这种“新理论”仍然是以主流的规范法学为基础。
在本文中,“规范法学”指19世纪奥斯丁开始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对法律自创生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20世纪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尤其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和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
二、卢曼:在“纯粹法学”的基础上前行
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被称为是“凯尔森‘纯粹(法学)理论’的女儿”,由此可见两者的密切联系,卢曼在 “纯粹法学”的基础上对“规范”和“法律”做了新的分析和诠释,同时也试图对凯尔森理论的问题进行全新的回答。
(一)法律的“实证性”基础
首先,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的理论出发点是和“纯粹法学”一致的,即规范与事实、当为(sollen)与实存 (sein)的严格区分;也就是将实证性(positivitat)作为法律的根本前提——这也是规范法学最基本的理论预设。
在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中,法律系统的内部是一套“合法/非法”的识别机制,法律就是通过这种识别机制来发挥作用、调节社会关系;而“这种系统的运作既不是由(外在)环境所输入的,也不把这些运作向(外在)环境输出”。尽管卢曼的术语是新的,但这种将法律独立于其它社会因素之外的理论预设却是和凯尔森一脉相承:法律和信仰、道德以及政治间有一条清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现为美国休斯敦大学荣休教授的赫格特 (janes e.herget)所评价的:“卢曼的理论具有和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极为相近的一面,这二者都将法律过程进行‘纯净化’,排除法律对其它因素任何程度的依赖。”
但是,卢曼显然并不满足于法律的这种“纯净化”。他认为“首先要进行的区分不是规范和价值的区分,而是系统与环境的区分。”而“系统——环境”的区分较之 “纯粹法学”有着更丰富的内涵:法律系统和环境(包括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是“结构耦合”的;系统的运作是内部过程,但系统之间会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法律也是以此发挥作用的(例如法律系统中税法的运作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系统、金融系统等)。这就是法律自创生理论的重要命题:“法律是一个在规范上封闭而在认知(对环境的反应)上开放的系统”——如果说,“纯粹法学”提供的是一幅“法律规范”与“其它社会因素”严格区分的静态图景,那么法律自创生理论则描绘了法律规范在自我运作的同时与其它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动态图景。这一动态图景不但体现在法律规范本身,而且贯穿整个法律自创生理论,以至于赫格特称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为“动态的实证主义”。
(二)法律的“自我生效”
基于法律的实证性,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提出法律系统的“自我生效(selbst—bestatigung)”,即“法律的效力产生自法律系统本身”,“只有法律才能改变法律…… 法律系统依据法律事件,也惟有依据法律事件,而使其不断地存续、繁衍和再生”。
“法律的效力来自于法律本身”显然带有浓厚的规范法学色彩。尽管早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如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但是这种思想随着法律实证性的进一步展开而逐渐被规范法学所否定;无论是凯尔森的规范等级序列还是哈特的第二性规范,都是试图在法律体系内部解决法律的效力问题。凯尔森的“纯粹法学” 在将法律规范“纯净化”之后,又构建了一个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将规范的效力归因于更高一级的规范,这样层层授权,最终形成一个基于“基本规范”的等级体系。这种规范效力等级体系为法律自创生理论开辟了可回旋于法律体系内部的理论空间,台湾学者洪镰德甚至认为凯尔森已经“有法律自生自导的意味……(只是)法律自生 (即自创生)观不够完整”。
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同样将目光投向法律系统内部,但是法律系统的基本元素不再是法律规范,而是规范的交互过程(kommunikation);这种交互过程是系统的运作方式,而规范的效力则来自干系统内部不断的运作:
像所有的自我再制的系统一样,法律系统的运作是在不断地自我往复中的。为了使其自身能够具有作为法律运作的资格,它必须找到它在上一层次所作的、以及它需继续怎样作,才能有资格作为法律进行运作。
在这里,法律自创生理论提供的是一种法律规范首尾连贯的循环,一种不需要中心、也不需要位阶的交互与沟通;法律的效力也就源于这种循环性。由此,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表现出与凯尔森乃至整个实证主义传统的重大差别:
奥斯丁(austin)。涂尔干(durkheim)和凯尔森 (kelsen)为避免循环性并找到法律效力的其它某种基础而竞相尝试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理论。然而,有效性就是循环性——当然,这种循环性需要在逻辑上展开阐述。
于是,法律自创生理论关于法律效力的论述,通常就是像卢曼听说的“判决在法律上有效的根据仅仅是规范性规则,因为仅仅当判决得到执行时规范性规则才有效”——卢曼还特别强调,“在这一短语中,‘因为’一词绝不是一个错误,而是有意这样用”。
(三)法律规范的网状结构
正是由于效力的循环性,法律自创生理论在规范结构上,也体现出与“纯粹法学”既有联系、也有差异的一面。
根据凯尔森的法律效力观,规范的效力来源于上一级规范,这样层层叠加,直到“一个不能从更高规范中引出其效力的规范,我们就称之为‘基本规范’凡能从同一个基本规范中追溯其效力的所有规范,组成一个规范体系”。
“纯粹法学”这种金字塔式的规范结构为法律的实证分析提供了简明的、理想化的范式。但是这个金字塔的 “塔尖”,即“基本规范”,作为规范效力的最终来源,本身却没有来自于规范体系内部的效力依据,同时也要避免成为道德那样的先验因素,而视为“社会事实”之类的经验因素同样也有损其“纯粹性”——严密的金字塔式规范结构在这里留下了理论上的瑕疵。
卢曼的法律自创生理论继续着“纯粹法学”构建规范结构的努力,但抛弃了金字塔式的结构,代之以“基于效力循环性的网状结构”、根据这一理论,法律系统中任何规范的效力都来自于其它有效的规范。例如法官根据法条进行判决,如果按照凯尔森的规范序列,判决的效力乃是源于法条;但在实践中,判决的功能就在于体现法律效力,从而彰显法条——因此,在法律自创生理论看来,判决和法条不是演绎或因果的关系,而是循环的、交错的,互相指涉的,没有高低位阶之分,当然更加无需一个最高的效力来源。用卢曼自己的话来说:
有效性是系统不断运作的产物。它的稳定性仅仅得自于最低限度可能性的预期信息持续运作的网状结构……对规则等级序列的改变使得我们可以放弃规则有效性来源于更高一级规则的观念。网状结构是法律系统的内部结构,是其在“规范上封闭”的微观描述。而法律系统同时电是“在认知上开放” 的,法律规范的运作也会与外在环境有所关联。再以往官的判决为例,如前所述,判决和法条之间形成循环交错的网状结构;但另一方面,因事实(环境)认知的原因,法官可能有所蒙蔽、有所偏颇,以致误引、错引法条,造成网状结构的错位。
于是,卢曼这个“在规范上封闭、在认知上开放”的规范网状结构避免了“纯粹法学”关于“基本规范”的理论瑕疵,同时也打破了金字塔式完全封闭的结构。正如季卫东先生评价的:“尼克拉斯•卢曼在凯尔森的思路上继续前进,似乎发现了在规范与事实的边缘上存在的‘曲径通幽’的门扇。”
三、图依布纳:对哈特的借鉴
如果说,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产曼“显然不打算对法官、法律家或法律从业者的法律工作提供帮助”,那么身为法兰克福大学私法和法律社会学教授的图依布纳就更多地以法学家的目光对法律自创生理论进行审视,这就使得法律自创生理论更加密切了与规范法学(尤其是哈特的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关联。
(一)法律超循环中的“半自创生系统”
如前所述,卢曼借用生物学“自创生”的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法律,用“循环的网状结构”来解释法律的有效性。但是,这种借用遭到生物学家的反对,生物学家认为只有生命体才具有“自创生”的特征,用“自创生”来比拟社会并不合适。对此,图依布纳回应道:
与生物的自创生相比,社会和法律的自创生通过其自然发生的特性来区别。需要形成新的和不同的自我关联循环以便为更高层次的自创生系统提供基础。
图依布纳所提供的“新的和不同的自我关联循环”便是他的“法律超循环”理论: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包括行为、规范、过程、特性等,这些组成部分本身的自我循环构成了法律的自治;当这些循环过程之间也形成
转贴于
循环,即联结成“超循环(循环的循环)”时,自创生的法律就产生了。
既然只有“超循环”是自创生的,那么“超循环”下的 “循环”就既非自创生、也非完全没有自创生,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这首先遭到卢曼的反对:卢曼认为,自创生的概念为“不可改变的确定性”,是一种“全有或全无”的过程;法律要么是自创生的,要么就不是,不存在“半自创生系统”。
于是,图依布纳将眼光转向了哈特的“第二性规则 (次要规则)”。哈特批判了奥斯丁的“法律即主权者命令”的理论,将法律规则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其中“第二性规则”包括“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 “审判规则”,在规则体系中分别承担规则引入、规则改变和规则适用的功能,以使“第一性规则”(即规定权利和义务的强制性规范)正常运转。哈特还特别强调,“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是。法律科学的关键”,“法律制度的中心”。
哈特的“第二性规则”也就成为“关于规则的规则” 图依布纳对其功能进行了新的阐释:
当法律系统的一个或更多的组成部分通过自我描述和自构成变得独立的时候,“部分自治法”的临界阈值就达到了。最为人知的法律自我描述的例子是哈特“次要规则(第二性规则)”的思想……用我们的术涪来说,法律沟通出现于对法律沟通的处理 ……它们形成控制其它结构的选择的结构。……次要规则的机制不能等同于法律的自我创生。法律还没有彻底地再生产它自己。“次要规则”只是构成采用法律结构自我描述形式的众多自我关联循环中的一种。
换言之,哈特的“第二性规则”就是图依布纳所说的 “半自创生系统”,是法律“超循环”理论的关键一环;但是,哈特“提供的是一个自我关联关系的不完整图像”,因为整个法律系统包括法律过程、法律规范、法律行为,法律学说等,“第二性规范”构建的是其中法律规范的自我关联和自我描述、即“法律规范的循环系统”。只有当其它部分也形成循环系统,并且这些循环系统之间也进行循环,法律的超循环(即自创生)才真正形成。尽管哈特的“第二性规范”只是法律系统中若干循环系统之一,但作为“半自创生系统”的一个理论模型,对于图依布纳的“超循环”理论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图依布纳将法律的自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 “‘社会地弥散法律’的初始阶段,法律话语的要素、结构、过程和边界与一般社会沟通的那些东西完全一样”;“部分的自治阶段”;“自创生阶段”、“图依布纳并进而考虑 “把这个模式适用于法律史和法律人类文化学并预测它对法律进化的可适用性”。在这里,图依布纳显然是试图将法律“超循环”理论与客观的法律史相对应,即法律迈向自创生的三阶段都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存。这点又与卢曼不同:卢曼的自创生系统摇摆于“理论假设”和“客观存在”之间,也有批评指其仅为理论上的想象而不能为经验所证实。
相比之下,哈特的“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相结合”的规范结构也带有法律进化的色彩:哈特认为,在那种依靠血亲关系和共同感维系的小型、简单的原始社会 (前法律社会)中,仅存在第一性规则;在复杂的、大型的社会中,第二性规则才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意味着 “从前法律世界走向法律世界”。。如果将哈特的这一进化图景与图依布纳的“法律自创生三阶段”相叠合,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的密切关联(见表一):
(二)通过反身法的社会调控
“通过反身法(reflexive recht)的社会调控”也是图依布纳与卢曼的理论分歧之一:传统的法社会学认为法律的功能之一便是社会控制;但卢曼认为,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各个功能系统都是封闭的,能够“控制社会”的实体并不存在。图依布纳认同卢曼关于功能分化的理论,但是认为在法律自创生理沦下,社会调控还是有可能的,调控机制便是“反身法”,即“通过自我调控来实现社会调控”——图依布纳认为“反身法”是法律自创生的结果:首先是法律内部(包括法律程序和法律实体)的自我描述,自我指涉和自我维系,形成一个自治的功能系统(即 “法律自创生的超循环”);正如卢曼所认为的,这个功能系统和政治、经济等系统之间是封闭的,而图依布纳则强调这些功能系统之间有着互动关系,“就像互不往来的 ‘黑箱’,其中每个黑箱都知道其它黑箱的输入和输出,但这些黑箱内部如何将输入转化为输出则仍是模糊的”,他更借助“黑箱技术”阐述了法律系统和其它社会子系统的关系:
“黑箱技术”……试图通过间接的“程序上的”路线将内部模糊造成的问题串接起来。当若干黑箱的行为综合起来,它们的关键就不在于那些不可见的内部过程,而在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于是,黑箱之间的互动过程就是互相“透明化”的过程;这就是说,黑箱之间发展出的互动关系在规律性方面达到了透明。
法律系统通过这种互动关系,便可以实现社会调控的功能——在这里,法律不是直接地对社会现实进行干涉,而是通过自我调控(即“反身”)来影响社会其它方面。于是,法律系统自我调控的机制就至关重要。卢曼以“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码来描述法律系统的内部状况,而图依布纳更从规范法学的法律形式主义中看到了这种自我调控的端倪:
法律形式主义还是法律自我指涉性的学说表达。它是在决定和支配之间循环关系的社会抽象化的一个特别类型;并且通过这一媒介,法律自我再生产出其标准的元素……在形式化的法律中,实质性法律推理在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是基于其形式性:其对社会自我再制的简易化。
尽管图依布纳随后又强调法律形式主义对于反身法来说是不充分的,但是他明确反对将法律形式主义视为 “纯粹基于不考虑实际结果的术语体系的法学”,而这显然带有哈特“内在观点(intemal point of view)”的色彩:
哈特的“外在观点”其实与奥斯丁的“主权者命令”或凯尔森的“上级规范授权”并无本质区别,但“内在观点” 却为法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1)“内在观点”打破了规范法学“从规范到规范”的格局,引入了人类行为和内心认同作为分析对象;(2)“内在观点”提示,人们对规范的观察也会指向自身行为,形成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的自我指涉;(3)“内在观点”提供了一个对法律体系进行反思的简单反馈机制,正如哈特所说“如果这个制度是公平的……它可以获得和保有大多数人在多数时间内的忠诚(即‘内在观点’),并相应地是稳固的”,否则便相反。
而以上三点,正是“反身法”的理论起点。正是因为有哈特的“内在观点”,图依布纳才能在规范法学的法律形式主义中找到“反身法”的基本元素,在与卢曼分歧之处得到法学内部的支援;也正因为如此,图依布纳强调反身法思想具有“规范性”和“分析性”。——当然,与哈特相比,图依布纳在法律的反思性、自我指涉等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了;图依布纳的“通过反身法的社会调控”既不同于卢曼对“社会控制”的消极,也不同于法律的直接规制;反身法“通过调控自身来对社会进行调控”的思路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图依布纳得以将其应用于对社会团体、公司治理、法律全球化等具体法律问题的研究。
四、结语:“中心”与“边缘”
篇5
作者简介:朱伟达,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
在《法律的概念》(The Concept of Law) 一书中,哈特(H.L.A.Hart)构建了一种描述性(descriptive)和一般性(general)的法律理论(legal theory), 这种法律理论将法律(Law)或者说法律体系(Legal System) 的核心(centre)领域 描述为是由初级规则(primary rules)和次级规则(secondary rules)相结合而成的规则体系。初级规则是指科以义务的规则,例如刑法中禁止杀人的规则;次级规则则是指授予权利的规则,例如授予议会修改法律的权利的规则。 次级规则由三种规则组成:承认规则(rules of 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s of changes)和裁判规则(rules of adjudication),分别是为了弥补初级规则的三个缺陷:不确定性(uncertainty)、僵化性(static)、社会压力的无效性(inefficiency)。 其中,承认规则与凯尔森的“基础规范(basic norm)”有些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承认规则因其重要性可以被称为哈特所描述的法律的基石 。接下来,笔者试图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承认规则,以期对其有较为全面的阐释。
一、承认规则的本质
承认规则的本质问题实质上是关于承认规则是什么的问题。在书中,哈特对于此问题的回答是,承认规则从内部视角(internal points of view)来看是一项规则(rule),因为它提供了识别初级规范的标准,从外部视角(external points of view) 来看是一个事实(fact),因为此时它表现为接受并适用这种标准的活动。 因此,承认规则具有事实和规则两个面向。但是这两个面向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答案是,哈特所言之“规则(rule)”有其特殊的本质,即实践性(practice),因而哈特称其为规则的实践理论(the practice theory of rules)。 具体来说,规则是一项被接受(acceptance)并遵循(follow)的实践,这种实践会因着采用不同的视角进行描述、解释或阐明而展现不同的面向。因而,承认规则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初级规则予以承认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接受并应用识别标准的实践。对于这种实践,如果从内外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看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即规则和事实面向。综上,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事实和规则两个面向都包含在这一本质中。承认规则的实践性还与其开放性存在联系,下面就分析下承认规则的开放性。
二、承认规则的开放性
承认规则的开放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是开放的,二是向什么开放。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首先,从法律的开放性入手。法律的开放性是指存在需要法庭或者官员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不同相对抗的利益予以平衡的行为领域。 法律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是一种规则,因此法律的开放性就是法律规则的开放性,而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的一种也就秉承了开放性。其次,可以从规则的实践性入手。前文已经论述而来法律规则的实践性,也论述了承认规则的实践性。由于语言的局限性和人类理智的有限性, 使得人不可能完全预见未来会发生什么,进而事先做全面的安排和规制。即使预见了,所使用的语言的局限性也会使将来对规则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不确定性,这也就给实践带来了不确定性,所以实践本身就意味着开放性,法律的实践也就存在开放性。由此,承认规则便具有了开放性。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承认规则开放的对象是道德、政治等非法律领域,书中着墨最多的是承认规则向道德的开放性,主要出现在哈特对法律与道德(moral)之关系 的论述中。哈特认为法律与道德两个命题是分离的,但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的主要表现是一些法律规则源于道德规则 以及可以用道德来评判法律 。因而在识别什么规则是初级规则实践中就可能会受到道德的影响。承认规则开放性的极端便是自身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前法律社会(pre-legal form of social structure)”或者说“简单的法律体系(simple system)”中,此时只存在初级规则。 当然也存在着很难确定承认规则是否存在或者存在什么样的承认规则的情况,例如国家处于革命、敌占或者失控状态。
三、承认规则的效力
承认规则的效力(validity)问题也与其本质息息相关。前面已经解释了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作为一项实践,也就不存在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只有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 说一项实践是有效的或者无效的是没有意义的,它一旦存在,就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四、承认规则与原则
在正文中哈特并未提及原则(principles),只是在后记中,为了回应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批评,他才对原则问题进行了解释,主要是回答承认规则能否识别原则的问题。首先,哈特阐述了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他认为规则与原则的区别只是程度上(degree)的区别,并无德沃金所言之实质上的区别,即依此所得出的结论的确定性程度上的差异,因此,他将规则称之为“near-conclusive rules”,将原则称为“non-conclusive principles”。 进而,哈特认为承认规则可以识别原则。哈特解释道,原则不仅可以而且也必须(necessary)从系谱(pedigree)上来识别, 而不是像德沃金所言,需要通过对内容(content)通过诠释性的检验标准(interpretive test)来识别。 因为即使在适用诠释性检验标准之前也必须先确定权威性的法律渊源,而这一步骤必然只能依据系谱。 而通过系谱识别就是承认规则的适用方式。 五、 与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之比较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的注释部分区分了承认规则和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之间的四点不同。 首先,承认规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事实,而基础规范则是一个拟制(hypothesis)或假设(assumption);其次,承认规则因是一个事实,所以也就不存在效力问题,而基础规范的效力源于预设(presuppose);然后,基础规范总是具有相同的内容,即“宪法或那些‘制定第一部宪法的人’应得到遵从”。这是一项独立于现实的规则。哈特认为承认规则是接受并应用某项识别规则的实践,因此并不表现为一项凯尔森所言的独立的规则,也就不具有如同基础规范这样一致和简单的内容。最后从承认规则不会推导出内容上相对立的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结论,而根据基础规范,内容上相对立的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不可能同时有效。
上述差异根本上源于基础规范与承认规则的不同本质。因此笔者结合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 对两者的本质上的差异再作一个补充分析。
凯尔森在《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一书中明确了基础规范是一项被假设的最终规则, 其效力是被预定或假设的。 根据韦恩-莫里森的研究,凯尔森起初只在将基础规范的作用限定在认识论上,将其作为一个康德式的思维范畴,但1963年后,凯尔森改变了立场,将其视为一个虚拟意志的虚拟产物。 因此,基础规范的本质是一个理论假设的论断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由此引出的两个疑问却是值得深思的。第一个是,为什么一个假设可以成为“法律科学”的基础?第二个是,由此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对于第一个问题,凯尔森本人的回答是:“基础规范只是对法律材料的任何实证主义解释的必要的预定。” 笔者的理解是,实证主义否定、摒弃自然法,同时也不认同法律现实主义,以此保证法律本身的自洽与纯粹。但单纯逻辑与概念的力量无法提供最终的理论根基,因为逻辑上可以对事物进行无限的追问。而实证主义又不愿从前面提到的两种在理性之外寻求根基的方式,所以,只有而且也必须采用假设的方式才能保证理论的完整与自洽。这种假设在笔者看来也就成了凯尔森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终极信念”。
由此带来的第一个后果是,凯尔森的整个法律理论的科学性遭到质疑。 在许多人看来,科学是不能建立在假设之上的。因此凯尔森的法律科学的科学性是可疑的。虽然争议的双方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可能也有分歧,但至少在一部分人的理解中,凯尔森的法律科学是“非科学”。第二个后果是,法律由此便成了一个“封闭的城堡”。法律向现实、超验、先验领域关上了大门,虽然关得并不严密, 但至少让法律看起来是独立而自洽的。这种封闭,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是使法律变得“纯净”了,不会混杂过多的非法律“杂质”了,从负面的角度来评价,就使法律失去了“活力”,变得“僵化”而无法发展。在笔者看来,理性毕竟是有限的,人类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世界,终极的根基是无法扎根于理性的土壤中的,必须在理性之外寻找根基。实在法作为人类理性的产物亦是如此。实践也证明了凯尔森所代表的实证主义法学的缺陷。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法学的沉寂多少与其封闭性有关,而哈特对实证主义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青春的方式就是打破实证主义法学体系的封闭性,使其向现实与道德开放。虽然这样一来,法律的自洽与独立又一次受到了冲击,但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种开放性根本上便是由承认规则的实践本质所决定的。综上,凯尔森的基础规范本质上是理论的假设,虽然其内容取决于事实,而哈特的承认规则本质上是实践,虽然其具有规则的面向。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承认规则的本质是实践,与凯尔森的作为理论假设的基础规范不同,其具有开放性,也不存在效力问题,同时它依然可以识别法律原则。
注释:
此语的依据来自后记的“The Nature of Legal Theory”一节,哈特说:“My aim in this book was to provide a theory of what law is which is both general and descriptive.”(p239)此句直接点明了哈特的法律理论的本质。
笔者以为哈特在相同意义上使用Law和Legal System两词的。因为哈特在第五章(Law as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中将“Law”的核心领域视为由初级规则和次级规则组成的规则体系,而在第六章(The Foundations of A Legal System)中将两级规则的存在作为“Legal System”存在的核心标准(非绝对标准),所以两者应当是哈特所描述的同一对象。也可参见“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is at the Centre of a legal system”.99.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is at the centre of a legal system;but it is not the whole,and as we move away from the centre we shall have to accommodate,in ways indicated in later chapters,elements of a different character”.99. H・L・A Hart.The Concept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81.哈特在此处概括性地描述了两类规则的内容。
关于两类规则的详细论述请参见第五章(Law as The Unio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Rules)。
笔者称其为基石的原因是,承认规则不仅如下文将要谈到的那样,提供了识别初级规则的标准,而且承认规则同样存在与其他两项次级规则中。可参见第94到97页哈特对三种次级规则的阐释。
关于内部视角(internal points of view)和外部视角(external points of view)以及内部陈述(internal statements)和外部陈述(external statements)的问题,哈特并未专章或专节讲述,但这两组概念在哈特的法律理论中十分重要,贯穿于全书。概括地说,内部视角是指从实践者或者参与者的视角来分析,所作的阐述便是内在陈述;外在视角是指从观察者或者旁观者的视角来分析,所作的阐述便是外在陈述。
后记中第三节(The Nature of Rules),该部分一开始,哈特便总结性地阐述了规则的实践理论.254-259.
在第七章(Formalism and Rule-Scepticism)中,哈特批判了法律形式主义和规则怀疑主义,这两种观点也正好是关于法律开放性的两种极端观点。法律形式主义认为法律不存在开放性,而规则怀疑主义则认为法律是完全开放的,因此根本不存在规则。哈特在批判中阐释了规则的开放性,即规则存在确定的核心领域,也存在不确定的边缘领域。而对这对法律开放结构的内涵,哈特说道:“The open texture of law means that there are,indeed,ares of conduct where much must be left to be developed by courts or offices striking a balance ,in the light of circumstances,between competing interests which vary in weight from case to vase.”(p135).
哈特在第七章(Formalism and Rule-Scepticism)中解释了法律开放性的原因,由于法律作为的规则的本质是实践,因此法律开放性的原因也可以被视为法律实践开放性的原因。哈特在书的第128页说道,除了语言的局限性导致法律的开放性,还有一项重要的原因是人的有限性,即人无法预知未来,笔者将其概括为人理智的有限性。
主要是集中在书的第八章(Justice and Morality)和第九章(Laws and Morals),哈特在这两张中主要阐述了法律、道德、正义三者之间的关系。
“No such question can arise as to the validity of the very rule of recognition which provides the criteria; it can neither be valid nor invalid but is simply accepted as appropriate for use in this way.”(p109)。此句中,哈特明确否定了承认规则存在效力问题,其理由是承认规则仅仅是一种接受并适用标准的实践。
“In face of such example of legal principle identified by pedigree criteria,no general argument that the Inclusion of principle as part of the law entail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octrine of a rule of recognition could succeed.In fact,as I show below,their inclusion is not only consistent with,bur actually requires acceptance of that doctrine.”此句中“consistent with”一语,根据前文,笔者将其理解为“可以”,而“requires”一词;根据后文,笔者理解为“必须”。
德沃金将确定权威性法律渊源的规则的实践称为“Preinterpretive Law”,其实质上是一种“共识(consensus)”、“范例(paradigm)”、“预设(assumption)”,而哈特则认为,这种识别法律渊源的规则和实践就是一种“规则(rule)”,即承认规则。
“If it is conceded as surely it must be,that there are at least some legal principles which may be’capt-ured’ or identified as law by pedigree criteria provided by a rule of recognition,then Dworkin’s criticism must be......”。
所使用的译本是:沈宗灵先生翻译的,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法与国家一般理论》。
汉斯・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