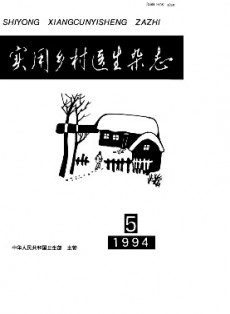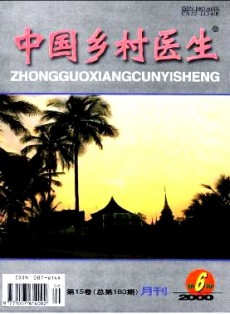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1:26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篇2
⑩徐子沛.大数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4-6.
.cn/gywm/xwzx/rdxw/2014/201407/t20140721_47439.htm,2015-4-10.
{12}石菲.我国电子政务十年发展成就.中国信息化,2011,(12).
{13}道格拉斯・斯诺.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
参考文献:
篇3
二、由于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管理滞后产生的生活污染
小城镇和乡村聚居点的生活污染物因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以及具体管制的不健全,一般直接排入周边环境中,造成严重的“脏乱差”现象:每年产生的约为1.5亿吨的乡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3000万吨的乡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乡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然而,在我国乡村现代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这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环境管理落后于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现象并没有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其对人群健康的威胁却在与日俱增。
三、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够产生的工业污染
受乡村自然经济的深刻影响,乡村工业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为特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不仅造成环境污染,加大了治理的困难,还导致污染危害直接影响到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我国乡镇企业废水和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占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布局不合理,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
由于我国乡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环境污染不仅将迅速“小污”变“大污”,而且已经“小污”成“大害”,给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和弱势群体的农民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应当采取如下措施:
1、加强环境立法,建立健全乡村环境管理机构,明确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水污染防治法》等,对乡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
篇4
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篇5
[作者简介]傅 琼(1972―),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与社会;练 艺(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与社会。(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礼仪文化传承与赣鄱乡村有序发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研究”(SH1608);江西农业大学协同创新招标项目“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礼文化重构研究”(XDNYA1511)
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乡村治理问题的早期探索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税费时代,乡村治理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税赋并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如何治理乡村呢?学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可分为两种倾向。
一是主张通过改造乡村社会来主动适合国家政权下沉及推进现代化的需要。如晏阳初等人认为乡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种教育为内容,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为形式的平民教育构想与实践。[1]以期改变乡村社会落后的面貌,以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卢作孚则在重庆北碚开展以谋民生,保民享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2]因为在他看来,乡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瘫痪与半瘫痪,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乡村社会的财富创造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会落后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单靠乡村社会是很难获取原始资本积累的,所以乡村治理中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国家扶持是乡村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见,尽管晏阳初和卢作孚改造乡村的着力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改造乡村社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二是主张借助传统来重塑乡村面貌,强调国家政权必须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标,以创办乡农学校和自治组织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建设实验。[3]林耀华则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宗族组织的形式与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体系及其作用,强调人类行为的平衡乃是由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的,是任何嵌入乡村的权力都不可忽视的。[4]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是差序格局,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解决乡村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在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5]
(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学者们的早期探索,为后世学者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这其中便包括美国学者杜赞奇。他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辅之以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威特质,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范式。成为与的社区功能研究方法、施坚雅的市场关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统研究方法以及黄宗智的市场-阶级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种分析范式。
其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将国家政权、乡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传统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将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中,还原乡村社会权力运行的真实具象,以诠释乡村社会不同阶层和组织的动态关系及其应对国家权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理性解读了乡村精英与乡村普通民众的合作共谋举措、动因及实效,阐明中国乡村社会独有的权力运行规则,揭示出如果抛开和破坏乡村文化网络国家权力下沉注定失败的铁一般的事实。
其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网络的各要素,对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组织的认同价值,对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深入描述。强调“权力文化网络”并非全封闭式,当规则不再适用时,竞争就会变为公开的冲突,从而创造出新的组织体系及文化认同,以适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博弈的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