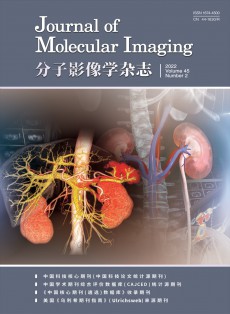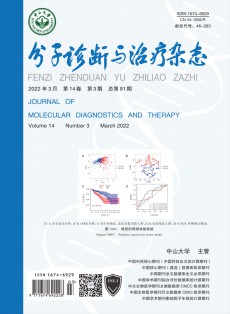分子遗传学综述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2:35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分子遗传学综述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又名麝鹿、香獐,属偶蹄目Artiodactyla、麝科Moschidae、麝属Moschus,是目前养殖规模较大、数量最多的麝科动物之一。雄麝香腺分泌的外激素――麝香在传统中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2]。由于国际香料市场和医疗行业对麝香需求量的大增,人类“杀麝取香”和对其栖息地的严重破坏,已使该物种野生种群数量急剧减少,现存麝类已面临濒危。目前,林麝已被列人CITES附录Ⅰ中,《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将麝列为濒危或易危动物[3]。我国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林麝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02年又将其提升为一级保护动物。麝的珍贵引起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的浓厚兴趣,在林麝的生态学[4]、行为学[5]、分类学[6]、生理学[7]以及麝香的药理学与临床应用[8]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新兴生物技术开始被不断地运用到林麝遗传育种工作中,为林麝的育种保护工作注入新的活力。其中,以新兴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标记技术最引人注目,分子遗传标记的出现使基于此类标记的选择育种技术有了实现的可行性,显现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当前,分子遗传标记在林麝遗传育种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遗传分类、人工繁育、泌香、疾病等方面。本文就分子遗传学在林麝研究中的应用现状做一综述,并对后期研究进行了展望,以期为提高林麝的生产性能提供参考。
1林麝分子遗传标记
分子遗传标记是基于DNA差异进行个体或群体遗传多样性分析的有力工具。常用于林麝遗传多样性分析的分子标记方法有AFLP,mtDNA,微卫星DNA等。
AFLP技术在种群结构和差异的调查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9]。陈轩[10]根据AFLP分子标记的特点,以四川养麝研究所白沙养麝场21只林麝样品和金凤山养麝场14只林麝样品为材料,对2个种群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发现四川养麝研究所白沙养麝场圈养的2个林麝种群均具有较高水平的遗传多样性,但金凤山种群具有相对较高的遗传多样性。赵莎莎[11]利用相同的原材料进一步检测了22对选择性引物组合,共获得了908个AFLP多态片段,结果证明了麝香高产组在多态位点比率(PPL)上极显著高于参照组和低产组,在遗传多样性水平上也有更高的整体竞争优势。
mtDNA是核外遗传物质,由于mtDNA的控制区富含A,T碱基,属于遗传高变区,进化速度比其他区域快,多态性丰富,常被应用到野生动物群体遗传多样性检测中。彭红元等[12]通过分析四川省3个本地种群中林麝mtDNA控制区域582bp片段,发现94个变异位点,在109个个体中检测出27个单倍型,表明3个群体间很少进行遗传交流,建议建立系谱以增加群体间基因的交流。2014年,冯慧等[13]调查了陕西省林麝1个圈养种群3个野生种群mtDNAD-Loop632bp片段的遗传多样性和种群结构,结果表明,陕西省林麝群体mtDNAD-loop区序列存在着较丰富的变异和遗传多样性,凤县野生群体和凤县养殖场群体的核苷酸多样性和单倍型多样较高,养殖场种群没有出现近亲繁殖及遗传多样性下降的情况。凤县野生群体和凤县养殖场群体两者遗传分化较小,存在着较高的基因流水平。
微卫星DNA广泛分布与真核生物基因组中,具有多态性高、共显性遗传、选择中性、易于操作等特点,是一种极具应用价值的分子遗传标记,由于微卫星重复序列在群体间和不同的个体间通常表现出很高的序列变异性,并且这种变异呈共显遗传,因而在微卫星重复序列广泛应用于物种遗传多样分析。2004年,邹方东[14]运用微卫星标记法构建了3个林麝基因组微卫星富集文库,每个文库含有上万个转化子。2005年,Zou等[15]又运用了改进的富集文库方式来分离微卫星位点,获得了野生林麝的多态位点,结果发现70%的基因组文库为(AC)_n文库,8个微卫星位点呈现高度多态性,可作为研究林麝的分子遗传标记。2006年,夏珊[16]对构建林麝的微卫星文库筛选了6个多态性好的座位,并对林麝的遗传多样性进行初步的分析,6个微卫星座位的多态信息含量(PIC)最低为0.6214,最高为0.7984,说明这6个林麝微卫星座位具有高度多态性,进一步证明了微卫星DNA是很好的分子遗传标记。
2林麝遗传分类研究
目前,对林麝的遗传分类有3种研究手段,分别为形态解剖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一种是根据外形、头骨和距骨的形态特点以及生态习性、分布等认为麝确是一个独立物种[17]。陈服官等[18]根据林麝生物标本,再一次肯定了这种分类方法。林麝作为麝科动物一个亚种除了在形态解剖学上得到了明确的肯定外,从细胞遗传学特征来看,也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细胞的染色体组型和染色体带型都代表着种的特性,它为不同物种在分类研究和确定其在进化过程中的位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2004年,邹方东等[19]以林麝外周血淋巴细胞为实验材料,首先建立了适合林麝淋巴细胞增殖的培养体系,并用培养出的细胞制备染色体,确定林麝核型是2N=58,且全都是端着丝粒染色体,还首次应用染色体G-带技术,对林麝染色体的G-带带型进行了研究,确定了林麝染色体是2N=58,且全都是端着丝粒染色体,这与其他鹿科动物存在较大差异。结果表明,从细胞遗传学角度将麝分为单独一科也是比较合理的。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麝作为独立的科在分子水平上相继得到了印证。Kuznetsova等[20]对鹿科家族成员和其他偶蹄动物的线粒体基因12S和16SrRNA(2445bp)的序列和核β-spectrin基因(828bp)的区域进行分析,发现鹿科和麝存在几个分子共源性特征。刘学东等[21]则利用测得梅花鹿、坡鹿、原麝和林麝的线粒体12SrRNA基因全序列,与GenBank中检索到的鼷鹿、长颈鹿和牛12SrRNA基因全序列进行对比,分别应用ME,ML,MP方法重建系统树,发现3种树拓扑结构一致,结果显示麝、鹿、牛、长颈鹿均各自为单系群,且麝作为一个单系进化。此外,采用PCR技术和序列测定方法从线粒体DNA上得到367bp的细胞色素b基因片段序列,分析其序列可得出在麝、獐、麂和鹿的系统进化中,麝约在600万年前与鹿科分歧,而鹿科的3个亚科是在350~500万年前开始分歧,表明麝可单独作为麝科[22]。张亮则采用克隆SRY基因的CDS区的方法,得到林麝和马麝的SRY基因,对其进行分析显示,支持麝作为独立一科的观点[23]。2009年,彭红元等[12]测定了林麝全线粒体序列,分别运用MP,Baryes方法与其他22种反刍亚目的动物相关基因序列进行系统进化分析,表明林麝与鹿科动物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并单独形成一支,在牛科和鹿科之前分化出来,为鹿科、牛科互为姐妹群。2012年,冯慧等[13]从秦岭林麝的毛发样品中提取得到线粒体DNACytb基因的部分序列,并对其进行序列分析,发现林麝、原麝、马麝、喜马拉雅麝、黑麝是5种独立的种,林麝与原麝的亲缘关系最近,进一步弥补了现有形态分类研究的不足,得到更有说服力的分析结果。截至目前,运用各种克隆方法得到的林麝DNA序列,对其分析后发现其遗传学分类与形态解剖学、细胞遗传学得到的结果是相同,对麝作为单独一个物种的结果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3林麝分子遗传学在人工繁育上的应用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林麝的人工繁育方面取得了不少优秀成果。但是,由于基础研究及资金等方面的问题,我国的圈养林麝规模一直徘徊在6000只左右[24],并且在林麝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种群退化、后代抗病力下降等问题也不断凸显,因此,加大对林麝的人工繁育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工作力度显得尤为重要。2004年,邹方东等[25]首次成功克隆了与林麝生殖相关的核β-A亚基成熟肽序列,为林麝的人工繁育和麝资源的保护利用提供了相关基础资料。也有人对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远东地区和萨哈林岛的麝进行遗传多样性分析,发现随着栖息地的分裂,麝的近亲繁殖遗传多样性在不断上升,进而出现种群隔离现象[26]。此外,岳碧松研究团队对四川省米亚罗、金凤、马尔康3个养殖场的林麝进行微卫星分析,表明都是有效的群体规模,其遗传结构具有重要的保护意义,并建议在林麝人工育种时应当充分考虑这种遗传结构[27],这为林麝的选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认识。2013年,岳碧松研究团队再次对四川米亚罗地区人工繁育林麝的多态性进行微卫星分析,发现由于引入新的血缘,林麝的杂合程度和遗传多样性在不断增加[28],为林麝的人工繁殖管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4分子遗传学与林麝泌香的关系
获取麝香是保护林麝遗传资源的本质因素,提高麝香的产量,对林麝泌香相关的研究已经从组织解剖水平深入到泌香分子机制的研究。陈轩[10]分析了林麝AFLP的多态性与产香量的关系,筛选出34个在高产组和低产组间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有显著(P参照组>低产组(P
白康[29]采用PCR-SSCP、测序分析等生物技术手段对雄性激素受体(AR)基因外显子1,4,8进行研究,结果显示,AR基因外显子1,4,8在所做样本中不存在多态性,说明雄性林麝AR基因外显子(1,4,8)在林麝中具有高度保守性。王勤等[30]克隆了调控林麝的繁殖和泌香的重要垂体激素FSH-β和LH-β基因,这为开展林麝泌香过程中基因表达的关联分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5分子遗传学与林麝疾病相关分析
麝类疾病是长期阻碍林麝人工养殖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分子遗传标记技术已经运用到林麝的疾病诊治过程中,这为寻找麝类疾病起因,制定相应抗体提供了一种新的借鉴方法。罗燕等[31]对林麝肺源致病性Escherichiacoli毒力基因进行了检测及鉴定,为进一步研究林麝肺源致病性E.coli的致病机制奠定了基础,同时为防治林麝E.coli性肺炎提供了依据。2013年,邹丹丹等[32]克隆和表达了林麝IL-1β基因,为其用于林麝疾病的防治奠定基础。李灵等[33]以四川养麝研究所的115只林麝个体为对象,通过对MHCⅡ类经典的DR和DQ座位的分离、遗传变异分析和化脓性疾病相关性的分析,揭示了林麝MHCⅡ基因多态性的维持机制及其与化脓性疾病的密切关系。周鑫等[34]为调查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肠杆菌O因子血清型以及相关耐药基因的流行状况,采用玻板凝集反应法进行O因子血清型鉴定,同时用PCR方法检测耐药基因,发现29株菌皆携带多种耐药基因,这对林麝临床科学合理用药有重要指导意义。
6问题及展望
6.1存在的问题
6.1.1林麝驯化程度低,对分子遗传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不便从1958年以来,全国陆陆续续开展了林麝的驯化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陕西镇坪、四川马尔康、重庆南川等养殖基地[35-37]。但由于科研经费有限及林麝养殖效益等问题,驯化研究并没有持续,这造成了林麝的驯化程度很低。这给林麝分子遗传研究过程中的样品采集、生产性能测定等工作带来极大不便,也给林麝带来强烈的应激反应。强烈的应激反应不仅给实验数据的可靠性与稳定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还对林麝自身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6.1.2林麝为一级保护动物且价格昂贵,限制了某些分子遗传相关工作的开展林麝为国家一级珍稀濒危药用动物,不允许因为科学研究而对林麝有任何伤害,因此无法及时地采集林麝内脏进行深入的分子生物学相关研究,只能采集林麝毛发、血液或因疾病死亡林麝的内脏,这给林麝分子遗传学相关研究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林麝资源量有限,存在非常严重的炒种情况,目前每对林麝的价格被炒到7万元,昂贵的种源成本大大降低了林麝产香的盈利能力,也大大提高了林麝研究的成本,这种现象不仅严重阻碍了林麝分子遗传相关研究,而且不利于整个林麝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
6.1.3相关科研人员稀缺,发展缓慢目前,相对与其他常见动物,从事林麝相关工作的人员极少,主要分布在四川养麝研究所、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陕西动物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几乎没有进行过林麝养殖行业的专题研讨及技术交流会。因此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在林麝上应用的时间相对靠后,这也大大地降低了林麝遗传学相关研究的进展。
6.2展望
6.2.1麝香资源奇缺是林麝分子遗传学研究开展的内在动力麝香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但由于麝香的产量极低,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这使得麝香的价格长期维持在黄金的3倍左右,因此,提高麝香产量就成为了林麝养殖行业的最重要目标。但由于林麝资源量极少且驯化程度低,传统遗传育种方法很难在林麝上得到顺利开展,因此通过分子遗传学方法筛选麝香高产分子标记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
6.2.2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将大大加快林麝分子遗传学研究进展林麝分子遗传学研究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DNA条形码鉴定物种技术[38]、DNA分子性别鉴定技术[39]已成功运用在林麝遗传资源保护与与繁育工作中。然而,相对于林麝如此丰富的遗传背景,仅靠分子生物学技术远远不够,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充分应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了解林麝的遗传结构,将传统研究方法和分子生物技术相结合,了解其遗传结构差异和特征,进行针对性保护和利用。另外,为了促进人工养麝事业的发展,提高林麝种群增长率和麝香产量,须继续加强对林麝的泌香性状、疾病抗性等表型的标记研究,为实现标记辅助选择(MAS),加速良种培育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中国药典.一部[S].2010:361.
[2]安谈红.麝香药用价值研究[J].吉林农业,2010(8):211.
[3]李天培.古老珍贵的物种――麝[J].中学生物学,2004(3):9.
[4]姜海瑞,薛文杰,徐宏发.林麝的生物学特性、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J].生物学教学,2012(5):7.
[5]卫宁.圈养雄性林麝期与非期主要行为的研究[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4.
[6]GrovesPC,冯祚建.安徽省麝的分类地位[J].兽类学报,1986,6(2):105.
[7]韩增胜,杨长锁,李青旺,等.林麝生殖生理和繁殖性能观察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31(6):103.
[8]陈怡君,钟玉绪,董武,等.麝香酮对斑马鱼胚胎的发育毒性[J].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2014,28(2):267.
[9]朱伟铨,王义权.AFLP分子标记技术及其在动物学研究中的应用[J].动物学杂志,2003,38(2):101.
[10]陈轩.林麝AFLP的多态性研究及产麝性能的标记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2007.
[11]赵莎莎.圈养林麝遗传多样性及泌香性能关联标记的分析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9.
[12]彭红元,张修月,岳碧松.林麝线粒体基因组扩增及其序列结构的初步分析[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1,32(2):63.
[13]冯慧,冯成利,刘晓农,等.林麝毛发DNA的提取及系统发育分析[J].西北农业学报,2012,23(8):14.
[14]邹方东,岳碧松,张义正.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微卫星的分离与多态性研究[C].南充:四川动物学会第八次会员暨第九次学术年会,2004.
[15]ZouFD,YueBS,XuL,etal.Isolationandcharacterizationofmicrosatellitelocifromforestmuskdeer(Moschusberezovskii)[J].ZoolSci,2005,22(5):593.
[16]夏珊.林麝(Moschusberezovskii)微卫星分子标记筛选及其应用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6.
[17]高耀亭.中国麝的分类[J].动物学报,1963(3):479.
[18]陈服官,闵芝兰,黄洪富,等.陕西省秦岭大巴山地区兽类分类和区系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1980(1):137.
[19]邹方东,岳碧松,张义正,等.林麝染色体制备方法及核型与G-带带型研究[J].兽类学报,2004,24(2):115.
[20]KuznetsovaMV,KholodovaMV,DanilkinAA.Molecularphylogenyofdeer(Cervidae:Artiodactyla)[J].Genetika,2005,41(7):910.
[21]刘学东,郑冬,马建章.从12SrRNA基因序列探讨麝类动物(Moschus)在新反刍下目中的系统学地位[J].东北林业大学学报,2005(3):59.
[22]李明,盛和林,玉手英利,等.麝、獐、麂和鹿间线粒体DNA的差异及其系统进化研究[J].兽类学报,1998,18(3):184.
[23]张亮,邹方东,陈三,等.林麝及马麝SRY基因片段克隆及其在系统进化分析中的应用[J].动物学研究,2004,25(4):334.
[24]李林海,黄祥云,刘刚,等.我国麝养殖种群现状及养殖业发展的分析[J].四川动物,2012,31(3):492.
[25]邹方东,张义正,杨楠,等.林麝、马麝及梅花鹿活化素基因β_A亚基成熟肽序列的克隆和分析[J].动物学杂志,2004,25(3):22.
[26]KholodovaMV,Prikhod′koVI.MoleculargeneticdiversityofmuskdeerMoschusmoschiferusL.,1758(Ruminantia,Artiodactyla)fromthenorthernsubspeciesgroup[J].Genetika,2006,42(7):955.
[27]GuanTL,ZengB,PengQK,etal.Microsatelliteanalysisofthegeneticstructureofcaptiveforestmuskdeerpopulationsanditsimplicationforconservation[J].BiochemSystEcol,2009,37(3):166.
[28]HuangJ,LiYZ,LiP,etal.GeneticqualityoftheMiyaluocaptiveforestmuskdeer(Moschusberezovskii)populationasassessedbymicrosatelliteloci[J].BiochemSystEcol,2013,47:25.
[29]白康.林麝雄激素受体多态性和性激素水平与其泌香量关系的研究[D].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30]王勤,张修月,王中凯,等.林麝促卵泡激素和促黄体激素基因的克隆及其序列分析[J].四川动物,2012,31(1):77.
[31]罗燕,王朋,赵洪明,等.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肠杆菌分离鉴定及毒力基因PCR检测[J].中国预防兽医学报,2012(8):615.
[32]邹丹丹,杨东,姜立春,等.林麝IL-1β基因的克隆、表达及生物学活性检测[J].畜牧兽医学报,2013,44(11):1734.
[33]李灵.林麝Ⅱ类MHC基因分离与化脓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3.
[34]周鑫,罗燕,程建国,等.林麝肺源致病性大肠杆菌O因子血清型鉴定及部分耐药基因的PCR检测[J].四川动物,2014(5):715.
[35]张义正,邓正已,李正昌.林麝的驯化及异地移养[J].中药材,1985(2):14.
[36]邓凤鸣.林麝的驯化与控制放牧[J].野生动物,1986(4):35.
篇2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270-03
医学遗传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介于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之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完成,医学遗传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基因组学与分子遗传学逐渐成为了21世纪的领头学科,在现代医学教育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1]。医学遗传学实验在知识与实践、实践与创新的链接上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当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变化,致使医学教育无论在教学手段还是在教学理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早地、更多地接近社会、接近临床,更注重人文精神,更多融入先进技术与研究成果[1~2]。而大部分医学遗传学实验则还主要关注在传统分子遗传学相关领域的基本实验操作,涉及遗传病相关资料的信息化获取与分析涉及很少,解决临床遗传学问题过程中存在理论与实践脱钩。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尚未达到提高医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求知探索精神、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的目的。为此,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优化了原有的医学遗传学课程教学体系,构建了新的实验教学模式。
一、利用网络课程资源,推进虚拟实验
依托于湖北民族学院网络中心,结合医学遗传学学科特点,进行数字化资源导学平台建设。网络平台的主体结构分为教师主导区和师生互动区两大部分。内容充实而全面,平台除了内容完善的多媒体课件,与教学内容或生活实际密切相关的研究成果,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还专门开辟了“虚拟实验室”栏目[3]。网络课程资源在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中主要解决二大问题:
1.是医学遗传学实验中所特有的一些对人体有重大危害的和涉及到比较先进实验技术的实验,出于安全和成本考虑,学生往往无法直接参与其中[4]。虚拟实验可突破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受时间、地点、方式的限制,实验的安全性高、成本低、效率高,弥补了实验场地设备不足、教学时空性的约束。虚拟实验教学不但可提供良好的人机交互,还允许学生在出错时,自行了解错误的根源及后果,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教与学的灵活交互[4]。利用网络课程资源来培养学生随时学习、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可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并将教师的教学行为由课堂上扩展到了课堂外。
2.是运用目前已经公开的人类基因组相关数据库,快速准确地查找、识别遗传病的相关遗传学背景信息,获取世界上最新进展的医学信息及科研成果[5]。近年来,遗传学领域的分子遗传学分支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致病易感基因位点和区域被筛选或定位识别。不单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致病基因被顺利定位识别克隆,一些复杂多基因遗传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阿兹海默氏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肿瘤等疾病,也筛选出了众多与疾病发生相关的遗传易感标记物及药物敏感或抵抗标记物,人类对于疾病的遗传学认知达到了空前高度[5]。如何识别查找获取人类遗传病相关的遗传信息已经成为临床医生和基础医学科研工作者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在基础医学的教学上与时俱进,让医学生更早地接触相关知识,训练相关技能。由此,我们网络资源课程中的“虚拟实验”内容中专设了常见人类遗传病致病基因的数据库链接,主要以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http://ncbi.nlm.nih.gov/)与在线人类孟德尔遗传(Online Mendelian Inheritance in Man,OMIM)数据库为主,并至少安排一次实验课的时间介绍如何利用数据库完成常见人类遗传病相关遗传学信息收集,包括遗传模式、发病率、家系连锁定位区域、在基因组上的定位信息及热点突变位置等。
二、结合临床实践,开展第二课堂教学
医学遗传学实验教学是对理论教学必要的补充和巩固,通过实验技能训练,提高实验的综合能力和实验素质,促使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对培养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影响更为积极[6]。从临床角度出发,研究疾病的遗传因素、病变过程及其预防、诊断和治疗的相互关系,为将来走上临床医生岗位的临床专业学生提供从事医学实践所必需的遗传学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
篇3
【中图分类号】R53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234(2015)12-1148-03
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是一种严重的共患寄生虫病,呈全球分布。在我国主要流行的是日本血吸虫病。2013年全国共报告血吸虫病感染184943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29796例[1],血吸虫病的流行位居水传播疾病之首,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健康。钉螺(Oncomelaniahupensis)是日本血吸虫的唯一中间宿主,主要分布在亚洲东部和东南部,中国内地仅有湖北钉螺一种,钉螺分布与血吸虫病的流行息息相关。目前防控该病最常用的方法是消灭钉螺,人工培养钉螺对研究钉螺的生物学特性和筛选灭螺药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钉螺的生物学特性和人工培养的方法进行综述。
1钉螺的生物学特性
1.1形态学
钉螺为水陆两栖,常栖息于田间、池藻等淡水水域。它主要由螺壳和软体两部分组成,软体部分的前部为头、颈、足和外套膜,后部是内脏;表面有纵肋者称“肋壳钉螺”,壳长约10mm,宽约4mm。壳面光滑者称为“光壳钉螺”,比肋壳钉螺稍小,长、宽分别为6mm和3mm,多见于山丘地区。钉螺形态学特点主要包括形态特征、解剖结构等方面。钉螺早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钉螺内外部的形态结构变化,如螺壳形状、螺肋的数目及厣核的旋数[2],并以此来认识与鉴别钉螺,如巴西钉螺被认为是光壳钉螺的一种,螺壳黑色,螺壳外唇无隆起线,壳光滑有黄色“假眉”,厣与齿舌与湖北钉螺相同[3]。钉螺的形态特征是研究钉螺的分类、遗传和进化的基础,分布于山区的光壳钉螺和分布于湖沼水网地区的肋壳钉螺生存条件不同。湖北钉螺具有遗传多样性,而且具有不同程度的遗传变异[4]。石朝辉等[5]通过对湖北庙河上下游钉螺调查发现,两个地区钉螺分别为光壳钉螺和肋壳钉螺,上下游螺群的遗传距离并无明显差异。
1.2分类学
钉螺俗称钉螺蛳,为动物界第二大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中的一类,有雌雄之分。早期对钉螺分类的研究主要是以钉螺形态学和解剖学为依据的,自1913年宫入庆之助和铃木稔在日本证实光壳钉螺为日本血吸虫的中间宿主以来,对钉螺分类的依据主要是根据形态和解剖结构,如螺壳、螺厣和螺肋数目及齿舌形态特征。美国Bartsh根据螺旋数、齿式将钉螺分为Oncomelania、Katayama和Schistomophora[6]。有学者发现螺壳颜色、螺厣、齿舌等差异不大,认为钉螺的分类以形态结构为依据并不严谨[7-8]。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对钉螺分类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George等[9]通过对中国大陆不同地区、不同种群钉螺的同工酶进行比较,再结合螺壳形态学的基础将湖北钉螺再分成3个亚种:滇川亚种(O.h.robertsoni)、福建亚种(O.h.tangi)和湖北亚种(O.h.hupensis)。牛安欧等[10]利用单重复序列锚定PCR技术(SSR-PCR)将中国大陆7省的湖北钉螺分为4类。周艺彪等[11]采用微卫星锚定PCR分子技术对19个种群钉螺的基因DNA进行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大陆湖北钉螺分为滇川亚种、广西亚种、福建亚种和指名亚种等4个亚种。
1.3遗传学
钉螺的生物特征、地理分布以及日本血吸虫和钉螺之间的相容性都与钉螺遗传学特性密切相关。表观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和景观遗传学的研究应用在生物灭螺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表观遗传学常用来作为钉螺分类依据,刘月英等[12-13]认为中国大陆钉螺属于一属一种,世界各地钉螺作为同一种属只有种下亚种和地理株之分,但种下具体如何分类尚未得到解决。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钉螺种群同工酶谱的分析、DNA基因序列的研究进一步得到发展。日本血吸虫与钉螺之间的相容性主要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同工酶等位基因[14],而且不同种群的钉螺对日本血吸虫的相容性不同[15]。周晓农等[16]研究了中国9省34个地区螺群的同工酶,结果表明钉螺种群间的变异程度较大,而同种群内的变异较小,肋壳钉螺的遗传变异分化程度小于光壳钉螺,且钉螺从喜马拉雅山脉扩散至世界各地,因环境变化,基因也发生了剧烈漂移。景观遗传学是在2003年由Manel[17]首次提出,其结合了景观生态学和种群遗传学的特点,意义在于研究物种微进化与景观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钉螺遗传变异分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18]。崔斌等[19]采用微卫星锚定技术对湖北松滋地区不同景观环境下钉螺遗传特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北钉螺种群间遗传变异并不明显,而钉螺个体间变异显著。景观遗传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将人类及其活动纳入了研究范畴,在理论和方法方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4生态学
钉螺繁殖、分布及扩散等生态学特征与血吸虫病的流行息息相关。钉螺生态学的研究对血吸虫病的传播和预防可以起到理论指导作用。钉螺的生长繁殖易受灭螺药物和环境改变的影响,其分布密度与植被盖度有关[20]。林丹丹等[21]对鄱阳湖的自然环境进行研究发现植被总盖度与钉螺分布成正比,总盖度越高钉螺分布越广。地形是影响钉螺分布重要的因素之一,杨慧等[22]对云南地形的考察,发现云南地形以山区为主,呈孤岛性分布,扩散不明显,建议灭螺范围应以阳性钉螺分布地区为主,并适当扩大范围。钉螺的扩散方式主要以主动扩散和被动扩散为主,水流、光照强度、钉螺吸附能力以及水中障碍物均可影响钉螺的扩散[23]。此外,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如水灾、水利工程建设及旅游开发等也可影响钉螺分布与扩散。
1.5生理生化
钉螺的生理生化对研究灭螺药物的作用机制以及灭螺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杜小华等[24]用不同浓度的水和乙醇提取物配置成不同浓度的羊踯躅溶液进行灭杀钉螺实验,结果显示浓度不同的提取物处理钉螺后的灭杀率不同,其中以70%乙醇提取物灭杀钉螺的效果最佳。周康等[25]通过实验发现瑞香狼毒同上述几种药物一样对钉螺的主要能量代谢物质糖原有较强的抑制作用,而且以浓度为70%乙醇提取物的效果最好。黄春兰等[26]用硫酸、蒽酮比色法鉴定湖北钉螺各月份的肝、头足部肌肉和整体软体组织的糖原含量,结果表明整体软体组织和肝的糖原含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吴明煜等[27]用不同浓度的蛇床子总香豆素处理液浸泡钉螺,在浸泡液处理的前96h内,钉螺体内糖原的含量随着浸泡时间的延长而降低,说明蛇床子总香豆素可以影响钉螺的糖原含量。胡彦龙等[28]研究发现田皂角甙当浓度超过0.80g/L时可以明显降低钉螺体内糖原含量,降低的幅度达12.49%~73.16%。刘金涛等[29]发现浓度大于0.85g/L的苦楝子可以降低钉螺内的糖原含量,降低幅度为10.78%~69.94%。过氧化物酶、三磷酸腺苷酶、琥珀酸脱氢酶、乳酸脱氢酶是钉螺进行有氧呼吸的关键酶,抑制这些酶的合成可以有效地杀灭钉螺。顾文彪等[30-31]用苦楝叶提取液浸泡钉螺发现三磷酸腺苷酶、琥珀酸脱氢酶和乳酸脱氢酶降低,而一氧化氮合成酶增高,一氧化氮合酶的升高可以使NO合成增加,破坏钉螺机体内的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使能量合成受抑制,达到杀灭钉螺的效果。王万贤等[32]分别采取樟树的新鲜叶、茎皮和根皮调配成1%、0.5%、0.1%、0.05%等4个不同浓度的溶液处理钉螺,结果显示钉螺体内的过氧化物酶的活性随着浸泡的时间延长活性降低,其中以根皮的效果最好,叶的效果较差,建议大量种植樟树作为生态林可达到较好的抑螺效果。
2钉螺的人工培养研究
2.1钉螺螺卵的孵化和幼螺的生长
对于钉螺螺卵的孵化和幼螺的生长,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温度、水和食物。钉螺螺卵的正常孵化需要在水中或是湿润的泥面上[33],饲料以奶粉及复合动物饲料为主,其中藻类喂养幼螺存活率较高,达90%以上,且生长良好[34-35]。田建国等[36]采用了收集螺卵恒温孵化法、直接恒温孵化法和自然状态孵化法三种方法对钉螺螺卵进行孵化,结果显示泥土也可以影响钉螺螺卵的孵化。
2.2成螺的人工培养
成螺培养因实验目的不同,室内培养方法也不尽相同,常用室内培养感染性钉螺是泥盘草纸饲养法[37]。成螺培养主要为感染性钉螺,其中毛蚴感染钉螺的比例至关重要,张聪等[38]采用泥钵内铺细土泥法,按毛蚴与钉螺数量比为5:1、10:1、20:1三种不同比例进行感染,结果显示毛蚴感染的比例为10:1时,钉螺阳性感染率最高。
篇4
分类号:B845
1 引言
抑郁通常用来指一系列范围较广的情绪问题,包括轻微的消极情绪到严重的情绪障碍。主要表现为悲伤、苦恼等消极情绪,伴随着退缩、注意力涣散等行为特征,重性抑郁患者还表现出失眠、厌食等躯体症状(cassano&Fava,2002;Compas,Ey,&Grant,1993)。抑郁是个体主要的情绪障碍和心理健康问题之一。在世界范围内,抑郁也是造成伤残和疾病负担的5种主要原因之一(Caspi et al.,2003)。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行为遗传学的兴起,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遗传因素在抑郁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早期双生子研究显示,儿童青少年抑郁的遗传力约为0.24-0.55(Happonen etal。,2002;Rice,Harold,&Thapar,2002a)。近年来,继Caspi等人(2003)里程碑式的研究之后,采用分子遗传学范式探究抑郁的遗传基础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成为抑郁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抑郁遗传基础的研究不断获得新的发现和突破,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就是遗传因素(Aslund et al.,2009;Eley et al.,2004;Jacobson&Rowe,1999;Jansson et alJ,2004)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Hammen,Brennan,Keenan-Miller,Hazel,&Najman,2010;sj8berg etal.,2006;Vaske,Beaver,Wright,Boisvert,&Makarios,2009)对抑郁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
考察抑郁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的表现及其原因,有助于推进抑郁产生机制的研究,对于解释抑郁的发生特点亦具有重要启示。鉴于此,本文对既有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进而从性激素、环境敏感性及中间表型3个方面分析性别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2 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
通过对该领域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定量行为遗传学研究主要比较抑郁遗传率的性别差异,较早期的分子行为遗传学研究考察基因与抑郁简单关联的性别差异,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开始探讨抑郁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GxE)的性别差异。鉴于此,本文按照其发展沿革将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基因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二是基因与环境的交互效应(详见表1)。
2.1 遗传直接效应的性别差异
早期研究大多采用数量遗传学中的双生子范式考察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双生子研究通过比较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在心理发展特征上的相似程度来了解遗传和环境对表型变异的相对贡献,以遗传率作为衡量遗传效应大小的指标,即在某一群体的表型变异中,遗传效应所占的比例(曹丛,王美萍,张文新,陈光辉,2012;Plomin,DeFries,McCleam,&McGuffin,2001)。采用这种范式,Jacobson和Rowe(1999)以自我报告的方式对美国青少年健康追踪研究中的2302名青少年(平均年龄16岁)双生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女性抑郁情绪的遗传率大于男性。之后,Jansson等人(2004)以1918名瑞典老年双生子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女性抑郁的遗传率高于男性,而且这种性别差异不受抑郁测评方式(二分法或连续记分法)的影响。此外,Scourfield等人(2003)以儿童青少年(5-17岁)为被试,以母亲报告的被试抑郁症状为指标,考察了抑郁遗传率的性别差异问题,其研究结果亦表明女孩的抑郁遗传率高于男孩。
近年来,随着分子遗传学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分子遗传学的方法对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进行了考察。目前,大多数抑郁研究考察了5一羟色胺系统基因、多巴胺系统基因与抑郁的关联,例如5-HTTLPR(serotonin.transporter-linked promoter region,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MAOA(monoamine oxidase A,单胺氧化酶A)基因、COMT(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儿茶酚胺氧位甲基转移酶)基因和DRD2 (D2dopamine receptor,多巴胺D2型受体)基因等。相关候选基因可以通过降解(如MAOA、COMT)和转运(如5-HTTLPR)功能调节突触间隙中5一羟色胺或多巴胺的水平,也可以改变脑内受体数量(如DRD2基因)调节信号传导,进而影响个体抑郁水平。
该领域的研究为抑郁遗传基因,特别是5-HTTLPR基因对抑郁影响的性别差异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并且诸多研究一致表明5-HTTLPR基因与女性抑郁存在密切关联。譬如,Eley(2004)等人以377名10-20岁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SS和SL基因型,研究者按照5-HTTLPR区域上重复序列的数量将基因型划分为由14个重复序列组成的短等位基因S和由16个重复序列组成的长等位基因L1的女性抑郁水平较低,但是5-HTTLPR基因与男性抑郁无关。Aslund(2009)等人以1482名17-18岁瑞典青少年为被试进行研究,结果亦发现5-HTTLPR基因多态性仅对女性的抑郁存在直接效应,携带ss基因型的女性其患抑郁的风险较低,但该基因多态性与男性抑郁无关。Uddin及其同事的一系列研究也表明5-HTTLPR基因仅对女性抑郁存在直接效应,具体表现为携带SL基因型的女性抑郁水平较低(Uddin et al.,2010;Uddin。De losSantos,Bakshis,Cheng,&Aiello,2011)。由此可见。5-HTTLPR基因与抑郁的关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研究结果在具体基因型上仍然存在分歧,这或许与对5-HTTLPR基因rs25531多态性位点功能的划分有关,需要未来研究进一步进行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有小部分研究发现某些遗传基因的直接效应只存在于男性群体中。如Nyman等人(2011)采用北芬兰出生序列(Northem FinlandBirth Cohort)追踪研究中的5225名成人为被试。探索多种候选基因与环境风险因素在抑郁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DRD2基因仅与男性抑郁症状显著相关(Nyman et al.,201 1)。此外,Baekken等人以北特伦德拉格健康研究fNord-TrondelagHealth Study)中的5531名成人为被试,研究COMT基因与焦虑抑郁的关系,结果表明在男性群体中,携带Met/Met基因型的个体患抑郁的可能性显著低于Val/Val基因型携带者,但在女性中没有发现该趋势(Baekken,Skorpen,Stordal。Zwart,&Hagen,2008)。
综上所述,双生子和分子遗传学研究均表明遗传因素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存在性别差异.而且分子遗传学研究资料进一步显示,不同遗传基因对男女个体抑郁的影响是不同的,5-HTTLPR可能是女性抑郁的风险基因,而对男性抑郁来说,COMT和DRD2基因的影响可能更大。
2.2 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性别差异
采用基因一环境设计考察抑郁的遗传基础是当前行为遗传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之一,诸多研究表明抑郁的GxE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Barr等人(2004)选择与人类直系同源的恒河猴为研究对象(恒河猴与人类在5-HTTLPR上具有相同的基因多态性),考察了5-HTTLPR基因与早期不利事件(early adversity)对压力刺激时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皮质醇分泌的影响,结果发现由同伴养育(即早期不利处境)的雌性恒河猴中,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个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增加,总体皮质醇水平下降(通常这一激素的反应模式被认为与压力导致的神经障碍有关),但在雄性中没有出现该反应模式。
除动物研究外,以人类为被试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性别差异模式。例如,Eley等(2004)和Aslund等人(2009)的研究一致表明5-HTTLPR基因与负性生活事件(失业、重病、丧亲等)或虐待对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别差异,携带S等位基因的女性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或虐待时,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Hammen等人(2010)以346名青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个体,在15岁时经历的慢性家庭压力(父母关系质量、亲子关系质量等)越多,其成年后的抑郁水平越高,但这一交互效应只存在于女性群体中。Vaske等人以2023名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DRD2基因TaqlA多态性与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交互效应,结果仅在非裔美国女性中发现了GxE效应(Vaske et al.,2009)。
然而,也有小部分研究获得了不同的研究结果。sjoberg等人(2006)以200名青少年(16.19岁)为被试,考察了5-HTTLPR与心理社会压力f创伤性家庭冲突、父母离异、居住地环境)对抑郁的影响,发现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GxE交互作用模式截然相反,在女性中,携带s等位基因的个体在经历了创伤性家庭冲突后其抑郁水平显著高于未经历家庭冲突的女性,然而在男性中,当携带L等位基因的个体处于风险环境(父母离异或居住条件不良等)中时,其患抑郁的风险较高。与此类似,Brummett等(2008)分别以288名和142名成人为被试进行了两项研究,结果均发现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在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亲属重病、社经地位)时,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而携带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在面临压力性生活事件时抑郁水平较高。最近,Priess-Grobe和Hyde(2013)以309名青少年为被试,考察了5-HTTLPR基因与负性生活事件(亲属死亡、父母离异等)对抑郁的影响以及MAOA基因与性别的调节作用(5-HTTLPR×负性生活事件×MAOA×性别),也发现在携带低活性MAOA基因型的个体中,5-HTTLPR基因与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别差异,携带S等位基因的女性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其抑郁水平越高,而在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的男性中,只有携带L等位基因的个体才表现出抑郁症状。以上3项研究似乎表明,面临压力时携带s等位基因的女孩容易患抑郁,而同样情况下携带L基因的男性患抑郁的风险较高。此外,Nyman等人(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COMT基因rs4680多态性与环境的交互效应仅在男性中显著,携带G等位基因的男性在经历了环境压力后抑郁水平较高(Nyman et al.,2011)。
通过分析上述研究可以发现,抑郁的GxE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并且在女性群体中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在压力环境下,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的抑郁水平较高。但是,在男性群体中所获得的结论仍存在分歧。
导致男性群体中既有研究结论存在分歧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单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范式,而没有考察多基因的交互效应。人类行为具有复杂的遗传基础,多数人类行为并不像单基因遗传疾病(如亨廷顿舞蹈病)那样具有清晰简洁的模式,而是会依赖于环境因素和多种基因的交互作用(McGuffin,Riley,&Plomin,2001)。事实上,已有研究证实了多种基因间存在交互效应,并且提供了与单基因研究不同的结果,如上述Priess-Groben和Hyde(20131的研究结果显示,同时携带低活性MAOA和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在经历了负性生活事件后抑郁水平较高,这与Aslund等人(2009)的单基因研究结果不一致。(2)研究者所选择的环境指标不同。多数研究只考察了压力性生活事件等直接对个体产生影响的近端风险因素(proximalrisk factors,指直接对个体产生影响的社会和身体经验,如负性生活事件、虐待等),如Eley等(2004)、Aslund等(2009)和Vaske(2009)等人以不利生活事件、虐待等为环境指标,均发现仅在女性群体中存在GxE效应,而少数不一致的研究则选择了远端风险因素(distal risk factors,指间接对个体产生影响的历史、文化、人口及地理特征等因素,如地区贫困水平等),如Uddin等(2010)选择了地区贫困水平等远端环境指标,发现仅在男性群体中存在G×E效应,而Moffitt等人指出远端环境的效应受到近端环境的调节(Moffitt,Caspi,&Rutter,2006),因而近端和远端风险因素的选择可能对研究结果具有重要影响。(3)研究对象的年龄不同。Moffitt等人(2006)指出在研究基因与不利环境对抑郁的作用时,年龄可能是导致大部分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重要因素。如Eley等(2004)、Aslund(2009)等人选择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仅在女性群体中存在GxE效应,但是Brummett等(2008)以中老年人为被试的研究却发现5-HTTLPR基因与压力的交互作用在男性和女性群体中呈相反的作用模式。
3 抑郁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的原因
虽然尚未有研究对抑郁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的原因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但综述既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可能与性激素、个体对不同类型环境的敏感性以及中间表型有关。
3.1 性激素
性激素可能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影响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首先,性激素直接调节基因与抑郁相关生理反应间的关系。Josephs等(2012、以成人为被试通过3种压力反应实验(研究1:通过社会排斥诱发地位威胁,研究2:认知失败,研究3:身体胜任力)考察了5-HTTLPR基因与素对皮质醇水平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均发现在素水平较高时,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个体的皮质醇水平较高,而携带LL基因型的个体皮质醇水平较低,但当素水平较低时,两种基因型的个体皮质醇水平相差不大甚至携带LL基因型的个体皮质醇水平更高,这一结果表明5-HTTLPR基因与皮质醇反应的关系受到素的调节,而已有研究显示重性抑郁患者的皮质醇水平较高(Maes,Jacobs,Suy,Minner,&Raus,1989),这提示我们性激素可能通过调节遗传基因与抑郁间的关联,进而影响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性激素对基因~抑郁关联的影响。
其次,性激素影响抑郁相关基因的表达。研究发现雌激素可以改变对5-羟色胺(serotonin,5-HT)神经递质有重要作用的基因的表达,这种改变会增加5-HT的合成,减少5-HT的自我阻断(Pecins-Thompson&Bethea,1998;Pecins-Thompson,Brown,&Bethea,1998)。Gundlah等人通过对切除卵巢的恒河猴进行雌性激素治疗(注射雌激素)发现。雌激素的增加会降低中缝核及下丘脑中MAOA基因的表达(Gundlah,Lu,&Bethea,2002),而有研究指出5-HT水平较低的人群更容易产生抑郁(Priess-Groben&Hyde,2013),因而,受雌激素调节的MAOA基因转录减少,会增加突触间隙中5-HT水平,进而影响个体抑郁的发生与发展。
第三,雌激素直接影响5.羟色胺系统的功能。研究者从不同的方面考察了雌激素对5-羟色胺系统功能的影响。首先,雌激素可以影响中脑和下丘脑5-羟色胺受体水平(Beyer et al.,2003;Zhou,Cunningham,&Thomas,2002)。与此一致,Chakravorty和Halbreich(1997)的研究也发现雌激素可以调节5-HT1受体和5-HT2受体,减少单胺氧化酶(monoamine oxidase,MAO)活性。其次,雌激素可以增加5-HT的合成(Dickinson&Curzon,1986)。简言之,雌激素和其他性激素一样作用于细胞内的雌激素受体(Rubinow&Schmidt,2003),当荷尔蒙与受体相结合时,调节编码基因的转录,制造大量蛋白,而这些蛋白对合成五羟色胺来说恰恰是必不可少的。最后,雌激素还能增强5-HT的活性。如Halbreich等人(1995)发现处于绝经期的女性5-HT的活性显著降低,而且更易产生情绪障碍,研究同时指出使用雌激素替代疗法(注射雌激素)可以显著减少抑郁的易感性并且增加了5-HT抗抑郁药物的功效。换言之,雌激素在5-HT功能上的累积效应就如同这一系统的激动剂(agonist)(Halbreich,1997)。
值得指出的是,抑郁的性别差异通常出现在青春期,表现为青春期女孩的抑郁水平高于男孩(Uddin et al.,2011;Piccinelli&Wilknson,2000),但是这一时期女孩的雌激素是升高的,这与上述研究中提到的“低雌激素水平与抑郁有关”相矛盾。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女性在青春期时雌激素迅速升高,导致雌激素内稳态(estrogenhomeostasis)紊乱,而这一紊乱会扰乱五羟色胺的合成过程并引绪障碍(Halbreich&Kahn,2001)。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性激素与抑郁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如一项男性研究指出素水平与抑郁症的关系呈u型曲线,即素水平过高或者过低,个体的抑郁水平较高(Booth,Johnson,&Granger,1999)。
3.2 环境敏感性的性别差异
众所周知,环境因素(如压力性事件)是抑郁的重要预测源。如前所述,遗传和环境对抑郁的交互作用存在性别差异,这既与特定遗传基因对两性存在不同影响有关,也可能与男女对环境的敏感性不同有关。一项对346名青年人的研究发现,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其经历的慢性家庭压力(如父母争吵等)越多,患抑郁的可能性越大,但这一GXE效应在男性中并不存在。换言之,相比男性,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对家庭人际关系(如父母婚姻质量和亲子关系质量)更为敏感(Hammen et al.,2010)。然而,Uddin等人(2010)以1084名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则发现,当地区贫困水平(该地区接受公共救助家庭的比例)较高时,携带5-HTTLPR SL基因型的男性患抑郁的风险较低,而这一GXE交互作用在女性群体中并不显著,这与Hammen等人(2010)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通过分析上述研究方法可以发现,两项研究选择的环境指标存在差异,前者选择的是家庭环境变量,而后者选择的为社会环境变量。这些研究结果提示,男女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敏感性可能存在差异。Sjoberg等人(2006)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该假设的合理性。他们采用不同类型的环境指标(创伤性家庭冲突、父母离异、居住地环境)发现,携带5-HTTLPR L等位基因的男性更容易受到公共居住环境和父母离异的消极影响,而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女性则更容易受到伤害性家庭冲突(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关系等)的影响。
结合上述研究可推知,在宏观社会环境水平(如社区环境)上,男性的敏感性要大于女性,但在人际关系及家庭水平的环境变量上,女性的敏感性要高于男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离婚这一环境指标上,男性的敏感性更高。虽然既有研究表明男女对不同类型的环境敏感程度存在差异,但大多相关研究测量的是女性较为敏感的环境变量。此外,多数研究只考察了消极环境变量的作用,忽略了积极环境对个体抑郁性别差异的贡献:而已有研究发现在社会支持水平较高的环境下.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的个体患抑郁的风险较低(Kaufman et al.,2004)。因而,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不同类型和不同性质的环境指标对抑郁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的作用。
3.3 中间表型(intermediate phenotype)
中间表型(intermediate phenotype)是内在的、可遗传的、稳定的个人特质,如神经生理结构、生物化学成分、认知等,与心理障碍、精神疾病等密切相关(Meyer-Lindenberg&Weinberger,2006)。正如心理学家Uher和McGuffin(2008)所言,中间表型比外在的心理症状更具有遗传性,对中间表型的研究将会扩展和深化已知的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近期,已有研究表明基因对抑郁的效应可能受到注意偏好、消极推理风格等中间表型的调节。如Gibb Uhrlass,Grassia,McGeary和Benas(2009)的一项研究发现,5-HTTLPR基因、儿童推理风格和母亲情绪性批评三者存在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具有消极推理风格的儿童中,携带5-HTTLPR SS基因型的个体经历的母亲情绪性批评越多,其抑郁水平越高。Gibb,Benas和Grassia(2009)的另一项研究还检验了5-HTTLPR基因、母亲抑郁病史与儿童注意偏好之间的联系,结果也发现母亲抑郁水平越高,携带5-HTTLPR S等位基因且同时表现出对悲伤面孔注意回避的儿童患抑郁的可能性更大。伴随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等神经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研究者开始考察脑功能、脑结构等中间表型与抑郁遗传基础的关联。由于杏仁核活性与个体抑郁有关(Lonsdorf et al.,2009),因此通过考察5-HTTLPR基因与杏仁核活性关联的研究可以推知中间表型对遗传效应的调节作用。Lemogne等人(2011)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认知评估任务中,5-HTTLPR基因与生活压力对杏仁核活性的作用模式相反,具体表现为,在自我指向的认知评估任务中,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S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杏仁核活性降低,而LL基因型携带者的杏仁核活性增强;但在情绪标签的认知评估任务中,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s等位基因携带者的杏仁核活性增强,LL基因型携带者的杏仁核活性则降低。此外,情绪系统中其他脑结构与基因的关联也备受关注(Cole et al.,2011;Andms et al.,2012;Drabant et al.,2012),如Drabant等人(2012)考察了大脑边缘系统与5。HTTLPR基因的关联,结果发现,与携带5-HTTLPR L等位基因的女性相比,携带sS基因型的女性在面临压力情境时表现出杏仁核、海马、前脑岛、丘脑、丘脑后结节、尾状核、楔前叶、前扣带回和内侧前额叶等脑区活性的显著增强,而这些脑区活性的增强与焦虑抑郁密切相关。
上述研究表明遗传效应可能受到中间表型的调节,并且既有研究发现中间表型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如在青少年阶段具有消极归因风格的女性要显著多于男性(Hankin&Abramson,2002;Nolen-Hoeksema&Girgus,1994),并且在女性群体中消极归因风格与抑郁的联系比在男性中更为密切(Gladstone,Kaslow,Seeley,&Lewinsohn,1997)。除了消极归因风格外,反思(rumination)倾向也是抑郁的特征之一(Nolen-Hoeksema,2000),一项关于成人的追踪研究发现反思倾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的反思倾向显著高于男性(Nolen-Hoeksema,Larson,&Grayson,1999),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中间表型的性别差异。
4 小结与展望
抑郁具有复杂的遗传基础,不论是遗传直接效应还是遗传一环境的交互作用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尽管一些具体结论还存在分歧。本文通过综述已有文献,从性激素、环境敏感性及个体中间表型三方面讨论了抑郁遗传基础性别差异的可能原因。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未来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如下问题:
(1)采用多基因一环境设计考察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
由前可知,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单基因一环境交互作用的研究范式,即使有的研究(Eley et al.,2004;Nyman et al.,201 1)同时考察了多种基因,也仅仅是分析单个基因与环境对抑郁的影响,并没有考察多种基因的交互效应。然而,神经递质之间的功能关系十分复杂,一种递质功能紊乱可能引起另外一种或几种递质的功能失衡,从而导致一定的病理生理现象(王美萍,张文新,2010)。不同基因间存在交互效应,如Kaufman等人(2006)的一项研究就发现BDNF(brain derived neurophicfactor,脑源性神机更营养因子)和5-HTTLPR基因对个体抑郁存在交互效应。如前所述多基因研究与单基因研究的结果也往往不同,因此未来研究应尽可能采用多基因一环境设计更深入地考察抑郁的遗传基础及其性别差异。
(2)考察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环境与遗传基因交互影响抑郁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抑郁遗传基础的性别差异可能是个体对不同类型的环境的敏感性存在差异造成的,多数研究并没有给男性敏感的环境变量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未来研究应同时采用男性和女性的敏感环境因素,考察其在抑郁遗传基础中的效应。此外,现有抑郁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多是“素质一压力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由于该模型认为,当个体处于应激或高压状态时,具有某种不良遗传素质的个体更容易发生心理与行为问题,因而以该模型为理论基础的研究多以压力性生活事件等消极环境为指标来考察抑郁的GxE效应(Aslund et al.,2009;Caspi et al.,2003;Beach et al.,2010)。然而,新近兴起的理论模型——“不同易感性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model)明确提出并证明,某些基因型的个体也更容易受到积极成长环境的影响而表现良好或优秀(Belsky&Pluess,2009;Ellis,Boyce,Belsky,Bakermans-Kranenburg,&van Ijzendoom,2011)。因此,现有以“素质一压力模型”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未能揭示GxE交互作用的多种可能方式,携带不同基因型个体对积极环境的敏感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重点考察的内容。
篇5
运动医学是建立在研究运动的基础上的,是医学与体育运动相结合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具体研究与体育运动有关的医学问题,运用医学的知识和技术对体育运动参加者进行医学监督和指导,从而达到防治伤病、保障运动者的健康、增强体质、运动损伤后快速康复和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
运动医学在欧美的发展较早,尤其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东、西德的发展较为引世人瞩目,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学及体育院校都设有运动医学研究所。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后来者居上,运动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迅猛发展。即使在某些欠发达国家,如拉脱维亚等的部分高校不仅有运动医学系,甚至还成立了专门的运动医学院,也有部分高校将运动医学作为一门课程加以学习[1-3]。
运动医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运动员科学选材。科学选材是指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客观地测定人体的某些数据和指标,以此预测其未来的竞技能力。科学选材关系到遗传学、形态学、生理学、统计学和训练学等多种学科的领域。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训练方法的更加客观和科学化,要使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科学的选材就是成功的一半。②运动营养学。研究合理利用食物以满足人体需要,以提高运动能力。③运动损伤。研究运动损伤的发生规律、机理、防治措施和伤后的康复训练等问题。④医疗体育。研究运用各种体育手段防治伤病,特别是常见病的体育疗法。
本文旨在对运动医学在运动员的选拔、提高运动能力以及运动创伤的治疗上的研究,综述运动医学的研究领域的现状与进展。
一、 运动医学在运动员的选材上的研究
所谓运动员科学选材,是根据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用科学的、先进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客观指标的测试,全面综合评价和预测,把先天条件优越,适合从事某项运动的人从小选,进行系统培养,并且不断地监测其发展过程。
运动员科学选材作为运动医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制约运动员成材的因素很多,因而选材研究的内容必然涉及到方方面面众多领域。目前,运动员选材已从单一方面研究深入到全面展示不同项目运动员身体形态、生理机能、生物力学及心理学方面的综合特征,尤其深入到运动员不同运动能力的遗传特征和家族聚集性等方面的研究,并已着手探讨体质与运动能力相关基因的分布特征、基因表达、变异状况等问题[4,5]。
近年,随着分子遗传学的进展及其对运动医学领域的渗透,国内外学者尝试着探讨与运动能力相关的基因。目前研究发现,有氧能力有关基因有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6]、肌肉组织特异性磷酸肌酸激酶CKMM、肾上腺素能α受体ADRA2A及线粒体基因mtDNA的D-loop和MTND5等[7];与肌肉力量有关的基因主要涉及GDF8、CNTF等[8,9];涉及到耐力素质的基因有ACE[10]、CKMM、ADRA2A、Na-K-ATPaseα2基因等。人们试图探明这些表型的基因标记或定位,以解决优秀运动员的早期选材问题,并从分子水平揭示人类运动能力的遗传生物学机制。
伴随着人类基因组学的飞速发展如果我国运动科学工作者能利用现代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及生物芯片等技术结合,了解其相关基因的结构和功能,对运动能力的预测、评定以及科学选材系统的建立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望从根本上解决竞技体育早期选材、早期培养和科学监控的难题。
二、 运动医学在提高运动能力上的研究
训练外的运动强力手段一直为运动医学所关注,其中膳食热量的调节和机能增进酸的补充广泛地被应用于运动训练实践。其中营养物质对提高运动能力一直被作为研究热点之一。
人们长期的观点认为,高碳水化合物(carbohybrate,CHO)膳食方案(碳水化合物提高能量占总能量的60%~70%)是最有利于运动能力的提高,其理论基础在于高CHO的膳食可增进人体肌组织的糖元贮备,从而提高运动员的高强度运动状态下的抗疲劳能力。但也有人分析,当运动员采用高CHO膳食时,势必要减少蛋白质、脂肪的摄入比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运动能力,如低脂肪的摄取可影响脂溶性维生素的摄取水平。因此提出高脂膳食。高脂膳食可提高机体血清脂肪酸水平,从而提高脂肪氧化代谢率。有研究发现无论是口服还是静脉注射脂肪,均可提高血浆游离脂肪酸的水平,在运动中可使糖元节省化[11]。就运动膳食是高脂还是高CHO性,还需考虑运动的性质,考虑高血脂对人体心血管系统的负面影响。
肉碱被长期认为与长链脂肪酸向细胞内线粒体转运的一些酶的活性及水平有关。理论认为,增加肌肉组织的肉碱水平,可提高肌肉组织氧化脂肪酸节省肌糖元,而另一可能的作用机制是肉碱转化乙酰辅酶A为乙酰左旋肉碱和辅酶A,从而提高辅酶A的水平。另有些报道说肌酸和支链氨基酸可提高运动能力,但机制都不甚很明确,也有些研究者对此存在些质疑,需要针对不同的运动性质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12]。
现代医学还证明了针灸能提高运动能力[13]。激烈运动之后,由于能量物质的消耗,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堆积,经络气血阻滞不通,致使运动能力下降,通过刺激经穴的方法,疏通经络系统,调节脏腑之间的功能,使内环境达到平衡,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促进能量物质的恢复和补充,促进疲劳的消除,提高运动能力。
三、 运动医学在运动疲劳和运动创伤方面的研究
运动性疲劳是由于运动性刺激所引起的组织、器官甚至整个机体工作能力暂时下降的现象。运动性疲劳造成机体的代谢失衡和医学问题,具有如下几点特征:中枢神经系统的疲劳、免疫功能下降、神经内分泌功能抑制、造血系统功能抑制、机体抗过氧化能力下降等。如何预防、缓解和消除运动性疲劳,增进机体的抗氧化能力,防止运动性损伤,提高运动竞技水平是当今运动医学中的研究热点。
通过研究发现,抗氧化剂的补充可以预防和缓解运动性自由基损伤,增进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机体在剧烈运动时,由于自由基产生增加,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从而导致疲劳的产生。田京伟等的体外实验研究表明,白藜芦醇苷体外可清除O2+及•OH;抑制H2O2诱导的大鼠红细胞氧化性溶血;抑制•OH引起的小鼠肝微粒体过氧化脂质(LPO)和大鼠红细胞膜丙二醛(MDA)含量的升高,具有很好的清除自由基及抗脂质过氧化的作用[14]。
高强度的剧烈运动还是导致各脏器官发生缺血再灌注损伤的重要因素。对由于运动或其他行为而导致的软组织如骨膜、软骨膜等的严重损伤,而进行软组织移植时,干细胞起到重要的作用[15,16]。利用成体干细胞技术治疗心肌损伤,主要集中在骨髓的神经千细胞和骨骼肌与血液来源的干细胞。许多对实验动物心肌梗死模型的研究发现利用干细胞技术可以使心脏功能改善33%,将人骨髓来源的造血干细胞注射到大鼠的心脏受损部位,可以促使受损伤部位附近的血管产生新的分支,使心脏功能提升26%。
中国传统的针灸在治疗运动损伤疾病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14]。而某些中药也表现出较好的抗疲劳效用。
四、讨论
近年,随着基因重组与克隆等分子生物学理论与技术的发展,运动医学研究又从细胞、亚细胞研究扩展到分子与基因水平的研究,使运动医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于运动员科学选材、提高运动能力和运动疲劳和运动创伤有了新的认识,为运动医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P.Morrison, D.J, Pearsalll, R.A, Turcottel, K.Lockwood, D.L. Montgomery.Skate blade hollow and oxygen consumption during forward skating[J].Sports Engineering.2005(8):91-97.
[2] Lijian Liang, Yong Jiang and Ruonan Fan. Recognition of Biological Signal Mixed Based on Wavelet Analysis[A].Proceedings of UK―China Sports Engineering Workshop[C].2006:1-8.
[3] Asok Kumar Ghosh, Tengku Adnan Tengku Abdullah, PalKishan.Effect of Hot Environment on Repetitive Sprint Performance and Maximal Accumulated.Deficit of Cyclis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08.2(2):94-100.
[4] 马力宏.用双生法探讨遗传因素对通气敏感度及女子最大耗氧量的影响程度[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88(1):8-17.
[5] 常芸.面向21世纪的运动医学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02(38):3-8.
[6] 赵云,马力宏.核DNA多态性与人类运动能力相关联的分子遗传学研究[D].天津体育学院.2000.
[7] 陈青,马力宏,陈家琦.人体有氧运动能力及其分子遗传学特征的研究[D].天津体育学院.1999.
[8] 邓文骞,王璐,左天香等.耐力素质与力量素质相关基因的研究进展[J].四川体育科学.2007.
[9] Taylor RR,Mamotte CD,Fallon K.Elite athletes and gene for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gene[J] .Applied physiology,1999,87(3).
[10] 周文婷,李丽文,刘向雨.ACE基因与运动医学[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07,25(2).
[11] Griffith J, Humphrey S, Clark M,et al. Immediate Metabolic Availability of Dietary Fat in Combination with Carbohydrate[J].Am.J.Clin.Nutr.1994(59):53-59.
[12] Clarkon P M. Nutritional Ergogenic Aid: Carnitine[J]. Int.J. Sport. Nutr. 1992(2):185-190.
[13] 江岩,龚鹏.针灸在运动医学领域内的应用[J].中国名族民间医药.2010.19(5):4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