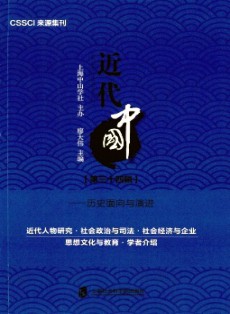近代文化交流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5 11:53:14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近代文化交流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Abstract: Transportation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real economy, but also the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a clear station of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in "Twelfth five-year" planning is presented. In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ition of transportation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modern industry provide guarantee and serv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Key words: transportation; real econom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D922.2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落实“十二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总体要求,要从以下六个方面组织推进。
1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适度超前,继续保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规模和速度,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建成并发挥效益,完善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
公路方面:以国家高速公路网建设为龙头,加强省际连接线(“断头路”)建设。修订国家公路网规划,强化国省道改造,力争“十二五”末路网整体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
水运方面:有序推进沿海港口建设,完善煤油矿箱等主要货种港口布局,加强资源整合,推进以临港工业为依托的沿海港口新港区开发建设。
民航方面:优化机场布局,增强机场保障能力。
邮政方面:加强邮政基础网络建设和增强快递发展能力,基本完成空白乡镇邮政所补建。
2加快推进结构调整。2010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提出“一条主线、五个努力”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的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十二五”要把结构调整作为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进一步加大力度,加快推进,务求实效。
(1)深化综合运输体系建设。
(2)深化现代物流发展。
(3)深化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建设。
(4)是深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行业建设。
(5)深化安全监管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
3着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信息化建设。深入实施“科技强交”战略,统筹推进创新能力建设、重大科技研发、成果推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围绕交通运输建设、管理的共性和核心技术,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注重消化吸收前沿技术,加强基础性、引领性重点项目研发,解决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
4不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交通运输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重要领域和民生工程。要加快构建衔接顺畅、方便快捷、经济可靠的运输服务体系,保障重点物资和城乡居民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运输畅通。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发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在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中的骨干作用,建设“公交都市”示范工程,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加强和规范出租车市场管理。
农村公路是农村重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要坚持扩大成果、完善设施、提升能力、统筹城乡的原则,着力改善中西部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农村交通运输设施条件,夯实新农村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推进交通运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组织实施以西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为重点的全国农村公路通达、通畅建设工程,进一步改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增强整体服务能力。提高农村公路抗灾能力和安全保障水平,加大农村公路桥梁新改建、渡改桥、安保工程等专项工程的实施力度,强化质量管理。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着力推进长期稳定的农村公路养护公共财政投资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现管养规范化、常态化。统筹城乡客运资源配置,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稳步提高农村客运班车通达率,鼓励城市公交向城市周边延伸覆盖。
5深入推进交通运输改革开放。按照中央大部制改革的部署要求,继续积极落实好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职责,加快职能转变,推进综合运输法制体系建设,逐步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交通运输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消除制约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
6持续推进行业文明和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推进和深化行业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开展好“学树建创”活动。
二、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推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
交通运输既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构成,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在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中,要深化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加快推进交通运输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为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服务保障。
1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是实体经济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现代物流是融合运输业、仓储业、货代业和信息业等的新兴复合型服务产业。交通运输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关键环节和主要载体,在现代物流链条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交通运输与现代物流融合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篇2
一、中国留学生概况
于中国而言,留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官派留学生。1872年至1875年间,由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倡议,在和李鸿章的支持下,清政府先后派出了四批总计12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
时至今日,中国留学生群体不断的发展壮大。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截止2013年,中国留学生总人数达到了305.86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人数除了在2004年有小幅度下滑外,一直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出国留学人数不断增长。2013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为41.39万,较2012年增加约14300人。
二、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产生的影响
文化交流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总揽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概况,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外交活动和战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形式。留学生究其本质属于一种文化交流的传统形式,作为文化交流传播的媒介,他们对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特殊的贡献。留学生远赴他国求学,作为某个留学生个体来说,他停留在他国的时间有限,造成影响的范围较小。但放大到整个留学生群体来看,他们在文化交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留学生所赴的区域范围很广,可谓遍布世界各地。“如此数量庞大的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置身于与自身成长环境不同的异国他乡,学习生活中频繁地与同学及教师的交流使得跨文化传播活动不可回避。”一代又一代留学生在海外生活求学,加之他们在此过程中自身对当地文化的不断适应,促使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深化,大大地延长了其影响的时间跨度及深度,且能够在此基础上有效地推动双方文化的融合与创新。
三、中国留学生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处于当下文化多元的社会,新文化不断衍生并冲击着传统文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成果加以巩固。作为一个中国人、更作为一个留学生,他们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他们在无形之中展现着母国的文化内涵,并将其向世界传播。留学生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巩固作用。
(二)有利于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遭到大肆渲染。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是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相互了解和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需求。留学生在国外生活学习,他们需要学会融入所处国家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身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践行是对此价值观最好的无声传递。文明、和谐、友善……外国友人在与中国留学生的接触中会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秀品质,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激进的民族,而是一个有责任,追求和平的民族。
(三)有利于我国吸收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引进有利于我国文化发展的人才、技术、经验。“近代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不仅刻苦求学,努力促进中外人民的友谊,同时还充当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留学生群体在传递我国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也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优秀学说引入国内,这大大促进了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
(四)加强公共外交
我国的公共外交主要以“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标,以“尊重、理解、共融”为理念,力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通过文化交流、艺术交流、公益慈善、民间对话等公共外交方式,加深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互动共融,增强本国的文化吸引力和政治影响力,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一个爱好和平、推动繁荣的中国。在公共外交活动中,留学生群体是一股不可取代的力量。他们年轻充满活力。在他们留学的国度,常有国人组织联谊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吸引他国民众参与进来。无形中逐步增强了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留学生群体深刻影响着国家形象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留学关乎一国文化的大局,中国留学生群体既代表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同时在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方面亦大有可为。
在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留学生群体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忽略的、强有力的助推力量。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此之下蕴藏的巨大力量。周棉在《留学生与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一文中概括说:“虽然这期间也有许多迷茫和教训值得加以研讨和总结,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告诉人们,他们在近代以来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具有特殊的贡献和特殊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文化交流与繁荣之路艰苦而漫长,但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A].公共外交季刊2012夏季号(总第10期)[C].2012.
[2] 兴越.基于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传播研究[D].复旦大学,2012.
篇3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篇4
一、“王韬研究”分期概述
在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时代,王韬成为“口岸知识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经历从“文人”到“译者”的蜕变。七十年的人生几经跌宕:译书、办报、游历、教学,柯文笔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与信仰的冲突中探索着。毋庸置疑,他是学者、政论家、文学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国的滚滚“西潮”,一个头衔或许更配得上他的贡献——中西文化传播中的先行者。
党月异②《王韬研究世纪回顾》把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王韬研究大致分为始发期、持续期、发展期、深入期四个阶段。最近的一个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这个阶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来“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韬生平和笼统整理介绍王韬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细致地考察了王韬的各种思想和活动。九十年代以后,相继问世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两部《王韬评传》(忻平④1990、张海林⑤1993)、《王韬年谱》(张志春⑥1994)、《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动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给他观念上带来的变化。目前,这种对主人公跨文化传播中表现的关注已逐渐开辟出研究王韬新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党月异在《王韬研究世纪回顾》中把王韬的事业划分为“报刊事业”、“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译事业”三个方面。总体看似没有问题,但细究起来却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传播的角度,三者之间有重叠部分,翻译书籍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环日报》的创立尤其是政论文体的大量采用,其实同样是在给民众灌输西方制度思想,增进民众对西学世界的了解。
二、王韬与中西书籍互译
王韬不仅协助麦都思将《圣经》等宗教作品翻译成中文,也在英华书院同理雅各合作将儒家经典译成英文。此外,王韬还与传教士合译过不少科技类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等。尽管著述颇丰,王韬的工作场所却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两地。
1、上海墨海书馆
选择步父亲后尘前往墨海书馆的王韬,最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王宏志⑦ 《“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力主此类观点并结合证据详尽剖析。关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译工作,有学者将其大致分为两期:前期以《圣经》、中文赞美诗等宗教作品为主,后期以科技、贸易类书籍为主。柯文的专著《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韬参与《圣经》翻译的相关细节,包括成员构成、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等。就王韬对两期工作的态度而论,不少学者从王韬的自述中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前期“消极应付、厌恶不已”,后期则“积极参与、引以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觉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态变化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将前期厌恶抵触的原因归结为传教士中文功底差劲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内在抗拒”。童元方⑧《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认为,后期翻译寄托了王韬“经世致用”的抱负。“以器通‘道’、藉‘器’见‘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构成了佣书墨海的王韬独树一帜的思想内涵。不论王韬自身是否满意,他的翻译工作却在“第60届传教大会报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罗香林⑨《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也对王韬参与的“代表本”《圣经》报以“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的肯定。
2、香港英华书院
1862年,因政治避难而客居香港的王韬给理雅各当起了助手,工作性质与在上海类似——翻译。不同的是,这次是把儒家经典译成英文,使“东学得以西渐”。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肯定了王韬在中西文化传播中的突出贡献,并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韬参与的不少细节,比如面对浩如烟海的各家注释,王韬不因个人喜好偏重一门一派等等。在英华书院的几年时间里,王韬直接参与翻译的经书共5部,分别是《书经》(第3卷)、《诗经》(第4卷)、《春秋》、《左传》(第5卷)、《礼记》(第7卷)。在与传教士的合作中,“华夷之辩”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传统文士的内心。如果说在上海翻译《圣经》的王韬多少存有“获罪名教”的痛苦与不安,那在香港翻译《中国经典》则充分填补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虚荣心。王志宏《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深刻洞察了王韬的上述心态,并把这次的跨文化传播与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触进行对比,得出了“尽管传播方向各异,却都秉承‘以儒学为重心’”⑩的结论。由于在上海有着十几年与西人合作译书的经验,外加自身深厚的经学功底以及对“东学西传”的积极态度,王韬在英华的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理雅各将其誉为“最博通中国典籍”的学者。王立群《王韬与近代东学西渐》也认为正是王韬扎实细致的工作使译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三、王韬与西学论著编撰
王韬一生著述颇丰。据学者统计截止目前约有40余种。这些书目中,涉及西学与中学的含量大体相当,而站在历史角度看,显然对西学的介绍更具分量。
1、科技类书籍编撰
王韬在上海除协助麦都思翻译《圣经》外,还花费大量时间与其他传教士们合译科技类书籍,主要有《格致新学提纲》(与艾约瑟合译)、《重学浅说》(与伟烈亚力合译)、《光学图说》(与艾约瑟合译)、《西国天学源流》(与伟烈亚力合译)等四本。《弢园著述总目》中对此做了记载,一部分学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等都对上述内容进行了考证和详尽分析。作为“译者”的王韬工作同时也留心西学知识,竭力让自己成为“学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译本为原始材料,另外编撰了《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证了其内容和材料来源。可以说,王韬在介绍和传播西方的科技知识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2、文史类书籍编撰
在国外文学作品翻译方面,王韬可谓是最早的“试水者”。李景元⑿《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指出翻译外国文学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韬,并将法国《马赛曲》的早期翻译归功于他。此外,这篇论文还引述和评价了王韬“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体必纯”的翻译主张。
在王韬的众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当比例,其中尤以《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两部影响最为深远,在当时的中、日两国均引起较大反响。邹振环⒀《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介绍了王韬编撰的历程,并给予《普法战纪》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欧洲当代专史”。忻平⒁《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则从体例、内容、评析等方面深入解读了这两部史著,认为“王韬治法国史绝非单纯为学术”,还寄托了个人“振兴中国”的夙愿。王韬对以法国史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编撰对近代国人观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导人们通过阅读西方各国历史来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3、贸易类书籍编撰
1857年,王韬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华英通商事略》问世,并于同年在《六合丛谈》连载。对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来说这部著作的意义可谓非凡,而“中国欲制西人以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的见识更是卓然超群。张广杰⒂《王韬商本思想论略》认为王韬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欧洲游历归来以后。但不可否认,“羁旅香海”尤其是编译了《华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韬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启思想的转型。
4、综合类书籍编撰
1853年,王韬逐步参与《中西通书》这部综合性科学刊物的翻译与编订,并为之作序。序中,王韬以“用心不专”、“墨守成法”概括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认为“这在当时无疑是非常先进的观念”,并进一步揭示出王韬在编撰西学书籍过程中思想转变的信号。
四、游历海外、宣道异域
跨文化传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籍,还有以声音为载体的演讲以及衣食为主体的习俗。按当时的条件,除了第一种方式的传播能做到跨越时空外,对于后两种来说则必须亲历亲为,零距离沟通。作为早期踏上西土的传统知识分子,王韬在幸运之余也多了份责任。
1、欧洲之行
1867年,王韬随理雅各前往英国,游历欧洲近三年时间。这期间,零距离接触西方文明的王韬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点,无分贵贱。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实让他自觉的承担起传播儒家哲学与文化的使命。通过《漫游随录》不难发现,王韬跨文化传播的一条主要途径就是演讲,地点包括在理雅各故乡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亚尔乡书院、在爱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对此,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据她阐述,在王韬的演讲中,“吟诵诗词”成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演讲的反馈效果来看,王韬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不是“诸女皆相顾微笑”⒃就是“一堂听着,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⒄等等。当然,这样用词难免有夸张成分,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传播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另外,演讲的顺利进行离不开精通汉学的理雅各的穿针引线,是他劲道的翻译让王韬的讲述精彩纷呈。
逗留英伦期间,王韬曾将所带的中国典籍赠送给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被誉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盛举”。对于这起“置书英国事件”的几个细节如“书籍存放何处?”“共多少书籍?”“是赠还是买?”等,多位学者间存在争议。田正平、叶哲铭⒅《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见,推测出王韬置书地应为大英博物馆,有203本共712卷中国书,被购买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韬开启历时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据此写下《扶桑游记》。但实际上,他对日本的关注早在墨海书馆时便已出发。通过英美传教士,王韬逐步意识到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变化。而凭借几部欧洲史著蜚声海外的王韬受邀前往日本进行文化交流。舒习龙⒆《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将王韬在日的文化活动做了大体描述,主要是与日本文士“相互拜谒、切磋学问、探讨诗词”。此外,舒习龙还进一步把这些文士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华文明的钦慕者;另一类则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关于王韬对日本态度的嬗变和矛盾,王立群《从王韬看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文人的日本观》认为,在王韬笔下的日本西化运动是彻底的,单从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断以威胁中国为代价则令王韬无法释怀。此外,王立群还提出,“对中国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韬也深感惋惜和遗憾。”⒇
五、王韬的办报经历
在近代口岸知识分子中,王韬的影响力可谓巨大。究其缘由,除游历海外的特殊经历外,离不开办报活动的推动。学者王立群在专著《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时间顺序,将其办报经历大致梳理如下:参与《遐迩贯珍》文字校对和发行、兼任《孖刺西报》中文附录《近事编录》编辑、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4年,《循环日报》创办,王韬的新闻事业步入顶峰。
《循环日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内容方面提出“君主立宪”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论文体则开启一代文风。王韬晚年,一部分政论文章被汇集成《弢园文录外编》出版,成为后人研究其新闻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六、王韬与格致书院
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回到上海,为献言献策。当初正因科举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韬,在人生最后的十几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给了“教书育人”,在格致书院践行自己“传播西学、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过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和傅兰雅《格致书院会讲西学章程》,不少学者(如王立群)认为,王韬接管下的格致书院与传统教育相比,从招生到教学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为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尔敏专著《上海格致书院志略》对王韬在书院“考课”等一系列举措进行详细考证和记录。
结语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关于王韬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几百篇论文的发表和五部专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说明。尽管如此,对王韬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王韬著作整理》项目获得高校古委会规划立项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论视角不断涌现,新闻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学、史学等领域的共同推进和交叉分析或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主流。
参考文献
①柯文[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6
②党月异,《王韬研究世纪回顾》[J].《德州学院学报》,2003(10)
③王立群:《中国早期口岸知识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王韬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④忻平:《王韬评传》[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⑤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⑥张志春:《王韬年谱》[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⑦⑩王宏志,《“卖身事夷”的王韬:当传统文士当上了译者》[J].《复旦学报》,2011(2)
⑧童元方:《论王韬在上海的翻译工作》[J].《上海科技翻译》,2000(1)
⑨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韬》[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韬和他的翻译事业》[J].《中国翻译》,1991(3)
⒀邹振环,《最早由中国人编译的欧洲战争史》[J].《编辑学刊》,1994(4)
⒁忻平,《王韬与近代中国的法国史研究》[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书季刊》,1994(1)
⒂张广杰,《王韬商本思想论略》[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1)
⒃⒄王韬:《漫游随录卷三》[M]:P135、97
⒅田正平、叶哲铭,《重新认识王韬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书英国事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⒆舒习龙,《晚清江苏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8(4)
篇5
Translation and Japanese culture
Zhang Xin
【Abstract】Making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developing course of Japanese culture, we can say that to use the foreign culture for reference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in Japanese history and translation is one effective and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the culture usage for reference. Japan has brought in and replanted Chinese and western advanced culture actively and selectively, made a series of social reform self-consciously and brought about the naissance of the new producing wa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hich has made Japanese society have stepped into the new history period one by one correspondingly stably. In this kind of Japan-type developing mode, we can see the business, translation, has an immense contribution and function for the culture, has brought people new concept and new idea, finished the bloodless revolution in people’s brain and also advance people to practice their opinion in the social reform, so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very great.
【Keywords】Translation Japanese culture
“翻译”一词最早见于《隋书•经籍志》,当时是特指东汉以来佛教经典的汉译活动。宋释法云撰《翻译名义集》(1143年)称:“夫翻译者,谓翻梵天之语转成汉地之言,音虽似别,义则大同。宋僧传云:如翻锦绣,背面俱华,但左右不同耳。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其所无”。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早已不限于梵文佛典的汉译活动,不仅成为中国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或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时沟通不同的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进行文化交流时的重要工具。翻译本身是一大文化事业,而译者就是文化的传播者和文化的创造者。
相对于其他文化来说,翻译对于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更加重要,因为历史上日本正是通过外来书籍的大量引进和翻译,积极主动地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学习,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富有特色的日本文化的,甚至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史就是一部翻译的文化史。在这种移植和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是有意识并有选择的,既汲取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精华,又保留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使日本文化成为多元复合的有机统一体。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近代以后因为日语的翻译书籍扼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思想学说和科学技术的概要,所以19世纪下叶和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家们反过来又把翻译日语书籍当作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捷径。在这种再翻译的过程中,大量的日语词汇进入了汉语,日本人合成的观念、解说也同样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翻译活动不仅对日本文化本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波及到了中国文化。
日本在汉字传来前没有自己的固有文字,以刻木、结绳为记事方式,汉字是何时传来、何时开始使用的已不可考。根据日本第一部书面文献《古事记》的记载,四世纪应神天皇年间有百济国学者王仁进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是中国典籍进入日本的最早的记录。在五世纪时,大和朝廷就已经可以正确地使用汉文了,478年倭王武给中国南朝宋皇帝的奏文就是熟练的汉文。
为了更加直接地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630年,舒明天皇首次派出了遣唐使,在以后的三百多年里先后派出了18次遣唐使,实际入唐15次,致力于输入唐朝的典章制度和思想文化,并在日本普及推广,结果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日益广泛。连朝廷官职也多模仿唐朝名称,建筑、风俗、朝服等生活方面也是唐风盛行一时。
随着平假名、片假名的使用,日本文学出现了日语的表现形式――和歌和物语文学,但在内容上也同样受到中国诗文以及古小说的影响。在最古的和歌集《万叶集》中随处可见中国六朝诗以及唐小说《游仙窟》的痕迹,紫式部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也被指出是受白居易《长恨歌》的启发。
当时日本派出遣唐使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中国学习佛教理论。日本虽然佛教盛行,但是受戒制度尚未确立,中国的高僧鉴真和尚为了弘传佛法,毅然前往日本传道。途中遭遇七十余次危难,历时十二载,以至双目失明,才终于抵达日本,为以天皇为首的日本信徒授戒,并开创律宗。鉴真还携来数百卷佛经,东大寺设置了写经司,从鉴真处借出经卷加以抄写。鉴真受到日本人民的敬爱,直到死后一千多年的今日,日本在鉴真圆寂之日还要举行纪念活动,可以说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可以说有两次。第一次是630年-894年间的遣唐使时代,当时中国正是封建经济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时代,而日本则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当权的新贵族富有进取心,在260年间先后向中国正式派遣了18次使团,大批的留学生和学问僧随同前来中国学习,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典章制度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改革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和巩固。
第二次是在近代。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那么第二次则主要是中国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对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中国是一个莫大的震动和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