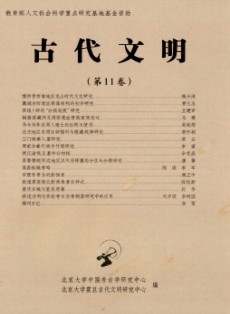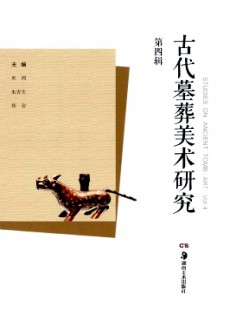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6 14:43:38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古代文学研究综述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原始社会的神话传说和歌谣,在人们口中代代相传,经过漫长的时间,才用文字记下了一鳞半爪。尽管零星破碎,但却是最早为人知的历史,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候人兮猗”,是比较可信的夏代歌谣,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语言简陋,却记载了原始生民真实的生活。
至文字产生之前,文明就已经存在,文字的产生是文明产生的标志之一,从结绳记事,到甲骨卜辞,再到钟鼎铭文,文化借助文字延伸,如果说原始社会,诗乐舞一体,那么到春秋时期,诗歌从乐舞中独立分化出来,产生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风格,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浪漫主义风格,便是文明的一种进步,而先秦文学文史哲不分的状况也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互有侧重,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禅学之于唐宋文学、理学之于宋明文学;包括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等都标志文学的发展与成熟,在漫漫文明长河中流光溢彩。
纵观中国古代文学,我们不难了解,古国的成长与曾有过的辉煌。我国一直以来就缺乏古籍整理方面的人才,老一辈的古文献研究学者,他们旧学根底好,博学多识,且有丰富经验,然这笔宝贝财富,被时间无情地渐渐失去,中青年一代又跟不上,青黄不接,一方面,这一阶段的人旧学根底不好,两一方面,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阶段,只有极少人能够沉淀下来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国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各学校设置了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硕士、博士点,但想要超越前人的成就,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古代文学在古代的价值与意义自不待言,倘若百无一用,就不会有产生的土壤,纵而观之,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也不无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传承真、善、美。就古代文学本身而言,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艺术的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求真、向善、尚美。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向善体现为“人文关怀”,尚美体现为“文体升华”,三位一体,相互交融,是人类三个最根本的精神世界:认识、伦理与美学,给人以感染,引起情感共鸣。古代文学的研究因此显得更加有必要,它对于培养以“真、善、美”为内在核心的人群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中国古代文明,大体看来主流思想不外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人际关系新的认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而强调“德政”则体现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历史责任感、使命感,这一点纵使在今天也有着莫大的指导意义,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单个的人,追求“无为”洒脱,是精神层面的另一种反应,且无论是儒是道,共同汇注了中国人独有的性格特质,连接起了祖国灿若星辰的历史文明,古代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教导我们前行。
第二、研究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儒学,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修养方面,也体现在维护社会秩序层面,表现了对政治的一种美好理想。《礼记·大学》提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是对和谐的一种比较早的阐释,《礼记·礼运篇》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为人们构建了一个理想社会,这些都为社会和谐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深化古代文学研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和谐共融。唐太宗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文学作为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不容忽视,它有利于培养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以社会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团结各个名族的人民,有利于传承中华独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不可能终止,文化的传承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敞开国门,就走入了全球化的世界中,机遇与危险并存。如何保持本民族特色,始终值得思考,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古代文学在面临现代文化的冲击下,日益边缘化,所以文学研究者更有责任深化对它的研究,疏源流,传文明。
“无用之用”意即世俗世界中,没有直接而实际的效用的事物,往往有着间接不显著的大用,研究古代文学对于当今社会的价值意义,也在于此,它帮助人们感受真善美,传承中国文明,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芳民.展望、回顾与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高层论坛综述[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3(4):171-17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VOL4:270.
篇2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篇3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66-01
一、民谣概论
民谣:民谣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民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性格色彩,民谣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所以各地民谣的风格亦有不同。看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候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已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谣,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二、民谣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则不仅掀起过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热潮,而且一些大家、名家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探讨研究工作,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曾有文章和专著研究民间歌谣。朱自清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歌谣课程,当时甚至还发行《歌谣》周刊,民间歌谣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空前的关注。研究民谣语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民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旨在分析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八十年代后,古今民间歌谣一度淡出了学者们的视野。近些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虽然日益兴盛,但是这些学科特别强调田野调查,而忽视文献研究,此外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漠视古代民间文学创作,文献上的古代民谣因此备受冷落。这使得古代民谣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止步不前。
三、文献整理分类与分析
政治角度的分析是基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角度。从当代的政治角度看待历史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项研究突破。如茹宁的《政治民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将政治民谣的流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将政治民谣作为一种有利的工具将其应用。
民族文化对于时代的潜移默化影响,使上世纪末的民谣研究出现的新的视角又将人们的一部分视线从当代的时尚风潮中拉了回来,国家的重视使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此时的民谣研究已从繁荣阶段继续红红火火的发展着,尤其从广度上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尹明举、薛家太、蒲亨强、许钰、陈子艾等人将各民族深处的优秀的民谣进行搜集、整理,不断壮大着民谣的队伍。但此时的民谣研究在深度上并不尽如人意,只是一味地纪录、整理,却未从中得出新的文化结论和研究成果,过于表面化的研究,未能给绚烂的民谣文化研究添姿加彩。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此时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如孙玉石的《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何中孚编《〈民谣集〉序》中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杨文全、李治儒《试论当代中国民谣语的语言特点及修辞策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并分析了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张海欣在《浅论民谣在当代的发展》中试从时政谣、校园谣、手机谣三大方面对当代民谣的内容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从成因、传播、民谣自身的魅力三方面探索当代民谣的繁荣原因;刘晓贵的《从政治性民谣中透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针对政治性民谣这一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能对政府作风起一种“良药苦口”的作用;控制不好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控制得当则能够缓和转型期政府与民众的不顺畅关系,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 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个人间接,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的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篇4
【关键词】《红楼梦》;《源氏物语》;贾宝玉;光源氏;对比
一、作品简介
《红楼梦》成书于中国封建王朝末期,作者曹雪芹经历了家道中落人生悲喜后,思考历史趋势,结合生平经历,淡看时间沧桑,十年呕心沥血终于谱写出了位于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的旷世经典。它以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家庭的腐朽生活为全文背景,以宝黛爱情和婚姻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衰亡为情节,揭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并揭示出封建社会必将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而《源氏物语》比《红楼梦》的出现早700年,由平安时代的没落贵族紫氏部执笔完成,它被公认为世界最早的完整的长篇散文体写实小说,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最高峰。作者紫式部主要描写了源氏的爱情生活,他在俊丑不一的一堆女子中努力追求情爱,在政治仕途上一心追求一席之地,但人生的可悲和虚幻,最终使他万念俱灰,丧命中年。故事以平安时代为背景,讲述了奢华糜烂的贵族生活和在冰冷的环境中的身不由己,以及极度渴望爱情滋润的人性。揭示了女性的悲剧命运,体现了虚无观和对无常命运深深的哀伤。
二、男主人公对比
男性作家曹雪芹和女性作家紫式部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地描绘了她们的复杂性格与丰富心理世界、艰难的生存境况和悲剧性的命运。《红楼梦》中的男主人公贾宝玉和《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作为封建男权社会的代表人物,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共性,但是由于作者受本民族文化的熏陶,受所处时代的限制与作者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他们笔下的男主人公人物形象不可能是相同的。
(一)唯美。对于《红》和《源》这两部文学巨著,都以一个男主角展开描述,而在人物设计和写作手法上,无论是曹雪芹还是紫式部,都给予了笔下的男主人公从内到外的极尽完美。
含着美玉出生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嗔视而有情”,单是外貌就芳华盖世,无人能及。其次,在性格设定上,又赋予了宝玉对功名利禄的淡漠,和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再次,在对待女性命运方面,宝玉更超凡脱俗,他不仅把女性放在一般的男子之上,更把她们放在了自己之上。贾府之内,从上到下,从贾母到王夫人,从众姐妹到寻常的丫头侍女,甚至是地位低下的戏子,他都能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爱护。由此可见,贾宝玉的形象,是完美的充满了唯美气质的理想主义色彩。
与此同时,光源氏的刻画也展现出了一个几乎十全十美的男人形象。他从小就色艺双全光彩照人。“这小皇子长得异常可爱,即使是赳赳武夫或是仇人一看见他的姿态也不得不面露笑容。”由此可见光源氏的容貌之秀美。接着,光源氏又被赋予了绝世才华与生性浪漫的情愫。“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清音响彻云霄”。而且他的“风韵娴雅、妩媚含羞”的姿态更是从小就令人惊叹不已。与宝玉极为相似的是,虽然光源氏生性好色,放荡不羁,但却屡次被作家美化成了一个有始有终的妇女的庇护者。
(二)泛爱。纵观两组作品,《红》和《源》的男主人公所处的生活环境都是香韵缭绕的女儿国,对于女性,贾宝玉和光源氏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点,都具有泛爱的特性。但是,由于贾宝玉作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 ‘泛爱’与新兴的民主要求息息相关。体现了最初的男女平等意识和对女性的欣赏、赞美、关心、照顾,可谓一副菩萨心肠,而不求回报。总体来说,贾宝玉对女孩子的态度是尊重的,注重情感的交流,而疏于两性关系。
而与之相对,光源氏的‘泛爱’,与封建等级制度密切相连,他作为一个为仕途地位奋斗终生的封建阶级代表,对于女性的爱更多的是非理性的,对于女性的情感更多的体现在对情人的温存体贴,有情有义,悉心照顾上。
(三)悲观。《红》和《源》在人物描写上都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与身边女性产生感情故事推动情节发展。但是作品中的人物,无论男女,都成为苦的化身。最终都以出家遁世或死亡得到最终的解脱和救赎。两部作品都满载着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无常观念,处处体现着悲彩。
贾宝玉作为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外表光鲜,锦衣玉食,但内心却一直不得平静,对表妹黛玉深爱,却不能违背家族意志娶了表姐宝钗,抑郁不已。对社会陈规的抵触,对家族约束的不认可,在成了他彷徨的生命轨迹,最终家道败落,看破红尘,大彻大悟,回归太虚幻境。
光源氏是世人眼中的美男子,光彩动人,人人羡慕,但是每得到一个女人的爱就多一分愧疚,在众多情人的相互妒忌中愈发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更是由于爱侣紫姬去世,最终悲观厌世,一心渴望早日遁世,终于还是归隐佛堂,悄然逝去。透过源氏的身世命运,从他的用世,到玩世,最终超世,映射出了佛教人生苦海无涯,四大皆空的观念,
三、主题思想类似的原因
比较两部作品,虽然成书于不同年代更是在不同的国家,但在描写由盛而衰的社会发展方面却惊人的相似,分别谱写了一道缠绵婉曲的封建主义末世哀歌。两部作品都以大量的描写展现了当时上流阶级社会的荒奢华,但这种盛世场面更多的是为了结尾的哀伤做出强烈对比只用,不仅反映了作者对世事无常的哀叹,也体现出盛极必衰的社会发展规律。两位作者在抒发悲剧主题时对封建贵族必将没落的预见,并不是巧合。中日文化源远流长,社会制度也有很大的关联性,更是处于相同的东方文化体系,侵染着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的东传,都为两部作品的内在气质相似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 紫式部著,丰子恺译.源氏物语[M].人民文学出版社.
篇5
江浙元末明初的五家诗派中,吴中派是学术研究的热点,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周明初、程若旦《元末明初吴中文学研究综述》[10](P37-42)从综合性研究、文学思想研究、社会文化研究等宏观方面,以及作家作品、诗社研究等微观方面入手,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吴中文学论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该文未尝涉及的重要研究成果还有廖可斌《论元末明初的吴中派》,晏选军《元明之际吴中地区士人群体与文学思想研究》[11]。元代浙东地区文化鼎盛,文人辈出,特别是在元明之际,浙东文人阶层因其与朱明政权的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董刚《元末明初浙东士大夫群体研究》、王魁星《元末明初浙东文人群研究》、魏青《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12]关注浙东文人的生平出处与政治选择,都将文人命运放在元明易代大环境下考察。后者主要选取刘基、宋濂、戴良三人进行研究,分别考察了他们的生平交游和文学创作。饶龙隼《元末明初浙东文人择主心态之变衍及思想根源》[13](P73-79)通过浙东文人择主心态的变衍,反溯其根源在浙东“正学”:将“正学”施之政治,陷入天下是否为公的悖论,终使择主失败。江浙郡邑文学研究方面,欧阳光《论元代婺州文学集团的传承现象》[14](P380-400)粗线条勾勒了婺州作家群的传承情况,并扼要分析了形成这一文学集团的历史原因。徐永明《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体研究》[15]以浙江婺州地区的文士和文学为研究对象,描述了当地的诗文创作情况,并为黄溍、胡助、吴师道、宋濂、王祎五人编制了年谱。杨亮《宋末元初四明文士及其诗文研究》[16]分析了宋元之际四明文士的心态及其文学理论与主张,并对舒岳祥、戴表元、袁桷的诗文活动分别设章进行了研究。崔志伟《元末明初松江文人群体研究》、朱传季《元末明初杭郡文人集群研究》[17]两篇学位论文则关注了元末明初松江和杭州的文人群体和文学现象。
江西元代的江西文学十分繁盛,取得了巨大成就,今人有以下研究成果:刘明今的《刘辰翁父子与宋元之际江西文坛》、《吴澄与宋元之际江西地区文学批评的风尚》[18]两篇文章聚焦元代江西重要文人刘辰翁和吴澄,分析了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江西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思想,并提出江西地域文学特质有异于其他地区。饶龙隼《南唐故家与西昌文学》《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西昌雅正文学的生长历程》[19]二文聚焦江西泰和(西昌),将该地独有的文化气质与南唐时期旧家古族迁居于此联系起来,并发掘其深刻的文学意蕴,认为其雅正和平的文风与明初台阁体的出现息息相关。唐朝晖、欧阳光《江西文人群与明初诗文格局》[20](P141-145)与饶文的结论颇为相似,该文认为江西文人群以其独有的性格特征,在明初得以超越吴中、越中文人而成为文坛的主要力量。其典雅淳朴的诗风文风与明初政治文化需求趋向一致,从而成为文坛的主导风格,并深刻影响了台阁体。刘建立《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以刘壎、李存为研究中心》[21]以元代陆学与江西文坛的交叉为切入点,以刘壎和李存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介绍元代社会思想潮流和江西文坛风气基础上,分析了刘壎与李存的陆学思想,以及在陆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学理论与诗文创作。
大都元大都是元代政治中心,也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辛梦霞《元大都文坛前期诗文活动考论》[22]主要考察了1215年蒙古攻占燕京至1315年元朝开科举的一百年间,以燕京及大都为中心的文学圈内,文人群体的诗文活动。该文以准备、开端、融合、前奏为次序描述大都文坛的历史发展,全景勾勒出文学的盛景。杨镰《元代文学的终结:最后的大都文坛》[23](P96-103)例举大量文人事迹,回顾了至正二十八年以前十几年间大都文坛最后的繁荣和落寞,揭示了大都文坛在沟通南北文人联系交流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最后无可挽回地曲终人散的结局。傅秋爽《北京元代文学史》[24]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北京元代文学的基本内容,包括对社会背景和文化特征的描述及对北京元代文学状况的简要勾勒,上编的主要篇幅则是以作家介绍为主的大都杂剧、大都散曲、大都诗文三部分。下编为北京元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杂论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