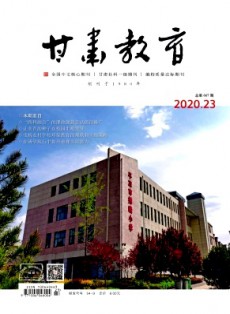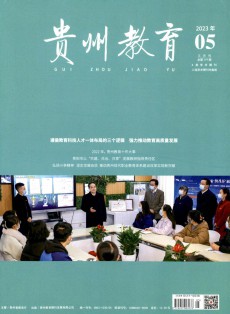教育与法律的关系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7 10:04:22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教育与法律的关系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因为人类需要在精神上寻找其寄托,从自身之外寻找更高的超越者,因此宗教从人类诞生起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甚至成为了一个文明区别于人类其他文明的标志。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必然通过相应的规范约束教徒或信众的信仰和行为,这本身也是宗教作为有组织活动的特点之一。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但前提是宗教活动包括宗教规范的内容,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活跃,各类信教的人群也日益增多。应当说,这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繁荣文化事业是有益的。但也有少数地方和部分信教的群众在从事宗教活动过程中,不遵守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有的甚至以所谓教规和信条为依据,打着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对抗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如近期浙江的一些地方在“三改一拆”清理违法违规搭建建筑时,部分群众就以“三改一拆”妨害信教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为理由,反抗政府拆除违规建筑的行为。〔1 〕更有甚者,一些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基于他们所谓的“信仰”,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全能神”组织成员在山东招远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杀人血案被抓捕后,记者问他们在实施犯罪时“你们心里不考虑法律吗,也不害怕法律吗”,犯罪嫌疑人的回答竟然是“不考虑”,也“不害怕,我们相信神”。就在审判他们的法庭上,被告人还拒绝认罪,认为他们杀的是恶魔,自己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2 〕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宗教规范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充分依法行使宗教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是今天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规范宗教活动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西方法律与宗教规范关系的历史考察
在当代中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更多的是文化方面(包括法律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严格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宗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的,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另一类是本土的,包括道教、佛教(佛教虽然也是外来的,但经过两千年的演化,已经完全本土化了)等。就宗教形态而言,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是有着很大差异的,它更倾向于帕森斯所提出的“弥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即教会缺乏组织度,而且有关的宗教信条与规约完全渗透入民众生活中,是与从饮食起居到生产贸易等种种活动相联系的宗教社会形态。〔3 〕这种宗教文化更多地是属于人生哲学意义上的,并且基本上已经世俗化。而外来的宗教情况相对就较为复杂,它们基本上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和严密的教规,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国家法律二元并行、相互影响,并且在这种不断冲突的过程中相互协调与融合,形成了今天的宗教文化与法律文化。因此,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历程。
法国学者杜尔干曾指出:“每当我们着手说明一件发生在一定时间的人类事物——不管它是一个宗教信仰、一项道德准则、一条法律原则、一种审美方法还是一套经济制度时,我们都应从追溯其最原始、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尽力阐明它在那个时代获得的特征,然后使大家看到它怎样发展并逐渐复杂化,又怎样变为被考察的状态的。” 〔4 〕从西方法律史的视角而言,法律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伯尔曼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法律以其稳定性制约着未来;宗教则以其神圣观念向所有既存社会结构挑战。然而,它们同时又相互渗透。”“即便在那些严格区分法律与宗教的社会,它们也是相辅相成的——法律赋予宗教以其社会性,宗教则给予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敬所需要的神圣性。” 〔5 〕
当然,西方社会法律与宗教关系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时间约为公元4世纪至公元11世纪。在这一阶段,其基本特点是:教权服从皇权,教皇更多强调的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教皇和国王互不干涉。第二阶段,以“教皇革命”为标志,时间从公元12世纪至公元16世纪。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皇权服从教权,依据是所谓“太阳和月亮”理论,教皇是太阳,国王是月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无权,他的权力同样是因教皇加冕而产生,因此必须无条件服从教皇。罗马教会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教法体系的建设,确立教权统治的。第三阶段,时间大约是16世纪初至今。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路德教会改革后,形成了新教国家与罗马教廷全面对立、对抗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法国政治理论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布丹认为,国家主权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性,它高于其他政治权力,不受其他政治权力的约束。法律仅仅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源于主权。国家主权在整个国家范围内都是不受限制的,它在本国范围内可以绝对支配一切。〔6 〕这一理论对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制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此后的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则论证了确认“主权国家”的重要性。通过三十年战争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家主义的国际体系,从法理上确认国家的主权特征,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国家在边界内拥有最高(绝对)权力,废除了教会对国家具有的高于主权的政治权威,否定了天主教超越国家主权的“世界主权”。由此,国家“主权”原则也成了国际法的基石。
从西方法律与宗教关系发展的进程,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虽然宗教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但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法律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宗教则逐渐失去其公共性格,丧失其政治性和法律性”,〔7 〕新型的由“世俗法”支配宗教活动、规范宗教行为的关系逐步形成了。
现代社会法律与宗教的关系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其基本要义是法律保障宗教自由,宗教在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外有着极大的自治权,但前提是不能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如伯尔曼所说:“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教会本身,其内部要有一种新的法律来指导它与上帝的关系,以及基督徒相互间的关系;在世俗法方面,也要有新的态度和新的政策。单个的基督徒在其世俗活动中要服从世俗法,教会作为整体在它与‘世俗’的关系方面也要受世俗法的支配。” 〔8 〕
可以说,这一原则也基本上反映在现代国家的法律中。美国宪法和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保护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活动。”但宗教自由的内涵是什么?宗教活动是否可以超越法律的规定?对于这一点,似乎有不同的解释。其实,正如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在《宗教与美国宪法:自由活动与公正》一书中所指出的,对宪法宗教活动自由条款含义最有价值且具有法律意义的指导资料,是那些在独立战争爆发后、权利法案通过前制定的州宪的内容。以1776年《马里兰权利宣言》的规定为例:
“因为每个人都有义务以其自认为最可接受的方式礼拜上帝;所有以基督教为信仰的人,都平等地享有保护其宗教自由的权利;因此无人可被任何法律,基于对其宗教观点或信仰的考虑,或因为其宗教实践,而在人身或财产上受到恶意干涉;除非,在宗教表象之下,任何人将破坏州的公共秩序、安宁或安全,或将侵犯合乎道德的法律,或是在自然、民事,或宗教权利上,伤害他人。” 〔9 〕
显然,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宗教自由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不得因宗教行为违反法律、危害公共安全或是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而宗教行为却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违反法律原则的宗教规范不被承认。在后来的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但宗教规范与宗教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违反国家法律的宗教规范将不被认可。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上升为法律制度的理念,也是我们今天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二、法律与宗教规范的法理思考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中,对于宗教的法律规制,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并看待国家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关系。
宗教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必然有自身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其教徒和信众的行为,但前提是这种规范不得与国家法律相冲突;同样,在此前提之下,国家法律对这种规范一般是不加干预的。但如何准确把握好两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教徒也好,信众也好,实际上具有双重身份:就其所信仰的宗教而言,他们是教徒或信众,按照宗教规范具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就他们所在的国家而言,他们又是国家的公民,依照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享有权利,承担和履行义务。但如果两者的规范要求发生冲突怎么办?美国宪法学者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立法机构或法院是否应当直接基于某人的宗教信念或根据其他标准——比如“良知”,它包含宗教信念但是并没有在它们自身与其他类似的非宗教信念间进行区分——创造豁免性例外。他还举例说,政府应当允许宗教和平主义者或是所有的和平主义者免于入伍,还是拒绝为任何和平主义者提供例外?假设一条普适规定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应当在学校待到十六岁,那么政府官员是否应当允许某宗教组织在此之前就将让他们的孩子辍学,从而为这些孩子的社会生活进行职业训练?一个州禁止食用佩奥特(peyote)(一种产于西南得克萨斯及墨西哥沙漠中的仙人掌,具有致幻作用),它是否应当允许某个教会的成员食用该仙人掌以作为他们礼拜活动的中心仪式?一项禁止在雇佣合同中进行性别歧视的法律是否应当对只允许男人担任神职人员的宗教组织听之任之?〔10 〕显然,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还必须从法理上厘清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
宗教信仰自由就其内涵而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仰自由,二是行为自由。就信仰自由而言,是指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个宗教里,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过去信教现在不信教的自由,也有过去不信教而现在信教的自由。从本质上讲,宗教信仰自由是信仰者的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没有界限的,因此国家公权力对这种纯粹属于内心的信仰是无需加以限制的。因为听命谁,服从谁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完全是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的问题,法律不得干预个人内心上的自由,不得干涉个人的内心活动。同样,他人也不得干预别人的精神自由,强迫别人信教或者不信教。一旦发生这样的行为,法律就应当进行干预,其目的还是保障公民个人的精神自由。因此,就这个层面的宗教信仰自由而言,属于一种绝对的自由。
但我们知道,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并不仅仅停留于内心的信仰,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如具体的仪式和活动表现出来的;同时,信仰本身也伴随着各种戒律,因此形成了相应的宗教规范,并通过这些规范约束教徒和信众的行为。这些行为和规范的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规制。那么如何来界定其中的界限呢?肯特·格里纳沃尔特对此提出了“利益说”。他认为:“如果个人根据宗教权利要求免受政府规定的普遍要求的限制,那么就存在两个显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即该宗教权利和与之对立的政府利益的说服力(无论该利益是属于政府自己还是政府试图保护的某个群体或个人的利益)。这时存在两种利益,第一种利益是该普适法律带来的利益,第二种利益是不为那些提出宗教权利的人提供豁免,从而不会与其他该法律限制的个人区别对待,前面提到的第二个因素中的政府利益并不只简单地是第一种利益,而是第二种利益。另一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这一有可能存在的豁免在执行中的可行性。” 〔11 〕也就是说,宗教行为和宗教规范应当服从于公共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而这种利益冲突的界限应当是由法律来进行界定的。
对于这一点,即便是主张宗教与法律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伯尔曼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需要保全法律,使它免遭不相干的并且可能是有害的宗教上考虑的干预。毕竟,无论它可能还是别的什么,法律是一种制定、解释和适用规则的高度错综复杂的程序和技术体系。这种体系未必因专注于个人的道德问题而受惠(更不必说个人精神性问题了),却可能因此受到重大伤害。” 〔12 〕
从司法实践而言,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就是美国1879年的雷诺德(又译雷诺兹)诉美国案了。〔13 〕摩门教是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宗教团体,实行一夫多妻制,而那时联邦法律并无反对重婚或一夫多妻制的规定。到了1862年,《莫里尔反重婚法案》通过,规定在整个美国,一夫多妻制为非法。187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普兰法》强化了《莫里尔反重婚法案》的规定,但引起了摩门教的不满。1874年10月,雷诺德因涉嫌重婚罪被政府起诉。然而,第一次审判以政府失败告终。1875年10月,雷诺德再次被诉。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摩门教徒雷诺德被地方法院判为重婚罪。雷诺德对此不服,他以宗教信仰自由受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并称此制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能建立和培养家庭与精神环境,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注重家庭和道德观一致为理由,上诉至最高法院。摩门教徒们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定会推翻原先的有罪判决。然而此案的结局却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败诉了。最高法院的判词指出:“美国宪法保证公民的信仰自由,这和在法律上对公民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不冲突。信仰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的心灵、灵魂的生活状态,是人的本能。法律保护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自由,不于涉人的内心活动。另一方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则没有权利用精神上的自由来代替行为上的自由,或打着精神上的自由的旗号在现实中不受约束肆意妄为。当信仰或者说宗教教义从单纯的教条变成具体的人的行为,在社会上实现的时候,它就必须承担起这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否则,任何人都可以在信仰或宗教的名义下作恶。如果有人相信,以人殉葬也是一种宗教仪式,难道也要真的允许他们这样做吗?将信仰的自由和行为的自由混淆起来的个人难免要触犯法律。在合众国绝对主权下的社会结构法不允许重婚。一个人可以以宗教信仰为由而反其道行之吗?允许这样做将使那一宗教信仰高于国家法律,从而等于允许每个人自成法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徒有其名。”
雷诺德诉美国案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宗教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宗教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任何宗教、任何人都不得利用宗教信仰进行破坏国家法律秩序的活动。实际上是划清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边界。
三、法律和宗教规范冲突与协调的中国实践
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样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享有的确信某一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以一定方式对其表示崇拜的自由,是公民的一种精神自由。其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1)内心信仰的自由,包括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选择或变更所信仰的宗教的自由等。内心的信仰纯粹属于内心的精神作用,是宗教信仰的起点与归宿。(2)宗教的行为自由,包括礼拜、祷告以及举行或参加宗教典礼、宗教仪式等形形宗教上的行为自由。此外,还包括宣教或布教的自由。(3)宗教的结社自由,即宣传特定宗教,以及以共同实行宗教行为为目的,来结合成团体的自由,包括设立宗教团体(如教会、教派)并举行团体活动、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以及不加入特定的宗教团体等方面的自由。
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在法律和宗教规范关系问题上,相关界限是比较清晰的。但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公民对宗教信仰的问题比较复杂,信众的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加上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人生哲学方面的、宗教信仰方面的、乃至迷信的问题掺杂在一起,从而使得不少人很难区分其中的界限。有的依据所谓的宗教规范作为不遵守法律、不履行法定义务的理由,有的甚至打着宗教的旗号对抗国家的法律,干扰和破坏正当的执法行为。因此,从法律上厘清相关关系,明确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的界限,依法规范宗教活动,是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与关键。从当代中国的实践来看,对法律与宗教规范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有关宗教行为规范的宪法原则
目前我国对宗教行为规则的基本依据是宪法,而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序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以及宪法第5条:“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从原则上明确了宪法和法律规范的最高性,明确了包括宗教组织和教徒、信众在内的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宗教规范当然不得同国家法律相抵触。
二是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这其中也包括了所有人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和权利时候的边界,这里所说的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的内涵是由法律法规界定的、并且受到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的。这也就明确了宗教自由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三是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这一规定主要保护了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精神自由的一部分,属于绝对领域,不受任何人的干涉,禁止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其次,宗教信仰不可能仅仅停留于内心,通常还伴随着一定的活动,通过一定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当这种行为与他人的权利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或者是对社会构成具体危害时,就成为国家权力限制的对象。也就是说,当宗教信仰外化成为一种宗教行为时,它就受到法律的限制。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而如果宗教活动破坏了社会秩序、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权利、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就要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最后,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所以任何宗教组织的活动,包括与国外、境外宗教组织之间的联系等,都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不能受到外国势力的支配,更不能依仗外国宗教势力和宗教规范对抗国家的法律,这也是国家法律主权在宗教问题上的具体体现。
(二)规范宗教活动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目前有关宗教活动的法律规范包括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四个层级。法律层级的有《民法通则》、《刑法》、《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等,分别涉及了宗教行为民事、刑事以及自治机关宗教事务等领域的问题;行政法规层级的有《宗教事务条例》、《社会团体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等,分别是政府处理境内和境外宗教事务的基本规范;地方性法规层级的包括了一些民族自治地方颁布的涉及宗教事务的法规、条例和一些地方制定的条例,如上海市人大常委会1995年制定、2005年修正的《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等;政府规章层级的有国务院各部委以及省级地方政府的行政规章,如国家宗教事务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等。这些法律规范对于依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规范各类宗教组织开展活动,依法协调相关的利益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和规范意义,也是协调和处理政府、宗教组织和公民之间相关关系的法律准则。
(三)宗教组织的活动规范及权利义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以及按宗教习惯在教徒自己家里进行的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如拜佛、诵经、烧香、礼拜、祈祷、讲经、讲道、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终傅、追思等,都由宗教组织和宗教信徒自理,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加以干涉。我国《刑法》也设立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对国家公职人员在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情况下设定了刑事处罚措施。宗教组织及其职业人员自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在这些场所信教者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应当到宗教场所进行无神论的宣传,或者在信教群众中发动有神还是无神的辩论。但是根据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任何宗教组织和教徒也不应当在宗教活动场所以外布道、传教,宣传有神论,或者散发宗教传单,和其他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出版发行的宗教书刊。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变通处理。如一些地方的殡葬法规根据一些宗教的实际情况,规定宗教教职人员及部分信众死后可以不实行火葬,而是按照宗教习俗处置遗体;一些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区对国家法律法规的变通实行权,颁布对某部法律的实施办法时,也会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习俗采取宽容对待。
当然,由于现实生活中的宗教问题是相当复杂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依法协调和处理宗教活动则是一个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在此前提之下,在处理法律与宗教规范之间关系时,应当把握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篇2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65 ― 02
引言
近几年校园伤害事故呈现多发势态,仅2010年4、5两就月先后发生“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名师生案”、“陕西南郑男子致幼儿园9死11伤案”、“海南歹徒入校砍人事件”,2013年还发生了更为惨烈的“信阳光山闵拥军砍伤23人事件”。这一起起血淋淋悲剧在给未成年学生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的同时,也在未成年学生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同时,加剧了未成年学生家长的担忧以及对学校的不信任,教育机构也面临着巨大压力。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法律关系作为认定教育机构在校园伤害事故中责任认定的前提,应该第一时间来解决。虽然侵权责任法以及学生伤害事故管理办法分别就该类伤害事故的处理原则、程序以及责任的承担作出了相应规定,但相关问题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以期使法律的适用更加贴合司法实践的需要,并尽量的合理。笔者试就校园伤害事故中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作出论述。
一、教育法律关系说
(一)行政合同关系说
行政合同关系说认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教育行政合同关系。支撑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力,这种教育合同从合同的签订到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合同的履行都由教育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和教育部相关规章强制性规定。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学说有其合理之处,作为事业单位,教育机构往往承担了更多的社会福利性职责、和公益职责,教育机构同未成年学生之间也确实存在上述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以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由于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由相关的法律法规直接作出规定,合同主体没有意思自治的权利,权利主体无权放弃权利,因为这种管理的权利同时也是法律赋予的一种义务,这与公法的性质相似,很容易给人一种行政法的错觉,让人误以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教育行政合同关系。
(二)准教育行政关系
该说认为双方之间仅仅是一种教育管理关系,这种关系的成立并非依据合同,而是依据教育法。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行政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一方面,教育机构对未成年学生负有保护其人身安全的义务,承担这种不利益的同时享有对未成年学生行使教育、管理权。另一方面,未成年学生接受教育机构的教育与管理,作为等价交换,未成年学生获得受教育机构保护的权利,这便是教育机构同未成年人之间法律关系内容的全部。该说认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只是一种单纯的、基于教育法律相关规定而形成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而非行政关系。
(三)教育合同关系说
该学说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成立基于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家长签订的民事合同,义务教育虽然是未成年享有的公权利,但同时也是未成年学生的私权利。这种教育民事合同的订立虽然要受到国家强制规定的种种限制,但教育合同的主体双方是平等的,教育合同的内容也是在法律给予的意思自治范围内约定的,因此教育机构同未成年家长签订的合同应当是一种民事合同。教育合同关系学说首先对义务教育属于公权利这一点给予了肯定,在此基础上还认为义务教育权利是未成年学生在教育合同中所享有的一种私权利,该学说更侧重于强调这种权利的私权属性。
(四)混合合同关系说
混合合同关系说认为教育合同是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融合在一起的独立合同类型。学生从属于学校,对学校有隶属性的一面;学校对学生行使管理的权利,与此同时学校与学生在主体上又是平等的。这种合同的类型有别于传统的民事合同中主体之间往往平等但互不隶属的特性,也不同于传统行政关系中行使管理权的主体与被管理的一方在地位上不平等的特性。因此教育合同这种主体地位上平等和隶属被管理的特质决定了其应当是民事关系与行政关系的一种融合,两者兼具,无论是单纯的民事关系,还是单纯的行政关系,任何单独的一种关系都不能准确描述教育合同的性质。
(五)两分法说
该学说依据是否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而分别将双方的法律关系区分为公法性质的法律关系和合同关系。当未成年学生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时,教育机构负有义务教育法上的法定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强行性规定,体现了国家意志,当事人没有意思自治的权利。未成年学生处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时,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是教育合同关系,教育合同的权利义务不再受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合同也不再体现国家意志的一面,而是允许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家长充分发挥意思自治。
二、监护关系说
监护关系说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关系定性为监护关系,这种学说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更具体的学说,简单介绍如下。
(一)监护权转移说
该学说认为,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期间,教育机构从未成年人父母那里获得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资格,并承继这种监护的权利。这种监护资格以及监护权利的转移自未成年人进入教育机构至其离开以前,无条件、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
(二)监护职责转移说
该学说认为是一种父母对未成年监护职责的转移,当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期间,这种监护职责无条件、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这种转移是一种责任的转移,教育机构此时将承受这种不利益。这种责任的转移是无条件的,不需要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另行约定,是一种约定俗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三)委托监护关系说
该学说认为未成年学生在教育机构期间,教育机构基于父母的委托担负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与教育机构形成委托监护关系。这种委托监护关系是一种双方不需要另行约定的默认、默示行为。
笔者认为,以上各种学说合理之处与不足之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从主体上看,教育机构在教育合同中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的,从内容上看,双方权利义务多由法律法规直接作出规定,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也要看到这些权利义务的内容却是民事性质的。虽然教育机构对接受教育者有进行学籍管理和奖惩的权利,但这种行政管理关系以教育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先决,是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而附属的一种不具有独立目的和功能的关系,因此教育行政关系说不足采信。准教育行政关系说片面的将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合同关系定性为单纯的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之所以准教育行政关系说得出这种片面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其所参考的法律规范仅限于教育法,而调整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除了教育法以外还包括义务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因此准教育行政关系说不够全面。教育合同关系说并不否认受教育权是一种公权利,但更强调其私权利的性质,然而教育合同中属于意思自治的内容却又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意味着教育合同中的私权利内容是比较有限的,因此教育合同公法性质的一面不容忽视。混合合同关系说既注意到了私权利的一面也考虑到了公权利的一面,可谓是比较合理的。两分法说划分合同性质的标准是未成年学生所处的教育阶段,未成年人与教育机构因所处教育阶段的不同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不同,义务教育阶段为行政合同关系,非义务教育阶段是民事合同关系,这种生硬的划分标准太过于牵强,也于法无据。这种区分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难以实际操作,因而实践意义不大,也与校园伤害事故的实际处理情况不符,因而理论上的意味更浓。
另外,监护权作为一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非因未成年人监护人与教育机构在签订的教育合同时就监护职责部分作出明确约定不发生转移。虽然从内容上看,监护人所负的监护职责内容与教育机构所负对未成年学生在教育机构期间的保护职责十分相似,但二者的性质却是完全迥异的。教育机构所负的职责不是监护职责,而是保护职责,这种职责的内容为育管理。另外,监护权资格人身专属性的权能属性将要试程序作为这种资格的转移前提条件,也即需要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与教育机构通过签订教育合同时就监护权利部分作出明确的约定,否则监护权不会因为未成年学生到教育机构学习,或者其他事由的出现而必然的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同样,监护职责的移转也不会因为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父母之间行成的教育合同而当然的由父母一方转移到教育机构一方。委托监护关系说之所以不成立也是因为需要明确约定作为前置条件。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监护权、监护职责的转移还是委托监护关系的行成都以约定的存在为前提。德国、法国、日本也都采用了监护权及监护职责转移约定为要试,因此监护关系学说整体上缺乏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其合理性较低。
结语
综上,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是教育合同的关系,以及教育合同附属的行政管理关系。未成年学生与教育机构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从主体上看身份是平等的,从内容上看除了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内容外,合同内容的其他部分多是由教育机构与未成年学生家长通过意思自治而确定的私权内容,因而这种合的性质更偏向民事合同而非行政性质的合同,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能虽然有行政管理的味道,但这种管理保护职能出发点是为了更好的履行教育合同的义务,具有从属性,因而并没有独立的目的。
〔参 考 文 献〕
〔1〕王利明,杨立新.侵权行为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49.
〔2〕劳凯声.中小学生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问题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02).
篇3
中图分类号:G526 文献标识码:A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of Legal Relationship and Adjustment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LI Ju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Hu'nan 425100)
Abstract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is a problem in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real life the dispute as a negative phenomenon, people often take evasive and negative attitude, in fact it's not the case, the dispute is the advanc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so-called science without sense. In the study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hools and students, only made clear respectiv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dispute ability, ensure that the school administration, maintenance of students' basic rights and interests.
Key wordsadministrative disput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review
教育行政纠纷是近几年来高校行政管理中遇到的新问题,作为具有行政管理权的高校在对学生进行管理时,还要维护学生的基本权利不受侵害。法制社会的建设使更多人的懂得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越来越多的学生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社会法制建设的进步,是值得欣慰的。但也对高校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学校的管理权无法排斥学生的权利。而学校在行使管理权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学生方面的民事权利,因此对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研究尤为重要。
1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
我国高校的管理权一直以来是政府的授权,学校代表国家行使教育管理权力,履行教育义务。在实践中,学校与学生的关系,既是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又是管理与被管理者的关系。高校的首要职能是保障学生在校期间受教育的权利,并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保障学生学业的正常完成,学生在校期间有受教育的权利。学校的管理权是建立在保障学生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基础之上的,在学校期间行使管理权,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提高自学、自理能力,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向上的学习环境,保障正常的教学秩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校生活是为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工作之前的锻炼。这是从教育管理学角度理解的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能全面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法学的角度还要求必须明确各种关系性质,要么是民事法律关系,要么是行政法律关系,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应该是一种基于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
学校在社会中担任角色和监护功能的特殊性,使之处在一个特殊的法律地位,从而决定了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呈双重复杂的特征。即学生与学生间会存在民事与行政两重法律关系。我国高校与学生的关系主要是教育管理关系与教育合同关系,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学生是发生教育教学管理关系的行政主体,学生与学校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即教育合同关系始终贯穿于学生在校期间,是产生一定行政法律关系的前置条件。高校与学生的教育管理关系主要表现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赋予了学校对学生在学籍管理、日常学生管理中的强制性支配的权利,如学生入学报到注册管理、主持正常成绩考试考核、升级与留、降级,休学、停学、复学与退学,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发放与授权等方面。日常教学管理主要指教师为了保障学生的正常教育权利对学生进行的日常教学管理,教育管理关系是学校与学生关系主要方面。高校与学生也存在缔约的关系,如在校期间高校为学生提供的住宿、供应必备餐饮条件等。此外,学校与学生之间也构成一种民事关系。
尽管在立法层面我国已确认了这两种关系,但由于它们的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解,尤其是对学校与学生管理关系理解不够,使这类关系没能得到法律的有效调整。实际上,依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司法审查只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民事关系,而不能处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管理关系。致使高校的管理权与被管理权之间的关系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使高校管理权的约束游离在司法审查之外。在现实的高校管理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这些侵权行为目前还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司法能否审查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此,必须从法律层面充分研究分析教育合同的缔约过程并认识各个阶段的行为性质,进而明确教育合同缔结形式和内容以及调整范围、双重法律关系对规范双方当事人的行为,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2 高校主体地位与学生基本权利
2.1 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与性质
在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中,当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如果学校不是行政主体,就不能成为被告,故学生的权益无法得到保证。调整高等学校行政主体资格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
学校的性质,依我国法律规定应属事业单位法人。从我国行政序列的规定来看,学校不是完全的公法法人,即学校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行政主体。在行政法理论上,为解释不是行政主体而履行某种行政职能的现象。学校虽然不是完全的行政主体,但却能根据法律的授权或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行使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学校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执行者,本身即具有相当的公益色彩,学校基于自身公共利益的属性和相关职能,也当然具有维护这种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利。因此,学校在性质上是授权性或委托性行政主体和民事主体的结合。
2.2 学生的基本权利
根据《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四项基本权利:(1)参加教育教学计划的各种活动,适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2)物质帮助权,即学生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和助学金的权力,学生有困难的学生也有权利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享有减免学杂费的待遇;(3)获得公正评价的权利,学生应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完成规定学业后有权获得相应学业证书与学位证书;(4)程序保障权,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有权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对学校、老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讼。
这些权利在义务教育阶段表现为学生根据《宪法》和《义务教育法》而享有的不可剥夺的受教育权,非义务教育阶段则表现为学生根据其与学校缔结的教育合同所享有的接受学校教育服务的权力。《教育法》规定的学生享有的四项权利是学生在校利益的最基本保障,并不是学生实际享有权利的全部。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权利义务关系,既有横向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又有纵向的行政管理权利义务关系。民事关系主体主要体现在学校与学生之间在招生录取过程中所签订的或事实上形成的一系列合同。合同是规定学校与学生之间民事权利义务的典型形式,凡是由合同规定的内容,就只能交由合同法或民法来调整,学校不享有管理权。除非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特定事项由学校行使管理权。
3 学校与学生产生教育行政纠纷的法律调整
3.1 合理、合法性的处理教育行政纠纷
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高校作为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权事业机关,具有行政执法的权利,在行政执法的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行政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合理性原则与合法性原则适用于高校行政管理的一切领域。
高校在进行行政执法的中,适用高校行政法规时,就可能遇到不同的行政法规范相互冲突的情况,正确的解决途径是选用和高校行政执法原则相吻合的行政法规范,保障学生的合法权利维护高校行政执法权。
3.2 加强对学校管理权的监督,维护学生的合法利益
在法治社会中,无论什么权力都需要制约。对高校管理权的监督与制约是为了保护学生的权利,增加高校管理权的法制化建设。在以前的高校管理中学生的权利很难受到保障,学校管理权没有必要的制约。对高校管理权的监督可以分为行政系统的内部监督、立法监督和司法监督。而司法监督与立法监督和行政系统内部监督相比,无疑更为公正、更容易赢得当事人的信赖,司法监督的方式具体体现为司法审查。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其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而在司法中适用,司法审查将有力地推动高等学校管理的法制化进程。
同时要求学校在行使必须权时必须遵循行政法治原则,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严禁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对违法、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维护和保障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监督教育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真正的做到了学校权力与学生权利的平等。
3.3 规范学生处分程序
在对一般行政管理事项进行研究后发现,在学校可以进行的众多管理事项中,对学生进行处分最具有典型性,也是最容易产生行政纠纷的。而且,由于处分影响到学校对学生的评价,是学校最严厉的管理手段,设置程序规范最有必要。因此,我们以学校对学生行使处分权为研究对象,规范学校行政管理的一般程序。
首先是调查取证。调查是学校对学生进行处分的首要程序,是对违反校级校规行为的调查取证。从程序法的角度出发,调查是对被处分事项事实的查证,是对违纪学生行为的取证行为,是对违纪学生是否做出处罚的基本依据。
其次是听证会制度。调查取证后,学校会根据基本事实做出初步的是否违纪的判断,也初步形成对违纪事实的处理意见。但处分决议毕竟涉及到学生自身的权利,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处分时,学生享有不可剥夺的知情权与申辩权,听证会制度为学生上述权利的行使提供了保障。听证会的最终结论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在评议人确定违纪行为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学校相关部门应当立即停止一切调查活动,终结纪律处分程序,并且不得以相同的理由重新进行调查。评议人确定违纪行为成立,应当交由有权处分的机关,依据调查取证的事实、按照校纪、校规,充分给予当事学生的陈述和辩解的机会,并根据违纪事实做出相应的纪律处分决定。
最后是公告与备案制度。经过以上程序之后,学校将会明确做出是否处理学生的决定,无论是何决定,学校管理部门都应该适用合适的方式予以公告,但必须保障学生的隐私权,不能在公告中损害学生的隐私。在公告后,将处理结果进行备案,记录在学生的学籍及学校的相关档案材料中。
项目资助:湖南省教育厅一般课题《教育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高校与学生纠纷为视角》
参考文献
篇4
根据相关法律对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对于民间借贷的利率,国家的控制是有一定的弹性和空间的。但以上规定却没有明确“银行”指的是商业银行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司法实践中标准不一。在当事人未约定按照某银行利率计算利息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上述意见以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四倍为参照;但在当事人约定以某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计算利息时,即使该利率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四倍,法院对当事人的以上约定应予以认可。
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往往只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对逾期利息却没有约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主张逾期利息的支不支持?笔者认为,借款时当事人只约定借款期间的利息的,是基于债权人信赖借款人能按时还款,是一种的交易习惯。但逾期还款是一种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逾期还款反而不用支付利息,不利保护交易的诚信原则,违反法律立法的本意,故应当支持;其标准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逾期给付的规定,利息和逾期利息加起来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当事人约定的利息已经是“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了,但又约定了逾期利息和违约金是否支持呢?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规定了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利率”包括了还款期间的利率也包括逾期利率,而“违约金”则是对违约行为的惩罚,故逾期利息不予支持,而“违约金”可以支持,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利息的百分之三十为限额。
9、在民间借贷中,当事人重新结算本息,并出具新的借条,经结算后的新借据所载明的数额能否认定为借款的本金?这也是人民法院矫正交易习惯下借款高利息的错位现象的重要内容。借贷双方经重新结算出具新的借条,是双方当事人对借贷关系的重新约定,应视为形成新的借贷关系。所结算的前期利息如不超过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应可以计入本金;即或超过了四倍利息,债权人不认可而债务人无证据证明是高利息又已经书立借条的,可视为债务人对前期利息的确认;有证据证明含高利息的应当剔除法定以外的高利部分。
民间借贷关系中的习俗、惯例以“准法律”的强制力量调节着民间借贷的运行秩序,其作用同样不容忽视。
将民俗习惯运用于事实的认定弥补证据不足就是途径之一。在案件事实认定中引入民俗习惯可以缓解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冲突,从而有利于保护对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对某项民事争议的事实都没有证据证明时,法院可以根据当地民俗习惯认定案件事实。例如,司法审判中常常会遇到有不少借款人在出具的借条上载明“利息5分”。是月息还是年息?利率是千分之五还是百分之五多有争议。依照四川地区民间借款习惯,“利息5分”是指月息百分之五,据此法院就可以根据这个民俗习惯推定当事人约定的利息是月息百分之五,而不能按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约定不明视为不支付利息”处。
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将公认的行业惯例作为裁判依据。如偿还部分借款的性质认定,在无法律明确规定并且有不同处理意见时,行业习惯规则就可以发挥作用。现代民间借贷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营利和临时性资金周转,因此,承担风险获取利息收益是债权人的追求目标。从实践看,银行借贷合同履行中清偿贷款的原则是先清偿利息,再清偿本金,这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行业习惯。因此,对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应当先归还本金还是先归还利息没有明确规定时,可以参照银行业的交易习惯。
除此以外,用人文关怀矫正错位缝合断裂也是法官在处理民间借贷案件时极其重要的手段之一。
1、人民法院用人文关怀审理案件包括以下内容:首先,积极正确指导当事人举证,缝合举证的断裂。当事人举证,因受法律意识、文化、身体等方面的制约,举证很不规范,或者不能举证、不懂举证,这就需要法官指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当事人第一次举证不能满足的,要指导其补证,可以突破法院一次性指定的举证期限,要不惜多次指导举证,必要时在休庭后,仍然有必要补充证据的,还可以指导当事人举证质证。其次,人民法院依职权收集证据缝合当事人举证不能的断裂。法官是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主导者和掌舵者,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必须处理好当事人主义与人民法院必要取证救济的关系。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身份或资格的限制而不能取得的证据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取得的证据,以及因年老、年幼、疾病等且因经济能力而无法举证的,人民法院应依职权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以尽可能做到所判的案件事实清楚,是非分明,裁判公正。再次,以公平分配举证责任体现人文关怀缝合证据断裂。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照有关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机械套搬法律,要充分运用人文关怀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和案件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公正合理地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2、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浓厚的亲情、友情、地缘、人缘、业缘,这就不但要求法官要运用法律法规、民俗习惯审理案件,还要充分运用人文关怀、人性审判维系伦理。
篇5
我们在进行法律教学的时候,其实也是为素质教育进行引导,通过法律的条文和条规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学生讲授法律的知识,让学生在法律的指引下不断进行个人素质教育的提升。比如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同时,一般正常情况是先给学生进行法律条文的讲解,不能泄露机密性文件或者技术,这是法律条文的硬性规定,让学生明确这是在法律上不可触犯的一个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