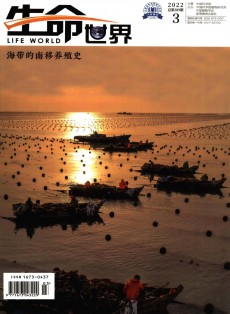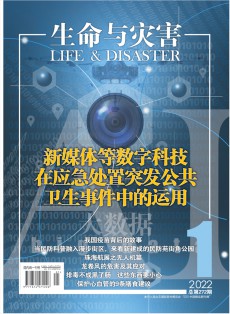生命的本真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7 17:39:18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生命的本真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关键词:华兹华斯 自然 孩童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威廉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是19世纪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主要描写湖光山色和田园生活,歌咏大自然的美。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对19世纪前半叶英国下层社会人民生活的反映;对自然的描写;对英国诗歌发展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密切、更自觉。自然是人类的哺育者,也是人类的朋友和导师,人类不但和自然有着物质上的联系,而且也产生了精神的关系,自然使人们惊叹、赞美、恐怖……,自然迫使人类斗争,使人类在斗争中变得更勇敢、坚强、聪慧。诗人正是凭借这一理解,才向我们展现了他美轮美奂的精神伊甸园。在中国,华兹华斯在20世纪70年代被介绍为:“华兹华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在肯定永恒的绝对的‘神’的前提下,把诗的目的说成是赞美人性和自然,以及证明这两者的内在联系,从而谋求人与神的契合。”“他一方面对社会现实妥协,另一方面又妄想历史开倒车,回到幻想的纯朴自然。”这一时期国内对他的诗歌和诗歌创作理论主要持否定批判态度。及至80年代,国内对这位杰出的诗人开始重新审视,给了他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到了90年代,学界开始将华兹华斯与我国的老子或陶渊明进行比较研究。虽然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华兹华斯主要讴歌了对自然和婴孩的情感,追述了自身从孩提到成熟诗人的心路历程。“自然”和“孩童”分别构筑了诗人诗意理想的两个重要要素。通过分析此二要素及其内在关系,本文得出结论:诗人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心中充满了恐惧、不安、焦躁,希冀在美丽和谐的大自然和天真永恒的儿童世界里,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当今纷繁复杂的社会,这一主题仍有一定积极意义。
一 “自然”――诗人一切的一切
华兹华斯因其大量咏颂自然的诗歌而被人们称为“大自然祭司”,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到了痴狂的程度。他对自然的描写不单局限于自然景物本身,更着力渲染的是这些自然景物在其心目中甜美的感受和愉悦的体验。他用心灵去抚摸自然中的万事万物,去聆听自然中的天籁之音,去凝视自然中曼妙无比的景象。大自然是他创作的源泉,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通过诗人的心灵进入其诗意世界,幻化成一种印象、一种向往。诗人由衷地说道:“自然对于我是一切中的一切”。华兹华斯认为与自然朝夕相处有益于人们道德水平的增长。农民自幼生活在山谷、河流、田野之间,因此成长得纯朴、勇敢、坚毅。在城市里,当人们无法逃避人欲横流的丑恶社会时,如果偶尔回顾一下过去所看过的瀑布、森林、山峦、湖泊,回想一下自己在它们面前凝神时的心情,就可以重新得到斗争下去的勇气。这种从自然中寻找力量、美感、和智慧的要求,是促使华兹华斯描写自然的动力。在华兹华斯的心目中,自然意味着美丽的乡村,乡村景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认为乡村是一个快乐和谐的世界,这里处处美丽幸福。相反在城市里,“无尽无休的社会交往消磨了人的精力和才能,损害了人心感受印象的灵感,”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人远离大自然,变得无根所依。
由此,诗人在他的诗意世界里表达了对自然界中所蕴含的人与自然亲和关系的渴望之情,他的诗歌充满了自然的魅力和田园生活的惬意,美丽的大自然在诗人心目中成了精神乐园和理想王国。投进大自然的怀抱,诗人一方面窥见了普通的花鸟草虫,听到了鸟儿动听的鸣唱,由此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表达了他对这些事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例如在《致布谷鸟》中,诗人静卧在山谷中,静听早春的布谷鸟的啼声,仿佛觉得布谷不再是一只鸟,而化成一个无形的“声音”,一个徘徊飘荡的声音,这声音既出现在身边,又仿佛回荡在远处。这声音勾起了诗人对儿时的回忆,在孩提时代,他总是被那从四面传来的呼唤声所吸引,但却不见它的踪影。布谷鸟的啼声让诗人产生幻觉,仿佛天地忽然变成了仙境,自己又一次体验到童年的天真和欢乐。对华兹华斯来说,自然界中这些寻常的草木鸟虫好似亲密无间的朋友,和诗人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陶冶了诗人的情操,净化了诗人的灵魂,在这里他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另一方面,自然界的山山水水塑造了诗人的灵魂,使他和大自然融为了一体,成为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他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时,大自然秀美的山川,清澈的湖水,蔚蓝的天空,皎洁的月光,飘浮的白云在他眼里变得更加美丽诱人,并成为诗人诗歌创作的源泉。
华兹华斯在《咏水仙》这首诗中描述了他的精神历程。诗人居住在他“不可理解的世界”中,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朋友,倍感孤独,寂寞,漫无目的。于是“独自漫步,像山谷上空/ 独自飘游的一朵云霓,/蓦然举目,望见一丛/金黄的水仙,缤纷茂密,/在湖水之滨,/树荫之下,/正随风摇曳,舞姿潇洒……。”诗人顿足凝望,立即被眼前的这番景色所迷住,孤独,寂寞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心中那种甜美的感受。这舞姿婆娑的金黄色的水仙花进入诗人的视觉,传递着温柔,友善,深入诗人的心灵深处,与诗人进行着心与心的交融,两者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水仙花如天上的星星,在闪烁。它们似乎是动的,沿着弯曲的海岸线向前方伸展。诗人为有这样的旅伴而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在诗人的心中,水仙代表了自然的精华,是自然心灵美妙的表现。但是欢快的水仙并不能时时伴随诗人身边,诗人离开了水仙,心中不时冒出孤独寂寞的情绪。这时,诗人写出了一种对社会、对世界的感受:那高傲、纯洁的心灵在现实世界只能郁郁寡欢。当然,诗人脑海深处不时会浮现出水仙那美妙的景象,这时的诗人会情绪振奋、欢欣鼓舞。诗歌的基调是浪漫的,同时带着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可以说诗人的一生只在自然中找到了寄托。而那平静、欢欣的水仙就是诗人自己的象征,在诗中,诗人的心灵和水仙的景象融合了。这首诗虽然是咏水仙,但同时也是诗人自己心灵的抒发和感情的外化。对诗人而言,此时的水仙花不再是一簇普通的植物,而变成了诗人亲密无间,知心的朋友。而诗人呢,在孤独寂寞时,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生命中永恒的契机。这里的一切处处充满了和谐,花和风,花和水,花和云等之间营造了一种和谐幸福的氛围。这种氛围感染了诗人,使诗人内心涌起一种甜美、愉悦的感受,体验着欢欣与鼓舞。水仙花――自然的化身在他眼里富有灵性与活力,医治了他孤独的心灵,给了他精神动力。此时的诗人在精神上飘游于山谷上空,大自然变成了他的精神归宿和乐园。
二 童年――生命本真之所在
华兹华斯诗意理想的另一要素是其“孩童”情怀,他对大自然的挚爱,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对童稚的迷恋和尊崇而流露的。他内心深处的孩童就像高山上的白雪,圣洁无暇。童年是社会腐蚀前的纯真状态,是人性完美的象征。正因如此,诗人才会踏破铁鞋去寻觅杜鹃鸟的踪迹,去聆听那神奇的叫声,直到召回那魂牵梦绕的童年(To the Cuckoo)。孩童是想象的天使,真理的体现,他们和大自然没有距离。他们用直观的方法去感知真理,感知自然之真谛。他们没有成人的所谓分析和智慧,童年是幸福而快乐的,因而是永恒的。像追求回归自然一样,诗人同样视童年为其精神乐园,因为童年代表了天性。在《致彩虹》中,诗人由衷地写道:“孩童是成人之父,希望在我的岁月里贯穿着对天性的虔诚。”“孩童是成人之父”看似有悖常理,但它恰恰是诗人对童真的眷恋与追求的表白,亦即对自然虔诚的爱的宣言。
诗人复归孩童的理念在长诗《永生的信息》中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明确提出了“灵魂前存在”这一理念,他认为,人的灵魂始于出生之前,是上帝在天国的恩赐,在孩童时期,人类的精神沐浴在天国的明辉中,一切是那样得纯洁、和谐与美丽。但随着儿童渐渐长大,圣洁的明辉也逐渐远去,人类的灵魂开始被世俗的杂念所侵蚀,最后明辉尽失,童真不在。因此,在他看来,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年华,儿时的华兹华斯与大自然建立了亲密而和谐的关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尽情地嬉笑玩耍,童年有不尽的欢乐和幸福。童年的他与大自然的亲和关系为他日后成为“大自然的歌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儿时的回忆成为他诗歌的创作源泉。华兹华斯把自然作为其心灵的归依,童心架起了他通向心灵伊甸园的桥梁。诗人认为,童心一旦失去,人就没了参悟自然的能力,而一旦失去这种能力,热情就会泯灭,心灵也就得不到抚慰。正是由于他对自然和孩童有如此的参悟,他才在童心中寻觅到了“真”,在自然中找到了“诚”。这二者正是诗人一生的追求。
诗人在《我们是七个》(We are Seven)这首小诗中为我们展示了他对童真的崇拜与向往。诗的大意是一位生命力旺盛,呼吸轻快,四肢充满活力的孩童,固执地认为他们有兄妹七个,而事实是其中的两个已经死去。很显然,依理性社会成人的智慧和分析方法他们只有五个兄妹,而女孩则固执地重复“我们有兄妹七个”,诗人被眼前这位充满活力,天真烂漫的女孩违背常理的回答所震慑。这位女孩尚未涉入成人世界,不知道“生”和“死”的概念,因为他们是用直觉和感情来判断周围的事物,一兄一姐生时与她情同手足,死后他们虽阴阳两隔,但墓地离家仅数步之遥,她仍与他们日日相依相伴,欢度着美好时光。虽然他们的身躯相离,但他们的心灵却是相通的,自然,他们两个不该从七个兄妹中消失,是永恒的。诗人被眼前的女孩所打动,精神得到升华。这首诗间接地反映了诗人对儿童世界所充满的天真,活力,永恒的渴求及对成人混浊的理性社会的反感。
从以上对华兹华斯诗意理想中所展示的诗人对自然和孩童的喜爱和拜敬的分析和阐释,可见“回归自然”是诗人精神追求的目的。即:追求精神乐园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回归孩童”则是诗人达到精神乐园的手段和方式。即:只有转向了过去欢乐永恒的童年,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亲和。因为只有那些“最初的感情和最早的回忆”是任何力量无法摧毁的。故此,无论在他想象的诗意世界里,还是在他晚年的隐居生活中,均表现了诗人所渴求的精神乐园,以摆脱由于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他内心深处所引起的恐慌,紧张和不安,并通过诗歌重新选择希望和永生。正可谓是一种“竞争,争论,斗争的声音,”是代表诗人所处时代的人“挑战占统治地位的现代价值观念”,是诗人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的积极思考和探究, 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这种对生命本真的执着追求精神,即使对我们生活在现代高科技和信息化时代的人们来说,也值得静下心来好好思考,从中悟出些什么。
参考文献:
[1] 傅修庭:《关于华兹华斯几种评价的思考》,《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第2期。
[2] 北大西语系资料组编:《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3] 郑敏:《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再评价》,《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
[4] 葛桂录:《道与真的追寻:老子于华兹华斯中的复归婴孩观念比较》,《南京大学学报》, 1999年第2期。
[5] Standford,Muriel and Drek Stanford,eds.Tribute to Wordsworth: a miscellany of opinion for the centenary of the poet’s death[C]N.Y.:Kennikat Pr.,1950.
篇2
书中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对人在危机状态下的情感和心态的描绘,对事业、爱情、亲情万象的诘问,给了我们深刻的启发。譬如,关于生命的本质,书中这样说:“人的个体,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缕青烟……无论它何时消散化灰,都不是真正的消失,只是一种回归。”这些颇有禅意的话语,不禁让我们感慨,人生实在没必要有太多的烦恼和患得患失。
整本书,作者基于当年的非典事件展开了新一轮的构思。类似的真实事件是本故事内容的最好支架,类似的人性反馈是本故事内容的最佳着眼点,类似的生与死的考验是本故事内容的最好思考点。一切就这样在真实和虚构的结合中以小说的形式展示给众多和平年代的读者。可想而知,《花冠病毒》饱含了作者巨大的付出和辛苦。用毕淑敏自己的话说:“暮鼓晨钟,我时刻警醒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的确是这样,这本书并不只是纸加油墨印刷的文字,它蕴含着作者的人生体悟。在这本思想性、知识性都很强的书里,不仅包含着作者绕行地球的漫长航程,以及对过去和将来世界的回眸与眺望,还包含着对宇宙的好奇和幻念。
篇3
池莉的中篇小说《你以为你是谁》在其众多小说中并未明显凸显出具有鲜明亮点的新质特征,也未引起评论界与广大读者的热切青睐与深切关注。近20年后重读此篇,掩卷品评,却发现该篇力图透视生活表象的浮光掠影,依然具有较强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新质不是它开创了崭新的文本范式,也并非它确立了独具匠心的经典叙事,而是她选择了符合当下某些特定阶层市民逻辑的话语方式,在文学受到冲击、趋向多元的传媒时代走向大众,更深刻、真诚地关爱个体生命,力图在生存本真的写实与生命诗意的消解中彰显人们努力探求诗意栖居的希望与亮色。小说以武汉三镇为背景,对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真进行写实描写,这既需作者的感悟与超越,更需在现实的生存认同之外探询生命主体灵魂的栖息。小说的标题与结尾就颇耐人寻味。“你以为你是谁”的标题,即以调侃的笔调质询自身,扣问读者。人与人生活在同一时空,却有着不同的生命体验。在探寻中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我们到底是谁?这是生命意识的自我审视、自我认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的过程。”小说中关于大学教师李某一家生活的描写与灵魂的深刻揭示,是现实生活中一类个体生命的真实具象。这个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带着小市民的虚荣与庸俗,双重人格及其客观生存的不对称性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谓的民族“劣根性”。
生命之轻与瓦罐之重消解了生命的诗意。李老师借口老婆不愿住学校而自己才不去学校住;陆武桥找其替打麻将,他本想去,却说:“等着翻译英法两种文字,要到联合国去宣读”;他吝啬,却说:“钱倒是小事,……”,这些都塑造了他清高、虚伪的形象。窘迫的经济状况扭曲了人性,使得李老师自尊又自卑、自怨而又自惭,内心也承受着现实之重。小说中写道:“李老师这个人是个自认为很深刻很有学问的人,如果他找不到凌驾于这种世俗生活之上的精神生活,很难想象他会正常地吃饭和排泄。”他生命的悲剧,揭示着深刻的生活内涵。
日常生活的悲剧生存背离了生命诗意栖居的理想,李老师的生命悲剧意蕴即在这里。在世俗的生命时空里,人们丧失了崇高与庄严的特质。正如梅特林克(比利时)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因素,它比伟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悲剧因素真实得多,深刻得多”。“可以毫不犹豫地宣称,‘新写实主义小说’所有的作家都是以生命的悲剧意识来书写现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包括那些表面上以幽默调侃的喜剧形式而构成,却是生命悲剧内容的作品。”生存悲剧的无意识或被忽视成为体现他们生命意识的重要标志。
“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作品揭示了“是环境改变了人而不是人改变了环境,人为了生存而顺应环境”这一生存法则。作品中日常悲剧意蕴与池莉对悲剧的独特理解和阐释有很大关系。邓树强、熊元义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分歧及理论解决》一文中阐述:“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这种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这从一个侧面揭示这个法则“撕裂”了人们内心某些太美好的向往。
但社会历史时空中大开大合的悲剧均无法真切地阐释生命意蕴的悲剧与文学世界的悲剧。池莉对悲剧的独特阐释使她坚持了形而上的平民阶层和市民阶层立场,消解了悲剧中的英雄光环。池莉的这篇小说中很多部分是生活场景的摄影式记录。评论家王绯称她的创作手法为“存在仿真”,但池莉更看重活着本身的意义而非形而上的活着,这使她的作品在表现生命的艰难与卑微时,同时也散发着丝丝生活的智慧和志趣。
审美地生存与诗意生活成为作家和我们共同的追求,以此对抗和拯救人的物化与日常生活的悲剧。池莉自己也说:“我的好些小说写得实实在在,但它却源于从前某一次浪漫空灵的撞击。”这种创作主体意识的自觉努力使其具有向上的力量,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和文化积淀,亦包容更多的社会思想内涵,也更趋向于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类生命栖居的理想境界“永恒地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池莉已经意识到并自觉实践着,正如她在这篇作品里对个体生命的特别关注与挖掘,将有益于对人自身的研究。即使是在当下,仍然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篇4
一、检视:当前语文教学中缺失“生命在场”,导致了课堂效果的低效
1.生命关怀意识的虚化造成了“生命在场”的缺失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教学要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道德生活和人格的养成。但教学中有时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教师对学生的个性解读的评价变得谨慎起来,只要学生能说、敢说、想说就行,至于怎么说、说了什么却不能及时加以引导,导致阅读取向偏航,道德评价失当,生命关怀意识虚化。
教学《田忌赛马》,师:田忌为什么会转败为胜?生:因为孙膑善于分析问题,敢于打破常规。生:因为齐威王太轻敌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师:你们欣赏哪一位呀?生:我喜欢孙膑,他能仔细观察事物,敢于大胆创新。生:我并不欣赏孙膑,他虽然赢了,但是投机取巧,令人所不齿。生:我喜欢齐威王,他讲诚信,赢得光明磊落,输也输得光明磊落。师:呵,有这么多与众不同的观点呀!课堂上虽然热热闹闹,但仔细想想,学生收获了什么呢?他们感动了吗?对于学生的选择,教师不应该从精神生命的层面进行价值引导吗?
2.生命诗意的苍白化造成了“生命在场”的缺失
儿童的生命是富有诗意的。他们善于用独特的情感和与众不同的想象诠释生活;喜欢用诗意的思维把客观的物体想象成具有生命气息的物体。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阅读教学成了认知的单向过程,造成了儿童富有诗意的生命的缺失。
有一则课例:老师指着一幅满树争奇斗艳的花儿和成群蝴蝶上下飞舞的插图,问学生:“这些花儿将来会变成什么?”学生说:“蝴蝶。”老师说:“不对,应该是果实。”老师让学生形容并组合有关花的句子,大部分学生说:“春天来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一个学生怯怯地说:“春天花亮了,秋天花灭了,花是灯。”老师评价:“大多数同学说得很好,但有的同学说,花是灯,那电是什么?这明显不妥。”学生富有诗意的思维却被老师无情地否定,也许生命的创新性火花再难被点燃。
3.生命体验的思想感情化造成了“生命在场”的缺失
许多课文蕴含了大量的生命教育因素。教学中,教师必须挖掘文本深处的至真、至善、至美,使学生心灵产生共鸣,思想受到涤荡,人格得以提升。然而在实践中,不少教师对文本的理解过于肤浅或有失偏颇,将生命教育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概括课文的中心,使原本充盈、真实的情感体验变为了干瘪空洞的躯壳。
教学《鸟的天堂》时,教师引导学生深谙文本言语,解读出大榕树的“庞大而茂盛”和“众鸟纷飞”的壮观景象,进而体会出作者对鸟的天堂的赞叹之情。然而此时课堂教学戛然而止,没有下文,给人留下一些缺憾。此时教师应联系写作的时代背景,当时中国正处在一个黑暗时期,像巴金这样的热血青年陷入一种苦闷的境地,借此文表达出自己对大自然这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现象的向往和追求。试想:如果教学能渗透到这个层面,引导学生认识生命、欣赏生命、尊重生命,进而珍惜生命,不是更好吗?
4.生命灵动的弱化造成了“生命在场”的缺失
语文教育应该是直面生命,提高学生的生命品质。但现今的教育将富有生命活力的学生异化成学校生存发展的工具,教师争名夺利的工具。学生在语文学习的过程中,多向的生命交流窄化为单向的灌输,丰富的生命体验异化为机械的训练,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无从体现,因而离文本的生命越来越远。
教学《牛郎织女》时,老师让学生抓住主要段落感受织女的形象。不料第一位回答的同学语出惊人:织女是“猪脑袋”,原因是牛郎无钱、无房、无权,嫁给这样的人,不是“猪脑袋”吗?立即有几位学生表示赞同,课堂顿时炸开了锅。教师本应该“以学定教”,顺势引导,可他偏偏“以教定学”:有哪位同学体会到了织女的美丽和善良呢?学生只好勉强去寻找相关语句,课堂再没有波澜,学生再难有心灵深处的体验。虽然,学生的体验偏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但这毕竟是学生珍贵的生命体验。如此,使灵动的课堂激情对话沦为“老生常谈”的活动,失去了提升个体精神生命的绝好机会。
二、探寻:“生命在场”的语文教学策略
“生命在场”的语文教学应该通过“有生命力的教”,激发师生的言语生命潜能,使教学始终“生命在场”。
1.我听到了玉兰花微笑的声音
——开启原生态生命的天性,让生命在与文本的诗意对话中得到化育
教学《广玉兰》时,老师让学生潜心读书并想象广玉兰花开时的各种姿态。生:有的广玉兰花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低着头,真是可爱。突然,一位学生发出“异音”:我听到了玉兰花微笑的声音。能听到玉兰花微笑的声音吗?同学们个个满脸疑惑。这位同学说:当我读到“盛开着的玉兰花,洁白柔嫩的像婴儿的笑脸”时,我仿佛听到了玉兰花微笑的声音。老师及时捕捉住这一教学资源:同学们,无论是花鸟虫鱼还是风霜雪月,只要我们用心去聆听,万物都有声音,让我们聆听万物的声音吧!生:我听到了太阳从大海中升起的声音。生:我听到了月亮穿过彩云的声音……
为什么能听到奇妙的声音?原生态生命的天性使然。儿童的天性是诗意的,对生活,对文字,他们有着完全迥异于成人的视角。“生命在场”的语文教学,强调顺应开启学生的原生态生命天性,把学生天真奇妙的想法当做宝贵的课程资源;教师必须真正具备开放的、创新的教学意识,活化教材,拓展教材,引导学生以自己的生命天性方式解读文本,从而开启一份生命的灵动与纯真。
2.钱学森,你是祖国的骄傲,你是科学的骄傲
——呈现“生命态”知识环境,让生命在个性化的亲身体验中得到化育
教学《祖国,我终于回来了》时,教师为了使学生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钱学森急于回国报效的赤子情怀,请学生计算出钱学森从决定回国到回到祖国,历时六年七个月。然而由于学生对这个时间跨度没有真实的感受,因此对钱学森爱国情感的认识仍是理性的。为了使学生从钱学森身上体悟到一生都需要的东西,教师适时地引导学生:你出门乘车去游乐园,等7分钟车还没来,你感觉怎样?生:太久了。师:等70分钟车还没来呢?生:真是太久了。师:是啊,那简直是煎熬。可钱学森回国经历了多少个7分钟,多少个70分钟呀!这是多么漫长的回国历程啊!生:钱学森,你是祖国的骄傲,你是科学的骄傲。生:钱学森爷爷对祖国的深厚情感,将永远激励我们成长。
学生在回忆等车的亲历感受中,深刻体验到了钱学森拳拳的爱国情怀,自己的生命内涵也受到了最丰富的影响。文本的生成往往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容易导致学生与作者对话时出现障碍。因此“生命在场”的语文教学,强调教师应将文本知识重新激活,实现书本知识与学生的生命经验世界相通,使知识呈现出鲜活的“生命态”。学生在自己的个性经历中与文本对话,便很快能与文本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获得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增加生命的厚度。
3.简洁是一种美,具体生动也是一种美
——建构绿色的“生态化”课堂环境,让生命在思想的多维砥砺中得到化育
教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于老师让学生赏析“他嘴里嚼着,嘴唇上的胡子跟着一动一动的”一句时,这样引导:如果你是一名语文教师,你批改你的学生作文,读到这样一个句子,你会写何批语?生:描写具体生动,引人入胜……忽然,有一个学生说:“这句话可写可不写,应该删去。”于老师迟疑了一下,但马上将这一问题交给学生讨论。学生很快形成两种意见:一方是不赞成删去,一方是赞成删去。对此,于老师作出了艺术性处理:简洁是一种美,具体生动也是一种美。于老师还分别与两位代表握手,对不赞成删去的代表说:“假如你将来成为一名语文老师,你的学生作文一定是具体生动的。”对赞成删去的代表说:“假如你将来成为一名语文老师,你的学生作文一定是简洁凝练的。”
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生命在思想的多维砥砺中享受到了“雨露甘霖”。“生命在场”的语文教学,注重建构绿色的“生态化”课堂环境,在这种环境里充满着生命间的民主、和谐、平等、宽松、温馨和尊重。教师要尊重学生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的不同感受,鼓励学生合理地多元化解读文本。学生在思想的多维砥砺中同文本和老师对话,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习的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保护原生态生命的灵动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精神生命的发展。
4.老师,我把春天送给你
篇5
陈越孟说:“创投,是一件非常理性的工作,需要多角度分析和调研,不能轻易相信摆在面前的那一组数据。更多时候,还需要沉住气,深入企业去了解最真实和详尽的信息。”
陈越孟的老家在宁波慈溪,附近有两座著名的寺庙,一座是千年古寺五磊寺;另一座是岳林寺。每一次去那里,都可以感受到那一份静谧和安宁。
陈越孟非常喜欢国清寺空气中弥漫的香火味,悠悠的钟磬声,禅师的诵经声。寺内大雄宝殿东侧梅亭前有一棵饱经沧桑的隋梅。陈越孟说,他最喜欢这千年隋梅。枯树新枝缀满梅花,它的顽强,它的生命力让他坚贞、敬畏。
他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立真、立美、立善。人的物质生活是主真的,精神生活是主美的,内心世界是主善的。他愿意心怀真善美,投入地工作和生活。
陈越孟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年轻时受老校长陈立和导师徐志强的影响,自今骨子里保留着一份传统,那就是对文化的痴迷。上大学时,他喜爱写诗、摄影,曾是“晨钟诗社”的核心成员,出版过诗集《15人集》,也获得过浙江省高校摄影一等奖。
他笑言:“大学时留下的踪迹,现在身上或多或少还会有,尽管现在工作比较紧张和忙碌,但自己还是会抽时间去看一下西湖,看一下荷花,有时还会骑自行车去看一下夕阳。”
他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家里只留下孩子和老人,留守儿童的生活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关照,所以生活质量很差,教育质量更差。
为此,他和朋友们发起成立了“浙江省阳光爱心基金”,帮助那些留守儿童回归正常生活。他们经常搞一些活动,为孩子们赠送书本、球鞋等,还到贵州山区为孩子们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去年,他们搞了一个有趣的“爱在后备箱”的活动,动员家人朋友把闲置物品捐献出来,放在汽车后备箱义卖,将所得费用定向捐给贵州。
他低言:“做慈善是发自内心地去做,如果为了扬名去做,就违背了做慈善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