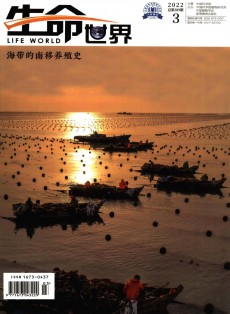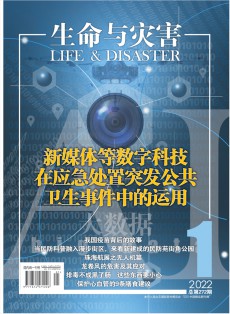生命的偶然性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9:15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生命的偶然性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行走在路上,总是有所期待。相望美丽,执著真实。追逐的目的是想有朝一日的拥有,但是慢慢感觉,这种期待很可能是破坏了那份美丽和安宁。相守、相望,似乎好一些,不至于让自己心仪的东西桎梏在自我的欲念之中而失掉了它的本真与价值。
将所有的关注聚焦于现在。从生命的偶然性出发,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一个令人为之赞叹的奇迹。试想在浩渺的宇宙间就出生了你,你的容貌,你的性格,你的一切的存在,都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偏差而不复存在,但你偏偏就在这个时刻出现在了这里,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这是不是就值得庆祝一番?《万物简史》给我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如此。所有看似高远的追求在这种偶然性面前突然是那么的苍白无力,但这也不能成为逃避生活的借口。《相约星期二》是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的故事。生命的消逝延长在十四个星期,于是,关于生命、关于人生、关于爱的隽语就这样在纸间流淌。“和生活讲和”,当死亡也可以平静面对时,生活中就没有了不能应对的事情,所有的争执也就无足轻重了。原谅自己,也原谅别人,认识一种偶然性与脆弱性之后,我心释然。之所以不放弃努力,是因为这是爱的需要,将自己奉献给别人,奉献于有价值和意义的活动。似乎一种精神性的诉求更为重要。
1月,我在阅读中相望人间,相望美丽,执著真实。
篇2
每个人都无法选择生,因为每个生命的诞生都具有偶然性。
我们活在世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使命,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碌碌无为或者奋进一生。
人来世上一次,就是来体验所有新奇食物的,而同时为了延续生命,人们得吃饭穿衣。
生命有限,选择无限,选自己所愿,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是正道。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中国画从无、从玄学出发,乃人世风景之印象。主观,求意象,求物我同一,求物皆是我,甚至就连自己亦不知所以然,故为哲理的。中国画家常与文人、官人、闲人交友,亦或自己就是文人、官人、闲人。
西洋画讲强烈,讲刺激,讲进取,以满足感官冲动。
中国画讲平和,讲退隐,讲镜花水月,讲忘却痛苦,连同理想上进一并暂且放下,以求得失意心灵的慰藉。
中国自宋代始,提出人品即画品,此为西洋画所无。如“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以此强调人之修养,强调人在画先。
西洋画讲外光,讲客观对象在外光下色彩变化引起的视觉冲击。
中国画不讲外光,讲光阴,讲浩浩阴阳移,讲悠悠千载,讲日长如小年,讲逝者如斯。因此中有对生命的感叹,是有情感的时空。故中国画地上无如影随形,水中舟船山石树木流云亦无倒影。
西洋画画女人体,求肉感,求视觉。
中国画画女人,不在画的对象,王顾左右而言他,只是对美好的寄托,亦或就是画作者自己。
西洋画之材料,硬质的笔,布,及油性的颜料,决定了作画的必然性,可反复涂抹修改塑造。
中国画之材料,毛笔,生宣纸,及水性的墨与颜料,决定了作画的偶然性,一笔就是一笔,稳、准、狠,不可涂抹,不可修改。画错了,只能毁掉,另取一纸,从头再来。中国绘画的偶然性,恰好最大限度地提供了创造性。因为一切创造均来自偶然。偶然性越大,创造的机会越多。
西洋画重技术,故要进学校受专门训练。
中国画讲方法,故拜师比进学校重要。更讲画外功夫,尤看重读书。读书的目的在增长心志,提升眼光,在超凡脱俗。真能脱俗之人,方可知道“好”究竟是回什么事。
西洋画是年轻的,当下的。
中国画是年老的,传统的。
篇4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废名与沈从文这两个名字常常同时提及,因二人作品类型、风格的相似常被划分到同一派别,诸如乡土文学、抒情文学、京派文学。他们的作品确有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京派文学,远离政治、远离社会现实而向自然贴近,在田园牧歌中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自觉地向抽象的生命本体追寻。然而我们对两个作家的比较不能只停留在共性层面而忽略其个性的一面,废名与沈从文虽同样以生命哲学为核心来展开审美、创作,但二人的思考方向却是相异的,这一相异之处在二者作品中得以体现。
废名的早期创作是偏向现实主义一派的,而小说《桥》的出现标志其创作风格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仅是创作手法的改变,更是废名思想的转变,其人生观、生命观在作品《桥》中充分展现。而沈从文的《边城》也可以说是其巅峰之作,创作《边城》时的沈从文正新婚不久,整个人生发生巨大转变。从一个乡下人变身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并娶到了心仪的妻子,这一翻天覆地的人生转变促使他思考人生、命运,向生命的深度探寻,《边城》则是沈从文思考的产物。废名、沈从文这两位作家都将其对生命的关注注入作品中,巧合的是《桥》与《边城》确有许多相似点。同样将人物放置在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小城,同样是年迈的老人抚养着年幼的孙女,小城的人同样善良淳朴,作品都具有田园牧歌气息也兼有忧伤的基调。废名与沈从文都将自己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融入桃源之中,重新构建桃源,然而他们的桃源却各具特色,呈现不同的面貌。本文将对废名的《桥》与沈从文的《边城》展开比较分析,从而探究废名与沈从文的同而不同的生命观。
一、死亡意识下的生命悲悯
“死亡”一词带来的恐惧常常令人对它避之不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关注素来少见。直到“五四”给中国新文学注入了新鲜空气,海德格尔、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哲人的死亡意识开始在中国传播。然而自觉关注死亡、直接描写死亡的作家仍在少数,废名、沈从文便在这少数之列。他们二人对死亡的关注或许是受西方死亡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自身经历有关。废名从小体弱多病,疾病的折磨不仅令他的身体与死亡靠近,也让他在思想上更加关注死亡,由死亡延伸出对生命的思考。沈从文的死亡意识则源于他亲眼目睹大量残忍杀戮和一次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切身经历,这些经历使他明白死亡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存在,无法逃避则只好面对承担,“向死而生”。
基于废名、沈从文的死亡意识,他们在作品中毫不忌讳死亡,并且有意识地描写死亡。废名的《桥》尤其明显。《桥》中有大量与死亡相关的意象,诸如“坟”“塔”“碑”等,也描写了“送路灯”“村庙”等许多与死亡有关的民俗,这些描写是废名有意为之,其自觉的死亡意识必然导致他将笔触伸向死亡。在认识到死亡的无从逃避之后,废名开始接受死亡、欣赏死亡,甚至借小林之口道出“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在《桥》的下篇第三章《窗》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小林凝视着熟睡的细竹联想到生老病死,进而联想到佛像,感叹“艺术品,无论它是一个苦难的化身,令人对之都是一个美好,苦难的实相,何以动怜恤呢”?这是典型的废名创作手法,随着意念流动的描写道出思考的核心。死是无法避免的存在,美与死同时存在,在死亡面前美愈发显出光芒与可贵,同时也不免令人心生怜悯与忧伤。在这一认识上沈从文与废名不谋而合,沈从文相信“爱与死为邻”,①认为“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②死与爱、美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存在。沈从文在《边城》中并没有像其他作品一样过多描写死亡、杀戮,然而死亡意识同样存在。故事中有这样一段:翠翠被爷爷丢下一个人站在河边时,“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望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怕人的想头,她想:‘假若爷爷死了’”。黄昏的落日象征着老人迟暮,象征着死亡。翠翠面对落日,心中油然生出对爷爷死亡与自己的未来的担忧,这种担忧也体现在爷爷身上。同样是一段黄昏时候的描写,翠翠坐在溪边,望着溪面为暮色所笼罩的一切,或许是基于同样的担忧开始呼唤在船上的爷爷,爷爷一面回答道:“翠翠,我就来,我就来”,一面却自言自语到“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死亡意识存在于祖孙两个人的心中,在表面单纯美好的生活背后潜存着因死亡而起的担忧、恐惧以及对生命的悲悯。因此,《边城》不仅仅是一曲田园牧歌,它更是对生命悲悯的哀叹。不管是废名的《桥》还是沈从文的《边城》,都是在田园牧歌的外衣之下诉说生命的悲悯、存在的困境,这种悲悯的成因除死亡之外,也由不同形式的命运导致。
二、命运未知下的生命思考
“命运”一词并不令人恐惧,人人皆有自己的命运,真正使人担忧的是命运的未知,偶然性与不确定因素直接导向人类生存的变数,从而产生对生命不可思议的慨叹。废名、沈从文作为关注生命哲学的作家,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自然也不会忽略命运的不确定性。并且他们在作品中不断表现和感慨着命运的未知与变数。小说《桥》并不热衷人物描写,更多的是思维、心念的表现,然而废名也在交代人物命运的同时表现出对命运变数的慨叹。小说中的三哑叔曾经四处流浪靠讨米为生,终于在讨到史家奶奶门下时命运发生了转变,成为史家的长工。小林遇到的和尚曾做戏子扮赵匡胤、扮关云长,最后流落到关帝庙做和尚,终日对着关公像发笑,偶然因素令其命运发生改变,却又巧妙地仍将他与关公联系在一起。小林与琴子、细竹三人出门看海,遇到的大千、小千与他们有着相似的境遇,小千暗恋姐姐的丈夫(与细竹相似),大千丈夫的死去又消除了姐妹之间的尴尬气氛,让二人重归于好、相依为命。而小林与琴子、细竹三人的命运又将如何?这仍是未知数。所以琴子才会感慨“人与人总在一个不可知的网中似的,不可知之网又如鱼得水罢了”。废名感慨命运的未知与变数,沈从文亦是如此。《边城》里造成翠翠命运转变的偶然因素是大老的死,大老是弄水的好手,常年在水上活动从未出事故,可以说偶然性是他死亡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偶然事件造成翠翠命运的转变。试想如果大老不死,两兄弟仍每日为翠翠唱歌,翠翠最终或许与二老会有个圆满结局。未知与变数其实并不可惧,毕竟变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它只会让人在回望历史时感慨命运的不可思议,真正令人感到生命沉重的是命运的变数所带来的哀与乐。因此,废名、沈从文才会在作品中不断描写命运的偶然变数,在感慨命运的不确定的同时对生命肃然起敬,对人的存在展开终极思考。
三、自然生命下的静与动
自然是废名与沈从文不可忽略的共性,他们对生命的认识与思考在自然中展开,规避一切现实来还原生命的本真。这里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自然环境,在远离俗世的自然环境中展开对生命的思考,以自然之静来衬托生命的静谧。另一方面是指最自然的生命形式,即生命的本来面貌,从而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然而这两方面的自然在废名、沈从文的笔下是合二为一的,二者不可分离,相辅相成。
废名的《桥》将人物放置在自然山水之中,在自然中进行他们诗情画意的人生。整篇小说中没有父亲的角色,父亲代表着父权文化,而废名似乎有意规避它。他认为“母亲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的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是最原始、自然的存在,废名否定父权,所渴望实现的正是这种贴近自然的本真存在。因此他让在外求学的小林又回到史家庄,回到自然的怀抱。然而史家庄绝非废名理想的桃源,真正的桃源在于梦。小林重返故园,仍在因生老病死而对生命产生悲悯,仍对人的存在产生慨叹,他真正的理想家园在梦里、在思想意识与灵魂里。因此才会说“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正如小说的题目为《桥》,废名也说最先定下的题目是《塔》,其实“桥”与“塔”只是意象而已,在小说中也曾出现,却并非实实在在的物,只是心生的幻象而已。比如《塔》一章中细竹向小林解释她画塔的原因,只是因为琴子给她讲的故事中出现了塔,而她就将话语之塔经过头脑中的成像而转为画上之塔。其实这个塔并非实在,只是虚幻的象而已,也是废名所说的梦。类似的意象遍布整部小说,而废名想要透过这些意象来构建他的理想桃源,实现生命的存在价值。在废名所造的梦境里或许可以摆脱生存的困境,可以对生命的哀痛产生短暂的麻醉,然而这种理想毕竟太过消极颓废,太过沉静而丧失了生命的力度,因此有人评价废名的《桥》呈现“僵尸似的美”,美而没有生气。这一点恰是沈从文超越废名之处。
废名与沈从文都思考生命,认识到死亡、变数等哀与乐所带给生命的沉重与困境,废名选择归于自然,归于梦,在灵魂深处创造桃源,让生命在宁静中实现其价值。沈从文与废名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能在融入自然之后超越自然,他认为“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所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即应在生存时知其所以生”,真正的“向死而生”是承担生命中必经的哀与乐,绝不逃避。所以《边城》里的爷爷会说,“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皆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方配活到这块土地上”,这才是沈从文提倡的优美、健康的生命形式。他承认“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与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与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他后天的命运”,而他也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理性所带来的勇敢可以战胜一切苦难困境,这才是生命的最高形式。这也是沈从文在自然中追求生命的纯粹、静谧的同时所把握到的动,即生命的力度。
注释
① 沈从文.烛虚[A]//友情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280.
② 沈从文.美和爱[A]//友情集[C].长沙:岳麓书社,1992:329.
参考文献
篇5
掩卷深思,同一时刻,同一块土地上,所谓“举国欢腾”下,正有人哀哀饮泣,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竟至于如此的不相同,一丝丝悲凉袭上心头。哈代完全无意于在对生活的漫画中去找寻悲剧感和喜剧感,而是把生活原样保留下来,这中间就蕴含着悲剧与喜剧的默默渗透,它已融入生活中,正是在这淡化与消失的过程中包含着一下些惊心动魄的东西。
——题记
托马斯·哈代,被予以“一个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时代交界线上的忧郁形象”,是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小说《 德伯家的苔丝》 是哈代悲剧作品中最深刻、 最成功的一部。一部小说是一个作者的灵魂深处的再现,整部小说中苔丝的形象都与哈代的思想密不可分,作家塑造了苔丝去表现“哈代的感情,他的直觉,对美感的掌握,是伟大而深沉的”。
(一)命运的悲剧
19世纪80年代的英国资本主义不仅在都市长足发展,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经营方式在农村也开始萌芽,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家长制统治下的英国农村一步步趋向崩溃,造成个体农民的破产,走向贫困。苔丝作为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又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其命运必然是悲惨的。
小说中作者为了更加突出这种命运的不可违抗性,穿插了大量的偶然性因素。老马的死;苔丝跟亚雷的相遇成为她生活中的转折点;遇见了心仪的对象安吉尔,准备谈婚论嫁,却在结婚前夕写给他的信产生了误会;一家人再次陷入无助,她被迫委身于亚雷时,安吉尔却悔改返回,无奈下的一刀,结束了一切。 在这一系列事情上,我们明显地感觉到了命运对人物的嘲笑,苔丝是天命或宿命的牺牲品;,小说中有那么多的偶然性,每一次偶然转折,都使她向毁灭的深渊坠落一层。这种偶然性,固然都是许多社会必然性与自然必然性的交叉点,但一连串的必然性,则是哈代构思的结晶和他的悲观主义宿命论的发展轨迹。
(二)社会的悲剧
麦克默特里曾说过:“毫无疑问,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来说,两性中存在着双重道德标准。女孩们被要求婚前保持贞节婚后忠贞,而男人们的情况却大不一样。 ”一个女人一旦 “堕落’,就等于毁掉了自我。她将不可避免地倍受折磨,甚至走向死亡。苔丝在围场遭受亚历克侮辱后失身的时候起,在众人、 甚至在她自己的眼里,她的身份便已不同于以前了。正是这种思想:成为她自己释怀不开的痛。她“根据陈腐无聊的习俗,布置了不同情自己的形体和声音”,用“一堆使自己无故害怕的道德精灵”来恐吓自己。即使在大自然中间,“老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罪恶的化身,侵犯了清白的领地”。苔丝按照传统的观来衡量自己的清白与否,她比别人更不能忘记自己的“耻辱”。
而亚雷为代表的恶势力及其强大的后盾——国家机器、法律对苔丝的迫害是一种无形的更可怕的精神残害。苔丝一生都是强权和暴力的受害者。亚雷之所以敢称霸四野,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不仅因为他有钱、有势,而且更主要的是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法律的保护。社会和法律都认为侮辱和迫害苔丝的人是正当的,而受迫害的苔丝则是有罪的。苔丝一生都必得逆来顺受,忍受含垢,不能自卫,而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起来自卫的时候,“‘典型’明证了,埃斯库罗斯所说的那个众神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苔丝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祭坛上的祭品。苔丝的悲惨遭遇,社会对苔丝的不公正,表明了资产阶级法律的不仁道和虚伪。
(三)性格的悲剧
在哈代的理想世界中,苔丝是美的象征和爱的化身,代表着威塞克斯人的一切优秀的方面:美丽、纯洁、善良、质朴、仁爱和容忍。因此苔丝是“一个纯洁的女人”。但她的不幸正是对她性格的讽刺——她的纯洁致使了她的轻信与天真。一位这样轻信他人的姑娘,她势必会既丧失名誉,又失去自己的爱人,这也是她不理解的,她的爱人安吉尔怎么能够不象她爱他那样,同样无私地爱着她。但若她不是这样纯朴,这样天真,她便不会这样爱着安吉尔,她也就能爱情的结局,亦不会深有负罪感,更不会说出自己的秘密,悲剧也决然不会发生。但是,若失去这些悲情性格,她也不为之苔丝了,也决然不会引发我们怜悯之情。
同时她的反抗性却不够彻底,一直受困于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她一生追求幸福,对埃瑞克敢恨,对安吉尔敢爱,在一定程度上敢于反抗旧礼教。她蔑视和否定宗教,但无法摆脱世俗观念的阴影,封建礼教压迫着她。她恪守那个时代的准则,在她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感。所有的一切,造成了最后忍无可忍的一刀。她内心绝望地纠结积郁着各种感情,性格的冲突达到了一个极限并走向巅峰,直至在悲恸与绝望中死去。
我们可以想象,在断头台中央,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苔丝的精魂,有一些说不出是什么的东西的挣扎,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隐约像是长嗥,像是一匹受伤的鹿,当深夜在城市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与悲哀。
鲁迅先生在《影的告别》中的一段话:
由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由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意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正如这段文字,那些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与自己内在的各种矛盾,就如这如怨如诉的声音,追逐着苔丝,钉子般的敲进人心里,让人感到恐怖,感到命运似毒蛇似的在尸林里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里奔驰的酷烈的沉默中的逼人的气势,这只能发自人灵魂的最深处,是时间洗刷不掉的,永远不能忘记的,却也无法逃避的生命的声音。
最后一刀,是这种绝望的反抗。它使苔丝无法避免法律的制裁,成就了苔丝的死。苔丝的死是一场不幸的悲剧是不可抗拒的偶然性,是时代的必然性,是生命的无常,这让我们觉得命运本生就是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其中每一个人牢牢捆住,没有谁能挣脱。正像赛捏卡曾经说过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的确命运可以反抗但不能战胜,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事物毁灭给别人看。苔丝最终没能逃脱命运,尽管她那么天真单纯善良,尽管她无私任劳任怨,但无常的生命不会对任何人“法外开恩”,她成了命运的。(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