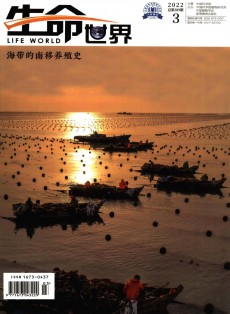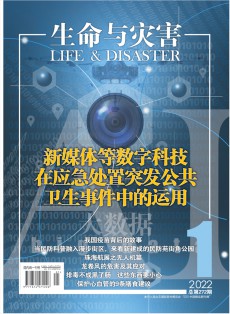生命有序性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8 17:39:19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生命有序性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一、生态文明和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涵义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按照人―自然―社会这个复合体运转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良性运行机制以及和谐协调、持续发展、全面繁荣的一种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其本质特征是自然―人―社会复合体的和谐协调。具体来说,生态文明包括了社会协调及人与自然协调的所有实质,生态文明贯穿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生态旅游建设、生态环境与保护、生态农业建设、能源和资源的保障、污染控制、循环低碳等方面,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所必然要求的社会进步状态。
(二)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
所谓可持续性发展指的就是既满足现代人的需要又以不侵害后世人满足需要的本领。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的发展和安居乐业。而作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其中一个方面的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其含意为:指满足当代人旅游需求的同时,不损害人类后世为满足其旅游需求而进行的旅游建设。传统旅游业在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而在生态文明指导下的旅游业,既满足了人们旅游的需要,又保护了环境。所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根蒂。
二、从政府的角度谈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通常政府以为其是权力的占有者,条例的制定者。在旅游行业中的表现就是,政府创造条件发展各种类型的旅游活动,支持发展旅游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到目前,我国一向倡导“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策略并在当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随着对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出现了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政府作为主导调控进行解决。在建设生态文明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对于发展我国的生态旅游有很大的鞭策作用,而我国的生态旅游的发芽几乎是由政府促成的。政府对生态旅游的治理表现在下述三个地方:
(一)拟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生态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方针,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二)找准当地的形象定位,并围绕其主题加以推广。政府必须组织对目的地形象建立有益的推广活动。必须考虑市场需求等问题,杜绝盲目跟风。
(三)为发展生态旅游创造各种条件。增加投入、鼓励外资和社会资本等投入到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中,建立多元化的投资机制。也可以让本地住户参与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兑现他们的利润分派并让他们参预生态资源保护工作,这样有益于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从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及游客的角度谈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旅游行业从业人员主要是指旅行社工作人员、景区工作人员、导游等方面。作为旅游活动的执行方,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将直接影响到旅游活动的主体――游客的行为。而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并不单单是政府、景区、旅行社等的责任,游客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游客有无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游客环保意识的程度、游客素质的高低,都将直接关系到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亦或是破坏程度。为此,我想旅游活动的执行方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以树立游客生态保护意识:
(一)作为旅游活动的组织者、执行者的各级各类从业人员首先自身必须树立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我们可以定期通过培训、讲座等方式对旅游业从业人员进行教育,丰富他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知识、生态旅游知识。
(二)旅行社在招揽游客的时候要注意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旅游的宣传。比如可以在宣传资料、网页、门市等进行宣传,使游客耳濡目染的接受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旅游的知识。
(三)景区或是旅游目的地在做好宣传的同时,还应多开展一些生态旅游活动,以此增强游客的环保意识。
(四)作为旅游形象大使的导游,他们是和旅游者距离最近、接触最多的人,能够更好的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旅游的精神。导游可以在讲解中向游客灌输生态文明意识,在具体的旅游活动中身体力行的进行示范带头作用,比如,旅游途中不乱丢垃圾,不乱涂乱刻等等方面。
四、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谈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旅游业本是资源、能源消耗低的产业,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对旅游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使我国旅游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一大批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旅游有着深刻理解,并且旅游管理水平极高的高素质人才,如何打造这样一支队伍,应该说在学校教育中,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我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四种教育途径,培养旅游管理人才:
(一)在人才培养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根据党的十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方针,并结合我国旅游业的现状,在对学生的教育中应注重生态基本知识的灌输,以及生态文明素养的培养。
(二)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关系到能否培养出具有生态观念的高素质旅游业管理人员,因此在教学内容和课程中应开设诸如《生态旅游》、《旅游景区的开发与保护》等课程,既和专业相关,又符合生态文明建设。
(三)在实践环节中融入生态文明教育。旅游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比如,教师带领学生到景区进行实地模拟导游实践。在实践环节中就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进去。开展以生态文明、生态旅游为主题的活动,增强学生的生态保护意识。
(四)培养教师的生态观念。学校可以对教师进行生态文明知识培训,丰富教师的生态文明理论知识水平。同时,可以让教师到生态旅游示范点挂职锻炼,以提高教师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水平,更新教学理念。我深信,只有教师自身的素养提高了,才能言传身教的影响学生,为生态文明、生态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五、以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的具体做法
在生态文明建设指导下,正迅速发展的一种旅游模式就是生态旅游,与传统的旅游活动相比,生态旅游品味更高,更加突出自然本色,具有更长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生态旅游才能真正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互协调,有利于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做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更新观念,营造生态文明的旅游业发展环境
生态文明要求公众具备较高的环保意识,生态旅游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开发、建设、保护、发展四者的关系,因此对旅游业的管理者、执行人、游客和其他人员需要进行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教育。有针对性的对旅游行业从业者进行培训,建造一支生态意识强、环保意识强的从业人员队伍,提高从业者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意识。同时,要加强宣传教育,引导旅游者文明旅游、低碳旅游、爱护环境,建立生态文明的旅游环境。
(二)产业结构创新,提高生态旅游产业的竞争力
生态文明建设的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今产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态旅游产业,有助于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同时,也能增强地区综合实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下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所形成的竞争力强的生态旅游产业有利于加速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要加大创新力度,要注重建立品牌、整合相应的旅游资源,提高生态旅游产业竞争力。
(三)制度创新,建立跨区域的生态旅游产业机制
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因此,政府在当中的作用不可小觑。政府的作用在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促进市场更为有效的运作。所以我们需要建立相关的产业协调机构,统筹规划、管理该区域的旅游产业,为生态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轻松的氛围。[5]同时,不应只局限于某个区域,应该把资源有效整合,建立跨区域的生态旅游产业机制。
篇2
“反者,道之动”,向着相反的方向运动是道的运动规律。“道”的真理同样也适合生命的过程,“还者,生之动”,还原过程是焕发生命活动和保持生机的规律。综观古今中外的各种养生术,其目的都是为了减缓生命的氧化过程,增强生命的还原过程,使生命得以延续和发展。
众所周知,生命体是一个系统。任何系统的内部组织都有一定的秩序,这就是系统的有序性。系统的有序性越高,表示这个系统功能越健全;反之,有序性越低,则表示这个系统功能越衰退。任何系统的基本功能是维持、提高自己的有序性。生命体是自然造化之物,其有序性的保持有赖于所使用的自然之物的有序性。
所以,越是接近自然越是原生的东西,就越能增强人体的还原过程,越能消除自由基对机体的破坏。比如茶中含有一种能大量消除自由基的成分,所以适度饮茶对健康大有益处;蔬菜、瓜果也有类似的成分,适度的素食能够使人神清气爽,心情舒适。而日常所说的“垃圾食品”,主要都是些氧化食物,如油炸类、方便面、汉堡包等。这些食物能在人体内发生氧化反应,损害脑血管壁的正常分子结构,不仅有损健康,而且容易导致思维迟钝。
原者,欲之度
还原生活,需要我们张弛有度,进退自如。既要满足自己合理的欲求,也要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抑制,对欲望之“度”进行合理地把握,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下面,以食欲为例,展示还原生命之张弛。
“欲要长生,腹中常清;欲要不死,肠中无滓”。细胞本身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不断地产生代谢废物(即毒素),这些代谢废物通过具有排泄功能的肾、肠胃、皮肤、肺等排出体外。加之,在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普遍大量进米白面、肉类以及饼干点心等加工食品,导致食物纤维缺乏以及体内酸碱失衡,使肠中废物积聚,从而产生腐败细菌形成有害物质,引起自身慢性中毒,加重了疾病的发生与衰老加速。
在进食尤其是终日饱食的情形下,要完全彻底地清除体内毒素和废物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世界各国都曾兴起过断食疗法,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断食,充分调动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从而将大量的宿便排出体外,因此能够比较彻底地恢复健康。当在断食的情形下,不仅肠胃得到休息,也带动了全身所有器官的休息。人体能够集中大量的能量来发挥自身的自净作用和排泄作用,最大限度地分解和排出体内积蓄的有害物质,从而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另外,断食本身就是对细胞的一种刺激,它可刺激细胞恢复正常代谢,从而提高细胞的活力。
众所周知,许多动物在生病时都会自动地停止进食,以减轻肌体的负担,然后发挥肌体的自愈力以恢复健康。对人而言,在身体不适时也会有食欲不振的现象,这其实如同发烧一样是人体的一种生物保护反应。人体就好像机器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彻底地停工大修一次。有些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在不思饮食时勉强自己进食,实际上是反过来延缓了身体的恢复过程。所以,最近一些年来,在西方国家也曾一度流行每周周末断食一两日,或其间只进行极少量饮食如苹果、蜂蜜、牛奶等等,以让肌体获得彻底的休息。其实,自古以来,在各大宗教中都对断食有所提倡,比如最著名的就是伊斯兰教每年都有一次斋月的传统。还原,生命在于平衡
“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本意在于强调变革发展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后来却广泛用在体育、医疗、养生等方面。这符合一般人的常识,运动促进新陈代谢,给人以活力,长期坚持运动的人似乎比一般少运动的人要健康一些。尤其,当下肥胖者越来越多,这些人中很多是以车代步,缺乏运动锻炼,使得人们对“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更是坚信不疑。
但是,任何运动,虽然对增进肌体的活力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同时又造成大量的能量消耗。所以,过量的运动反对肌体造成损害,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员退役之后伤病缠身,身体状况并不好,不能成为长寿的群体的原因。于是乎,养生学方面又提出另一种观点——“生命在于静止”。
篇3
1、食物能量:它是人类最基础、最原始的价值形态,因而被定义为“标准的有序化能量”,其它所有的价值形态都以它为参照系和基本尺度进行统一度量,食物的使用价值量等于它所等价的标准食物中所含有的生物化学能量。
2、温饱类价值(包含食物能量):它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机体的能量代谢,节约体能,减少体热散失,在数值上等于它所节约的标准的食物能量。
3、安全与健康类价值:在一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生理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生理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个人的实际劳动潜能,这是由于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任何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因为内部的健康原因和外部的安全原因而丧失其劳动能力,即个人所积累的生理化劳动潜能总会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安全与健康类价值主要通过提高机体的自然有效生命,降低机体的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自然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能量代谢率×效用时间。
4、人尊与自尊类价值: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下,并不是所有的个体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能力,这是由于任何个人都会因为某种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劳动岗位并不能完全与其劳动能力相匹配,或者找不到可以释放劳动能力的劳动岗位,从而造成部分个体化劳动潜能的失效和浪费,即个人所积累的个体化劳动潜能总会因劳动岗位的不匹配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因此人尊与自尊类价值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社会有效生命,降低人的社会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社会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温饱类与安全与健康类价值的消费率×效用时间。
5、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在一般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化劳动潜能都能最终转化为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有用的劳动能力,真正用于人类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这是由于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各种社会性弊病,如、思想僵化、分配不公等,这些社会性弊病必然引导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投入不合理的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造成流失与浪费,即社会总会因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其部分社会化劳动潜能不符合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真正需要或理想需要,而存在一定大小的失效率,这种失效率称为“理想失效率”。因此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类价值主要是通过提高人的理性有效生命,降低人的理性生命失效率,来提高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价值的有效性,其价值量在数值上等于:理性生命失效率的改变量×温饱类、安全与健康类、人尊与自尊类价值的消费率×效用时间。
二、生产资料使用价值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为了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高等的耗散结构(即人类)通过改造环境中的某些事物,使其功能特性发生变化,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组织的生理功能。例如,衣服可以用来御寒,以替代和加强机体上皮毛的保温防护功能;劳动工具可以用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某些运动组织或思维组织的劳动功能;人们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取长补短,使原有的劳动能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这些外部事物与机体各细胞组织之间不存在任何生理性质上的联系,不参与机体的能量代谢过程,因而在本质上区别于机体的细胞组织,不属于耗散结构的范畴,但是它们可以依附于一定的耗散结构,并在耗散结构的作用下完成一定的功能服务,来替代、放大、加强、增补机体某些组织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而且这些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与耗散结构的细胞组织一样,也需要不断地与外界进行必要的能量交换、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换,在许多方面具有与一般耗散结构相似的特性,是人类本体的延伸,因而称之为“扩展耗散结构”,而人类自身就是“本体耗散结构”。显然,人类建立和发展“扩展耗散结构”的根本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就是人类用以构筑扩展耗散结构的基本材料,其目的在于提高生活资料的功能价值或降低生活资料的耗散价值(使用价值=功能价值-耗散价值),即增长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量,因此它的使用价值大小通过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来体现。也就是说,所有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它本身不会产生增值,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以折旧的形式逐渐地、分批地将其使用价值等量转移到生产系统的产品之中。生产系统的产品可能是生产资料,也可能是生活资料,由于任何生产系统的最终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地生产更多更好的生活资料,因此任何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最终都会转移到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中,从而可以折算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
三、劳动价值与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人在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即不断地付出劳动价值。由于劳动力的形成和恢复只需要通过足够多、充分丰富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消费来完成,劳动力的直接耗费实际上就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的间接耗费,因此人的劳动价值的付出量实际上可以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消费量”来衡量。
政治经济学把“劳动价值”概念抽象化、神秘化了,把它与使用价值对立起来,提出具有“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劳动价值”的观点。事实上,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是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劳动价值是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它是由生活资料使用价值转化而来,又服务于使用价值的增值。人类的机体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价值投入产出系统,投入使用价值(以生活资料的形式),产出劳动价值(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具体过程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是生活资料使用价值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人的劳动潜能;二是劳动潜能在“劳动过程”中释放出来并转化为劳动价值;三是劳动价值又在“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使用价值在信息的驱动下产生相干作用和协调作用(注意,劳动过程通常与生产过程同时进行),并与之一起等量转移到产品之中,同时产生一定的价值增值,也凝聚于产品之中。理论证明,劳动价值可采用“社会必要补偿性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来进行度量,且劳动价值与劳动强度、劳动复杂度、劳动熟练度等变量之间存在特定的函数关系(详见拙著《统一价值论》)。
四、各类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价值增值的内在机理
人在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一方面能够不断地生产出(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会不断地付出代价,这个代价既包括生产资料自身使用价值的不断丧失,还包括劳动力的不断耗费(即劳动价值的不断付出)。在没有信息参与作用的情况下(既没有正信息的参与作用,也没有负信息的参与作用),生产系统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总量与所投入的使用价值与劳动价值总量是完成相等的,即产品的使用价值总量等于投入的生产资料使用价值总量与劳动力所付出的劳动价值总量之和,从而不产生任何的价值增值,此时,生产系统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而要想使生产系统的价值总量产生增值,就必须向该生产系统输入信息。
笔者在拙文“对耗散结构论进行重大改造”中指出,信息的基本特征是消除不确定性或提高有序性,然而,系统的有序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结构有序性,二是功能有序性。任何耗散结构的有序性应该是指其功能上的有序性,而不是指其结构上的有序性,人类获取和运用信息的客观目的不是为了抽象意义地消除其结构上的不确定性,而在于实实在在地增强自己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即增强其功能上的有序性,信息的本质应该从它的功能特性去理解和定义,而不能从它的结构特性去理解和定义。由于耗散结构的功能有序性实际上就是价值性,因此信息的本质特性就是改变耗散结构的价值率,即“一切能够改变事物价值率的内外因素称为信息”。根据信息的定义,自然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信息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信息的原始积累来源于生物进化,虽然这一过程非常缓慢和微弱,但它形成了价值的原始基础,构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生物之所以不断进化,关键在于生物信息的不断积累;人类社会之所以高速发展,关键在于信息和知识的高速积累。对于人类来说,其机体的进化过程主要是通过劳动来带动的,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也都是通过劳动创造的;劳动促进了手与脚的分工,使人学会了使用工具;劳动促进了语言的产生,形成和加速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劳动之所以被确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并不是因为抽象意义上的定义,而是因为劳动在信息(包括人类机体的生物信息)的形成、传播、处理和运行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此时,“信息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唯一源泉”。
由于人在劳动过程中通常总会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携带一些新信息(注意:常识不是信息,不会产生价值增值)参与各生产要素的相互作用,因此生产系统通常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价值增值,这些新信息可能来源于基础教育时期的书本知识与社会见闻,也可能来源于生产过程中自身的经验积累、技术熟练与思维悟性,还可能来源于他人的技术传授与前人的经验教训。人类劳动由于含有创造性成份,能够自发地、积极地积累、吸收和运用信息,因此是构成价值增值的根本性动力。当然,人在生活资料的消费过程中,由于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积累、吸收和运用有关新的消费信息,也会使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产生价值增值;人在接受基础教育或技术培训的过程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积累、吸收和运用有关新的知识信息,也会使原来的常识性知识体系的使用价值产生价值增值。因此,价值增值现象不仅只发生在生产领域,也会发生在消费领域;不仅只发生在制造性的生产领域,也会发生在流通性的生产领域;不仅只发生在经济领域,也会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
篇4
关键词:思维方式;系统论;黄帝内经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7-03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DING Bao-gang, MENG Qing-g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Systematic thinking is a thinking style that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heory. Although system theory is originated in modern west society, its ideology had existed in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nd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theory's four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e holism principle, relativity principle, dynamic principle and orderliness principle. Then it shows that the ancients applied systematic thinking to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ccomplished lots achievements.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thinking style of the ancients in studying TCM and give some inspiration to thinking style in TCM study.省略。
思维方式是人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事物、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是该历史时期人们相对稳定的思维格局或思维定势,影响和导引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1]。系统思维主要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而系统论作为一种研究系统特性和规律的科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社会,但其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并且早已被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农业、军事、政治、医学等。中医学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采用了具有系统论思想的思维方式。基于此,自古至今中医学的理论处处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明确提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思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1980年给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的一封信中提到:“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2]。纵观历代中医著作,系统思维犹如一树奇葩,早已贯穿于中医发展的始终。
1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系统论作为系统思维的理论模式,其基本原理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和有序性原理。分而言之,其主要内涵可简单概括为:①整体性原理指的是系统的整体属性不是各部分属性的简单加和,而是大于各部分属性之和,并且具有各部分所不具备的某些属性,这是系统内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②联系性原理主要是指系统内部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性,它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内在原因;③动态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趋向并保持在特定的目标值上,揭示了开放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走向并保持一种稳定目标的特性规律;④有序性原理指出有序化是系统自组织和进化的内在本质[3],体现了开放系统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进而保持和恢复平衡状态的特性。系统论的这4条原理各有特点,又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2 系统思维在中医研究中的体现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在利用中医为人们解除病痛折磨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又一部辉煌的著作。这些传世经典,不仅凝聚着他们一生行医中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渗透着他们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推本溯源,《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理论奠基之作,是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必读之书,书中不仅汇聚着《内经》以前古人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亦是《内经》之后医者研究中医的理论源泉和思维方式之典范,故研究《内经》,可窥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
2.1 研究对象 古人研究生命规律,除了研究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的内在变化规律外,还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而且“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看成自然变化的产物,认为外界的一切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影响,故同时还研究与人体息息相关的环境、时间等的变化,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气候变化、节气变更等等。因此纵观《内经》全文,可以看出古人把研究对象定格为一个内有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相互作用,外有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时间推移等相互影响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复杂生命系统,而研究这样的一个复杂系统,必须要有相应的思维方式来支撑,而系统思维就是其中之一。
2.2 研究内容 《内经》包含的内容涉及哲学、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等多学科知识,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而这些复杂的内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庞大系统。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运用了系统思维,对人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与联系性: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联系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而发挥出各部分不具有的整体功能,比如在生理状态下,五脏系统中的心系统是由心脏、经脉、气血津液等的有机组合及其他脏腑的配合才发挥出其主血脉和主神志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部分所不具有的;二是人体是形神的统一体,形与神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人是形神的统一体,有形无神或有神无形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病理状态下,神的变化可影响形体的状态和功能,如《素问・疏五过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以及《素问・举痛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飧泄,故气上矣。”分别讲了神志的异常变化可以消耗精气,损伤形体或使气机逆乱;同样形体的变化也可影响神的状态,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指出气血是神的物质基础。《素问・调经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说明气血的充足与否会产生不同的情志变化趋向。而人体的这种整体性离不开联系性的作用,同样联系性也离不开整体性的配合,故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挥出各自相应的功能和系统的整体功能。
(2)人与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与其他万物一起共同构成大自然这个整体。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包括时间和空间),必然会影响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人类的状态。在构成大自然的各个要素中,对人的生存具有最直接影响的是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由于人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因而人体自身状态的发展势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这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天人相应”。人体运行自身这个小系统同时,又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描述了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人们不同的体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多发病和治疗方法,说明自然环境对人体的生理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又是社会中的人,故人又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整体,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发展的各种状况紧密相连。社会的安定与动乱、富裕与贫穷等状况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都会对人体造成影响,比如《素问・疏五过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就讲了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的地位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这就要求中医大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在诊治疾病时,应该本着整体和联系的观点“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3)人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性:大自然的昼夜更替和四季轮回,产生了万物的寤寐与生长化收藏。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其生理和病理状态亦必受此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由盛转衰的变化趋势和随着昼夜四季的更替而呈现盛衰的交替变化两方面。首先,人体会随自身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由盛转衰的生理状态,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了男子从八岁到八八,女子从七岁到七七,精气的盛衰变化及其对人生殖功能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指出了人在四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衰老状况。其次,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还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大到一年四季,小到一日的每个时辰,人体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了四季变化的特点及人们养生方式的变化,旨在使人体顺应四时变化而调节身心,以达到健身防病的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盛,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讲了一日之中阳气的盛衰变化与昼夜晨昏的变化相应,人体的生理状态亦随之而变,反之则会产生疾病。《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则讲了在疾病状态下,随着一日之中阳气的不同盛衰变化,出现了正邪之间的胜负变化,故人体的状态亦随之而变。由上可见,人体每一时刻的状态都有变化,都在随着昼夜更替、四季轮回及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同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体现了人体状态的动态变化性。
(4)人体状态的有序性:大自然的阴阳晦明和五运六气等的变化,使得整个大自然处于一种有序状态,而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其生理状态势必亦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体处于一种与大自然同频共振的有序状态。如《灵枢・口问》:“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讲了人随昼夜更替而处于睡眠与清醒的有序状态;《素问・六微旨大论》:“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亢则害,承乃制。”人与自然相应,运气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体的状态,使人体与自然一样皆有生有克,这样方能保持人体功能活动的最佳状态。另外,人体状态的有序性还受自身系统的调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体先天具有维持有序性的机制,主要表现在通过阴阳的对立制约和五行的生克制化来维持人体各种功能的动态有序性。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指出了阴阳之间的互根互用关系,并以此来维持人体的平衡状态,同时在该篇中也指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指出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人体的五脏、五体、五志等皆与之相应,并依此维系人体脏腑、情志等的平衡性;二是通过各种后天的调节方法,或自身精神的调节,或外界药物等的干涉,调动人体的自愈机制,使人体保持健康有序状态或使之从疾病状态向健康状态转化,即从无序到有序,从阴阳失调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转变,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及《灵枢・本藏》:“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都说明保持精神的安静与调和,可以使人体正气充足、脏腑安宁,从而保持一种阴平阳秘的有序状态;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指出在疾病状态下,可根据疾病不同的发病阶段和部位,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使人体恢复健康有序状态。因此,人体无论是随自然变化的自动调节,还是借助于后天各种方法的配合调节,都揭示了人体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趋于有序性的特性。
3 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由上分析可见,《内经》从把研究对象设定为人体这一复杂生命系统,到对具体的内在变化及其与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生命规律的描述,都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反映了古人早已运用系统思维来研究中医,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说明系统思维适合中医自身发展的需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曾说:“生命是宏观的,但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4]。指出了微观层次的规律不适合宏观现象的研究,而中医则偏重于对宏观现象的研究,故研究中医须用宏观层次的规律,而系统思维就属于思维方式上的宏观层次。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说过:“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5]。指出了在中西医的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而系统思维就是在思维层面上研究中医的道路。因此,无论是古人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中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近现代著名专家、学者的远见卓识,都证实了系统思维在研究中医中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东海,林少健,李勇.从东西方文化差异谈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7,15(6):417-418.
[2] 吕炳奎.对当前中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1(4):1.
篇5
一、世界之在:本然世界与现实世界
在庄子那里,世界之在有两重内涵,其一为本然世界,其二为现实世界。由现实世界出发,向前追溯,直至世界的原初存在形态:“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庄子?齐物论》)“始”即开始,是宇宙在时间上的开端。由“始”这一开端向前追溯,达到的是未曾开始的开始,再向前追溯,则至于未曾开始那未曾开始的开始,即达到了“天地之始以前之再前”[1]72。换言之,由现实世界之时间上的开端向前追溯,最终达到的则是存在之无始或无开端,而这种无始其“本体论意义是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它意味着存在的终极形态或本然形态无时间上的先后之‘分’”[2],也就是说,存在的这种无始扬弃了时间上的先后特征,从而在实质上亦消解了时间之维。同样,现实世界纷杂、多样的现象呈现出“有”、“无”的分别,由之出发,向前追溯,达到的是“有”、“无”都不存在的形态,再向前追溯,最终所达到的是超越“有”、“无”之分的“无”。现实世界之“有”、“无”是具体的形态之存在或消失,因而具有空间特征;与之相对,源始意义上的“无”扬弃了具体对象的“有”、“无”之分,从而在实质上消解了空间性。在现实世界中,时间维度上的先后之分、空间维度上的具体对象的有无,都是分、别的体现;与之相对,向前追溯所达到的世界的原初之在超越分、别,消解时间、空间,呈现的是世界的本原或初始的形态。唯其无分、别,所以世界的原初之在作为本然的存在表现为玄同的世界。[3]
显然,庄子的以上分析立足于分化的现实世界,通过逻辑的推论,从现实世界直至浑而无分的原初之在。原初之在之原初性,说明其已然的性质,而对庄子而言,现实世界之既成性、现实性,赋予其实然的特征,构成庄子不能不面对、不能不生活于其间的存在形态。当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的世界时,多样的形态便得以展现:“万物殊理”、“四时殊气……五官殊职。”(《庄子?则阳》)“万物”确认了物的多样性,“殊理”则彰显了物之为自身的特殊性;“四时”之“殊气”、“五官”之“殊职”则从自然到社会均确认了多样性、差异性。
然而,就分化的现实世界而言,在多样的形态背后,实质上仍然以“通”为其内在特征。
首先,这表现在庄子对“气”的理解上。“气”在庄子那里,对应的是分化的现实世界,并只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杂乎芒芴之间”与“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泰初”一样,是对世界原初形态浑然一体的表述。“变而有气”表明“气”产生于原初之在。就形而上的层面来看,“气”具有质料的性质,从而赋予“气”以“有”的特征,即获得了某种具体的规定。在有“气”的基础上,由气作为质料,物之“形”才得以产生,由此衍生出天下万物。因而,就“气”之产生意味着“有”之产生而言,“气”展示了其与原初之在的疏离,并确证其与分化的世界之在的关联。尽管“气”是“有”的一种形态,但“气”与万物之“有”却不相同,作为万物形成的基础与质料,“气”具有“一”之特征:“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天下万物,不管是“神奇”所表征的具有正面意义的事物,还是“臭腐”所指涉的具有负面价值的事物,均由“气”构成。而“通天下一气”既确认了“气”在质料的层面构成万物,又确认了“气”之“一”,就此而言,可以说万物“一”:“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庄子?田子方》)与此相关,“气”之“一”既蕴含着自身之通,又赋予万物以通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万物在质料的层面通,另一方面又使得具体世界中不同的存在形态之间在彼此能够相互转换的意义上通。相对于世界的原初形态,分化的现实世界最先具有的“有”即是“气”,并进一步展现为具有多样存在形态的万物,但“气”之“一”、“通”使得多样的事物在呈现各自独特性的同时,彼此之间又并非隔绝和分离,而呈现出通之维。对于庄子的“气”,刘笑敢曾说:“庄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一气”,“气是万物存在变化的基础,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元素”,“但是气远不如道重要”,“庄子自身的逻辑应该是气由道生,道为气本。”[4]136同时,他分析了庄子在其哲学体系中引入“气”这一概念的原因:“首先,在无为无形的道产生具体有形的万物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过渡状态。其次,庄子是强调齐万物而为一的,在物质世界之内需要一个体现万物共同基础的东西。最后,庄子是强调事物的相互转化的,需要一个能够贯穿于一切运动变化过程之中的概念。适合这些需要的概念必须是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可以运动也可以凝聚、可以上达于道也可以下通于物的,这样的概念只有气。”[4]137
其次,庄子对道的规定亦展示了现实世界之通。在庄子看来,道构成了世界之在的根据,并内在于不同的存在形态之中。就世界的原初之在而言,其表现为浑而未分的原始统一,这种存在形态可以看作是“道未始有封”(《庄子?齐物论》)的呈现。“封”即界限,“未始有封”表明道没有分际、界限,以统一性为自身的内在品格。刘笑敢指出:“‘道未始有封’即说明道是外无界限、内无差别的,因而道是绝对的同一。‘道无封’的特性是庄子预设的齐万物而为一的客观依据。”[4]113“未始有封”之道作为世界原初存在的形上根据,在此,道之通主要呈现的是其未分化性、无界限性、统一性。
在分化的现实世界之中,道“无所不在”:“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庄子?天道》)万物之形态各异、大小不同,但道普遍地存在于一切物之中。庄子与东郭子关于道之在的对话清晰地展示出这一点:“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庄子?知北游》)不管是蝼蚁、?稗、瓦甓这些价值形态较低之物,还是屎溺般具有负面意义的事物,道都内在于其中,“无所不在”体现的就是道的这种普遍性。而在“万物殊理,道不私”(《庄子?则阳》)中,“殊理”是使物在本质上成为其自身的形式规定,从而将物与他物区分开来,“万物殊理”表明不同之物具有不同的规定,而与之相对,道之“不私”意味着道超越具体事物之异而具有普遍性。因而,作为存在原理的道,在分化的现实之在中,其通主要呈现的是普遍性。但是,道对于万物之“无所不在”并不意味着道之分化,道之普遍性背后隐藏的是其统一性:分化的世界中,道仍以统一性为自身的内在品格,并呈现于一切对象之中,使得每一物均有自身的存在根据、本原。于连指出:“世界的多样性,从小草到大檩,从丑女到西施,以及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可’,但是,‘理虽万殊而性同得’,所以‘道通为一也’。因此,‘道通为一’远没有导致万物的趋同和贫乏……这种统一……是贯穿性的统一,同时也是过程性的统一。”[5]
因而,从形而上的层面来说,作为存在本原、根据的道既具有无限唯一性,又具有无限包容性;既超越于万物之外,又内在于万物之中;既在原初之在中,又在现实之在中,它同时跨越世界之在的这两种图景而伫立于其间:道以其统一性、普遍性赋予世界原初之在与分化的现实世界以通的特征,又成为两种世界之在的形态具有连续性的形上依据。
二、人之在:人与万物为一
世界的原初之在分化为具体的世界,万物得以产生,在这一分化的过程中,作为万物之一的人亦获得了存在性:“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庄子?知北游》)就“气”作为万物形成的质料而言,人作为万物中之一物,无疑以“气”为构成人自身的基础,庄子用“气”之聚、散解释人之生、死,即突出了这一点。同时,“德”作为道在具体事物之中的体现,亦呈现于人,并表现为人之为自身而异于他物、他人的本质规定:“物得以生谓之德”(《庄子?天地》)之“物”即包含人在其中。就此而言,人与天地间之万物通而为一:“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地”作为世界的具体的呈现形态,是原初之在分化后的产物,而“我”作为类之人,其产生一如“天”“地”之生成,是世界原初之在之分化,由“气”构成。对应于世界之在之分化过程,可以说,“天地”与我“并生”,而推广开去,亦可说,具体世界中的一切存在形态均与我并生。然而,与我并生之万物的呈现形态各异、大小有别,如秋毫通常意义上意味着“小”、泰山则代表着“大”;人之生命亦长短有别,如殇子之短命而“夭”、彭祖之长“寿”。但是,在庄子看来,大小、寿夭等具体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区分、差异,并不构成包括人在内的万物之间的绝对界限,在天下万物都“一”于气、内含“道”的意义上,可以说,万物通而为一,进而言之,人亦与万物“为一”。
人与万物为一,同时内蕴着人与人通而为一的维度:首先,就作为类的人来说,从人之获得生命为气之聚、生命结束为气之散来看,人之生死呈现为气的聚散。唯其统一于气,因而人之生、人之死这两种不同形态之间具有了能够相互转化的根据,从而表现出生死相通。
其次,就个体来说,不论是如殇子般短命,还是如彭祖般长寿,不同之人均需经历从生命开始至生命结束的整个历程,不管该历程是长是短,从过程及最终的指向来看,人与人之间在由生走向死这一点上是相通的。这在如下论述中得到了体现:“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至乐》)庄子在其妻死后,对人之生命存在向前追溯,直至无形、无气、浑而未分的世界原初存在形态,展示人作为万物之一,其生与万物一样,产生于原初之在的分化:“杂乎芒芴之间”即是对世界原初之在浑然一体的表述,亦即“无气”的原始之通,而由无气至有气,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世界,再至“有形”,“形”在此指人之形所表征的人之生命存在的获得,接下来,由生至死,即人之生命的终结,人之生伴随着世界之在的分化,并如同春秋冬夏四季的交替,这使得人之生、死成为世界之在演化过程中相继的两个环节。因而,对于作为个体的人来说,其生、死相通。由此,人之由生到死既表现出自然性,又具有必然性:人之死意味着人之生命存在的终结,而由生至死的过程是不可逆的。
就人与万物的关系来说,人之死虽意味着个人生命的不复存在,但他又是万物中之其他物形成自身的质料:“子来……将死……子犁往问之……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庄子?大宗师》)“以汝为鼠肝”、“以汝为虫臂”十分形象地表明子来死后,可以作为“鼠”、“虫”等自然之物的构成。在这里,庄子将人的生命置于世界之在的链条之中,使得“生”“死”同时融于万物之中:“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庄子?田子方》)就天下万物来说,作为“气”的不同形态,生、死如同昼夜的更替,表现为一个循环的过程。毋宁说,作为个体的人之由生走向死的背景、前提是天下万物之生、死的相继、循环。
再者,就个体来说,存在形态不同、精神境界不同的人,均由气构成,从质料的层面来看,人与人通;从人人体现道、人人具有“德”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亦通。
事实上,人与万物的合一,在本体论上体现着世界之在的普遍相关:不管是人与万物通而为一,还是人与人之间相通,都肯定并确证着这一点。陈鼓应曾作了如下论述:“从哲学观点来看,庄子是从同质的概念去看待人与外物的关系的。……就是说,人与天地万物的原质是相同的。因而从同质的概念出发,庄子认为人与外物、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隔离的,而是一体的、合一的。”[6]
人与万物之通还体现在价值论的层面。价值,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如果没有人之在,价值之维亦不会存在。就价值论来看,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突出地体现在社会领域。庄子区分了社会领域的不同存在形态: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就至德之世来说,其特点是人与万物合而未分,因而,庄子把它作为理想的存在形态,以“至德之世”来表述即是对其理想性的肯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马蹄》)李勉说:“‘填填’、‘颠颠’押韵,同一意义,当时口头语也,自在而得意之词。言民之真性。”[1]247在此,用“填填”、“颠颠”形容人之“行”、“视”表明人的存在方式同于自然。而“蹊隧”、“舟梁”是人化之物,“山无蹊隧,泽无舟梁”则表现了外部世界完全停留在本然之在的状态。在这一本然之在中,人、禽兽、草木等万物都呈现出自在的形态。因而,在这种存在形态中,万物虽然已分化而出,作为类的人虽然亦生活于其间,但人与禽兽、草木等各自呈现出自在的存在形态。从整体来看,整个外部世界表现出的是未经人的任何变革的原初状态。显然,在这一原初状态中,人与万物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分化的存在,但在实质上,人与万物却以合而为一为其特征,这显然是“未始有封”的世界原初存在形态在社会领域中的显现。同时,在至德之世中,不仅人与自然之物合而未分,人与人之间也以无分为特征:“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庄子?马蹄》)无君子、小人之分即显示了人与人之间通而为一。以人与万物合一为特征的至德之世作为理想之世,内含着应然的规定:应当达到的理想形态。同时,它又是前概念的存在形态:“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羲)氏、神农氏……若此之时,则至治已。”(《庄子??箧》)“昔者”展示出以人的视角对历史的回溯,“至治”表明庄子对这种前概念形态的态度及评价。在此,对历史的回溯和评价赋予至德之世以理想性,又使得其与前概念形态合而为一,二者无疑都以未分化为特征。
然而,由人与万物合而未分的淳朴之世,走向“世与道交相丧”(《庄子?缮性》)的动乱之世,社会由“至治”而趋于“乱”。庄子认为这一历史演进的根源在于分、别,“礼乐遍行,则天下乱矣”(《庄子?缮性》)。礼、乐即以分、别为特征。“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庄子?天运》)“治天下”亦以人与天下万物之分为前提,表现为人对天下万物的作用过程。因而,以分为前提的“治天下”,只能是以“治”为名,而实质上却是“乱莫甚焉”。同时,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亦具有负面的意义和否定的价值:其既以分为前提和内涵,又具有外在于人的特征。与庄子一致,马丁?布伯亦看到了这一点:“社会制度乃是‘外在的’,人于其间追逐种种目标……社会制度……是无灵魂的泥偶……不知人为何物……不能接近真实人生。”[7]37-38
可以看到,由至德之世的人与万物合而未分,走向动乱之世的分而别之,庄子立足于动乱之世而对上古以来历史演进过程的回顾,既是对动乱之世的现实性的表明,又把着重点落在对人与万物合而未分的理想存在形态上。就此而言,庄子在社会领域区分至德之世、动乱之世,其旨在突出人之在应与万物通而为一,这既在价值观上体现了人之在应当以通为其品格,又以形而上领域未始有封的本然之在为其根据。
三、存在之序
庄子以道为世界之在的本原、根据,既展示了存在之通,又内蕴着存在之序。“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庄子?天道》)即确认了道所蕴含的秩序之维。存在之通展示的是对统一性的关注,而存在之序则隐含着对条理性、有序性的要求。因而,庄子之道既展开为统一性原理,又表现为秩序原理。与存在之通一致,存在之序亦呈现于世界之在的两重形态当中。
就世界的原初存在而言,其由于未分化而展示出原始的统一性,同时,亦呈现出秩序之维:不论是与“未始有物”相联系的浑然一体,还是与“未始有封”相关的浑然无分,作为原始的混沌,其中所蕴含的统一性都使得它们与纷杂、无序无关,而内含着自身之序。但是,原初之在本身的秩序只呈现为有序,并具有隐含的性质,从而区别于分化的现实之在的秩序性。在具体世界中,其秩序性既呈现为有序性,又表现为条理性,并展开于自然领域与社会领域。
就自然的层面而言,庄子以分化的现实世界为基础,对“道”所蕴含的秩序之维进行了分析。“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尤,尤而不救。”(《庄子?人间世》)原初之在分化而为具体世界,便呈现为具有区分、差异的多样的形态。然而,当物与物之间的分际被过度强化时,世界之在便呈现为“杂”的形态,由之而来的则是“多”,这一意义上的“多”所体现的不是多样性,而是与纷杂、杂乱相联系的无序。就分化的现实世界来看,道作为存在的根据,其统一性、普遍性统摄着具有区分、差异的多样存在形态,赋予多样化的万物以内在的秩序。因而,“道不欲杂”既是“道”以其统一性对“杂”所体现的杂乱的否定,从而表现为对无序性的扬弃,又彰显出“道”所肯定的条理性、有序性。后者首先体现在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中:“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肃肃”即寒冷,“赫赫”即炎热,“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表明阴、阳是两种彼此不同且彼此对立的力量。[8]从万物的生成、演化来看,阴阳二者交互作用所体现出来的“和”,真实存在并使天地万物得以“生”。同时,这种“和”内在地蕴含着秩序之维,正是这种内在的秩序,使得万物之死生盛衰呈现出自身的法则,从而有规律可依、有理可循。因而,天地万物之生、之化,都非杂乱而无序,而是内含着秩序性。
在万物既生之后,天下万物与道的关系使得存在之序与存在的本原的关系得以揭示:“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作为“本根”之道,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本原、根据,而且内在地规定着天下万物运行的方式。在万物变化、运行过程中,正是内在之道,使得阴阳四时的运行呈现出有序性,使万物的变化展示出秩序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四时之“明法”、万物之“成理”都体现了存在的秩序性,而天地之“大美”在“美”的背后隐含着的是天地之间的有序,因为纷杂形态的天地万物呈现的是“乱”,而非“美”。
但是,分化的世界所具有的存在之序完全自然而然,从而不同于目的性的安排。每一物均具有自身特定的时空位置、因果网络,并“各居其位,各循其途,各具其可测度性及特定本性”[7]26。这在庄子“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齐物论》)的论述中得以体现。宽泛而言,分化的世界中天地万物、阴阳四时所具有的秩序并没有“怒者”使之然,其有序性、条理性完全取决于自身,自然而然,不假外求。
就社会领域来说,庄子确认了不同的存在形态:至德之世与动乱之世。在至德之世中,世界虽已分化为多样形态的万物,但万物之间却“未始有封”。与对自然层面的本然世界所隐含的秩序性的确认相同,庄子也确认了至德之世体现的是最完善的社会之序(“至治”)。与之相对的,则是非至德之世中社会的失序。从远古时期人与万物相融、人与人和谐到充满冲突、争战的动乱之世,庄子认为在“至德之隆”的“神农之世”之后,则是所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的非至德之世。在非至德之世中,人与万物逐渐分离、人与人之间充满争斗,社会则趋于“乱”,“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展示的就是社会的无序。
但是,在庄子那里,就社会领域而言,其秩序性既体现于至德之世,又需在非至德之世中实现。因为至德之世具有的已然的特征,指向的是时间的过去之维,尽管它代表着“至治”的最完善的社会秩序,并作为理想的存在形态而指向未来的向度,但它终究不具有现实性。而非至德之世作为现实的存在形态,作为人不得不生存于其间、不得不面对的社会,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有序性,这从“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乱世不为苟存”(《庄子?让王》)中庄子将非至德之世区分为“治世”与“乱世”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非至德之世中的“治世”之“治”不同于至德之世的“至治”,前者只是呈现某种程度上的秩序性,而后者则是最完善的社会之序。但就二者均体现着社会的有序性来看,则又有着相关性。由于“治世”呈现出有序性,因而对人的存在具有积极意义,而“乱世”之冲突、争斗所呈现出的无序、失序,则往往会危及人的生命存在,因而呈现出否定意义。
同时,非至德之世之“乱”亦直接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庄子?齐物论》)当社会呈现无序、失序的状态时,相争、相斗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存在方式,反映在个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当中,心灵的紧张、不安随之产生。与之相应,个体的精神世界呈现的亦是相互对峙、彼此排斥的失序状态。
人的精神世界的分化、失序,不仅是社会政治形态之乱的反映,而且也是观念领域失序的体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在此,“天下大乱”主要指向的不是政治上的失序,而是观念领域的分化、无序,它集中体现在由执著于一偏之见而导致的观念、意见的纷乱即是非之争上。“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庄子?齐物论》)是、非的形成,及执著于是或非,是对具有统一性的道的分裂。与之相应,是非之争表现为不同立场、观点之间的相争、相斥,而“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庄子?齐物论》)则显示出是非之争所导致的精神世界的迷乱。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是非之争体现出具有不同观点的各方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执著与追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情感层面的好恶,如对其所“是”的显然喜之好之,对其所“非”的则怒之恶之。这种喜怒、好恶之情的“失位”即偏失或无序,则将进一步引发精神世界的不健全,从而最终导致人之本然之性的失落。
因而,要扬弃精神世界的紧张、冲突,实现精神的平和、有序,既要求在政治领域实现其“治”,又要超越是非之争,并且合理安顿自身的情感,以维护和挺立自身本然之性。在观念领域,庄子以齐是非来扬弃乱而无序的状态:“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对庄子来说,精神世界的有序性即为“和”,所谓“心莫若和”(《庄子?人间世》)便确认了“和”作为“心”的存在形态,代表了平和之境。这种平和的心境既蕴含着有序性,又以“一”为指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也就是说,个体只有保持、守护其精神世界的内在的统一性,才能使之达到心灵平和的有序状态。在此,精神世界的统一性所蕴含的“一”之维,与心灵的平和、宁静所体现的秩序性展开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庄子对存在之序的关注,与世界之在的两重形态相应,在自然层面上既赋予世界之原初存在以秩序性,又通过分而齐之赋予分化的现实世界以内在之序;在社会领域中,既肯定至德之世所蕴含的自发之序,又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非至德之世中呈现的有序形态,而“治世”之有序性则为人精神世界之平和、宁静提供了担保。因而,不管是自然层面的万物,还是社会领域中的人的存在,当它们以条理性、绵延性、有序性为其存在的方式时,多样的存在形态之间不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相通、相互关联的。就此而言,存在之序既使存在的分离性得以扬弃,又使自身与存在的统一性合而为一。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之在的终极本原,“道”在庄子那里既展开为统一性原理,又表现为秩序原理,二者分别从统一性、普遍性与条理性、有序性的维度使存在之通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因而,存在的图景及与之相关的存在之通,所展示的是存在本身,换言之,即存在是什么和怎样是。就世界之在而言,在世界的原初存在形态中,其浑而未分的性质使得通显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作为形上原理的道之未分化及统一性则是这种存在形态之通而为一的根据;分化的现实世界既在质料的层面以“气”作为万物通的根据,又在存在根据的层面以“道”之普遍性赋予存在以通的特征(2);世界的原初之在与分化的现实之在作为世界的两种存在形态具有连续性,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连续性亦可看作是通的体现。就人之在而言,作为分化的现实世界中的存在形态,人与万物的合一,则从人的角度展示着世界之在的通之维。同时,存在的秩序之维从有序性、条理性彰显出存在之通,并展示着其与存在的统一之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