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贸易数据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09 15:03:51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进口贸易数据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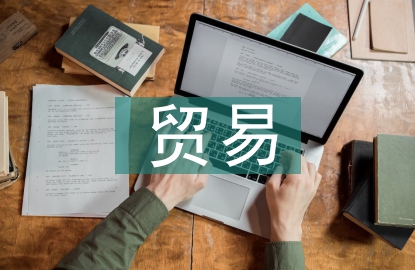
篇1
[关键词]劳动收入份额;进出口贸易结构;劳动者报酬
[DOI]10.13939/j.cnki.zgsc.2017.29.036
[作者简介]吕子夷,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金融学专业。
1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研究
1.1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研究
劳动收入份额是劳动者报酬(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通常用劳动者报酬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来计算,本文参考张吉超(2016)采用Gollin的第二种方法,计算出 2008 年以前个体经营者的劳动报酬和营业利润,并调整到与 2008 年以后相同的范围。
从图1中可以得出,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从1995年持续上升,在1999年达到峰值62.6%,但从2000年开始基本保持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8.5%下降到2011年的47.1%,2012年以后又有所回升,但仍普遍低于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13年上升至52.6%,2014年又下降。从总体上来看,1995—2014年间劳动收入份额呈波动下降的趋势。
1.2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研究
进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个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各种类别的进出口商品在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中的份额,它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水平和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文以出口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和进口工业制成品占进口商品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情况,数据均来源于《1997—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了出口战略导向,极大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1995—2014,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产品总额中地比例持续上升。2004年出口商品结构比(工业制成品:初级品)为13∶1,超过发达国家5∶1的水平,到2011年约为18∶1,工业制成品已经在出口商品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2]
另一方面,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总额所在比重1995—2002在80%~85%上下波动,从2002年开始持续下降,在2014年下降至67%。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在工业技术方面不断发展进步、企业技术改革步伐加快和产品质量提高,能生产更高品质的工业制成品以满足国内需要,因此对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需求下降,而生产初级产品需求相对增加。这也与出口商品的结构变化是一致的。详见图2。
2 实证分析
2.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1.1计量模型的设定
综合考虑已有研究对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本文将模型设置如下:
LSt=β0+β1 IMPTt+β2 EXPTt+β3 KTYt+β4FDIt+β5GDPt+β6TECHt+β7SIt+β8TIt++β9GOVINt+β10GONOUTt+εt
被解释变量为劳动收入份额(LS),解释变量为进口商品结构(IMPT)或出口商品结构(EXPT),控制变量包括资本-产出比(KTY)、外商直接投资额(FDI)、经济发展水平(GDP)、技术进步(TECH)、产业结构(SI和TI)、政府干预(GOVIN和GOVOUT),随机变量。
2.1.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
主要计算方法和数据在第三部分已经详细解释,不再赘述。
(2)控制变量:资本-产出比(KTY)
白重恩(2009)指出,引入资本—产出比(KTY),可以控制要素相对价格和要素投入。考虑到中国目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资本要素投人仍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选定10.96%为资本折旧率。参考江三良、李攀(2016)和单豪杰(2008)的数据,以实际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实际GDP计算出中国1995—2014资本—产出比。
(3)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额(FDI)
FDI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国内外研究都指出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但积极或消极并无定论,因此本文将此因素纳入,按照每年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的平均值将各年的进口、出口和FDI数值换算成人民币。
(4)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GDP)
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的显著的影响。本文使用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1997—2015中国统计年鉴。
(5)控制变量:技术进步(TFP)
索洛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产出增长率扣除了要素增长率之后的剩余部分,度量了生产技术的变化。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从符栋栋(2015)运用索洛残值法计算出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中,选取1995-2014数据作为本项指标的数据来源。
(6)控制变量:产业结构(SI和TI)
产业结构也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通常,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高,由于PI+SI+TI=1,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在实证分析时,分别引入PI、SI或PI、TI回归。根据理论以及已有的实证实证研究,预期PI、TI的系数为正,SI的系数为负。
(7)控制变量:政府干预(GOVIN、GOVOUT)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分别以财政收入(GOVIN)和财政支出(GOVOUT)占GDP的百分比衡量,数据均来自各自中国1997-2015年的统计年鉴。
2.2实证结果及分析
2.2.1实证结果
首先,考虑到时间序列模型的序列相关问题,本文对应被解释变量劳动收入份额(LS)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如图3所示。
单位根统计量ADF=-0.974002都大于显著性水平1%~10%的ADF临界值,所以接受原假设,该序列是非平稳的。
根据序列相关图图4,自相关(ACF)图基本呈指数递减,而偏自相关(PACF)图在1阶处截断,由非零相关系数衰减为小值波动的过程非常突然,所以偏自相关系数可以视为一阶截尾,由此考虑拟合模型为AR(1)。建立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如下结果,判断截距项(C)和AR(1)参数的t检验和P值都具有显著性。
根据图5的判断,建立包含不同自变量的回归模型,结果如下表所示。
2.2.2结果分析
回归模型1无控制变量,只检验了进出口商品结构(LNEXPT和LNIMPT)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模型拟合优度较好。在10%显著性水平下,出口结构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随着工业制成品在出口总额的比重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而进口商品结构正好相反,与之前的预期基本一致。
回归模型2加入了产业结构(SI)这一控制变量,模型拟合优度为89%,产业结构(SI)回归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下为负,第二产业比重的增加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也有着很大的负面效应,也符合本文预期。
回归模型3同时加入了资本产出比(KTY)和产业结构(SI),模型拟合优度提升,控制变量资本产出比(KTY)的回归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资本深化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
回归模型4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财政收入(GOVIN)和财政支出(GOVOUT)两个控制变量,模型拟合优度不变,进口商品结构(LNIMPT)不显著。财政收入(GOVIN)的回归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说明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对劳动份额有很大的负面效应;而财政支出(LNIMPT)的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也为负,与之前预期不同。
回归模型5在模型2基础上加入外商直接投资额(LNFDI)、技术进步(TFP)两个控制变量。前者回归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为正,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有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
回归模型6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前模型中显著的变量变得不显著,但此模型拟合优度为92%,比之前都有所提高,推断可能产生了多重共线性。
3 结论与建议
首先,出口商品结构的上升确实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这是由于近年来我国资源禀赋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资本高速积累导致资本深化加强。同时,劳动力供给则缓慢增长且速度慢于资本深化。要素禀赋的变化导致我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制成品在出口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越来越低,而工业制成品在进口中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国际贸易中的H-O理论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充裕要素所有者将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稀缺要素所有者会受损,因此我国资本份额上升而劳动份额下降。
其次,资本-产出比的提高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国内投资者热情高涨,加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加,导致我国投资金额一路高攀。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引起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获额的收益更高,导致劳动份额的减少。
再次,财政收入增长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获得的财政收入越高,会提高政府收入,并增加劳动者负担,对劳动者的报酬产生越强大的挤压作用,从而引起劳动份额减少。
最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越高,劳动收入份额越小。其产业增加值越多,会导致农业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低。而农业生产和服务业运行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如果这两个产业的产值增长缓慢,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就越低,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就越少。
通过实证与理论分析,本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有了清楚认识,同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为了尽可能避免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应积极开发新型劳动密集型产品,实现劳动密集产品升级,在未来国际化市场竞争中培育新的贸易增长点;政府应鼓励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加大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政策优惠和扶持力度。同时,应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落实结构性减税,减少财政收入以增强企业竞争力,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积极发挥税收优惠政策的收入调节作用与范围,加强保护劳动要素的收益。
参考文献:
[1]肖文,周明海.贸易模式转变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实证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40(5) .
[2]安立.出口商品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 2013.
[3] Edward E Learner.What´s the Use of Factor Content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nomics,2000(50):17-49.
[4]Paul R Krugman.Growing World Trade:Causes and Consequenses [J]. Brooking Paper on Economics Activity,1995(1):327-362.
[5]Paul R Krugman.Trade and Factor Pric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nomics, 2000 (50):51-71.
[6] Bentolina S,Saint-Paul G.Explaining Movements in Labor Share[J].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2003,3(1).
[7] Harrison A E.Has Globalization Eroded Labor´s Share?Some Cross-country Evidence [R]. Mpra Paper, UC Berkeley and NBER,2002.
[8]Slaughter M J.Globalization and Declining Union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Industrial Relations, 2007(46): 329-346.
[9]Guscina A.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on Labor´s Share in National Income[R].IMF Working Paper,2006:294.
[10]李坤望,冯冰.对外贸易与劳动收入占比: 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2(1).
[11]张杰,陈志远,周晓艳.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抑制效应研究——基于微观视角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7).
篇2
中图分类号:F22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2-0088-05
一、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贸易往来越来越多。不仅出口在迅猛增长,进口也是在逐年增加。2004年进口贸易总额5612亿美元,2006年7914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种类和进口来源国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海关进出口数据库》显示,2004年中国进口产品种类6994种,2006年7114种;2004年中国从2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2006年这一数量增加到216个国家和地区。从总量上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关系是持续稳定增长;从微观层面上看,公司是贸易关系的承载者,基于公司层面的考察,或许可以从更深层次揭示国际贸易关系。当我们将考察视角定位在公司层面上,即一个公司从某个国家进口某种产品被视为一个特定的贸易关系时,发现中国2000年有166万对进口贸易关系,2001年183万对,2002年199万对。表面上看,中国外贸公司似乎与各伙伴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是持续、稳定、长期的,在新的贸易关系产生的同时,旧有的贸易关系也在继续。但在作进一步分析后发现,情况完全相反,中国公司与各国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是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旧有的贸易关系不断结束,新的贸易关系不断产生。在2000年的166万对进口贸易关系中,只有68万对贸易关系持续到了2001年,大约60%的贸易关系没有持续到第二年。2002年,仅有38万对贸易关系(占22.8%)还存在。只有10万对贸易关系(占6%)持续时间超过7年。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贸易关系呢,他们又是如何影响的呢?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中,人们经常忽视了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问题。一些理论模型总是倾向于假定贸易模式是静态的和稳定的,在这些模型中,他们认为贸易关系一旦确立就会持续到永远。例如俄林的要素供给比例理论认为,贸易是基于两国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说只要这种要素禀赋差异在两国中存在,这种贸易关系就会保持下去。尽管有另一些模型涉及到贸易的动态关系,但也很少讨论出口市场的退出问题,这些模型更多的是考虑新的出口商的进入,而对于已经存在的贸易关系会怎么样,则没有进行分析[2-5]。
除了利用理论模型来考察国际贸易关系之外,学者也利用数据进行了不少实证分析。如利用生存分析方法分析了美国的进口贸易关系及其持续时间以及德国的进口贸易关系[6,7]。
以下将根据2000~2006年《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进口贸易数据,运用K-M曲线以及Cox比例风险模型,考察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同时,与Besedes & Prusa(2006)关于美国的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相关研究不同,这里考察的视角定位在公司层面的贸易上,以能够更为细致地描述和揭示中国的对外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问题。
二、 数据、模型和变量选择
(一)数据的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
《海关进出口数据库》(2000~2006年)包括出口和进口贸易数据,这里使用的是进口贸易数据,该数据库的产品分类标准为8位国际HS编码,逐月统计了中国进口贸易公司从各个国家进口的各种产品的金额、数量、价格等信息。为分析方便,以及借鉴同类文献的做法,本文使用经过整理后的年度数据,即只要以年为单位发生了一次或以上的贸易,都认定贸易关系持续,否则认为贸易关系中断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数据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存在删失数据(censor data)。因为考察期间是2000~2006年,共7年(表1表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超过7年的仅占5.12%,绝大部分不超过7年,所以,7年样本数据可以说明问题),有些贸易关系一直持续到2006年,但我们却不能观测到2006年之后的状态,因而存在删失数据问题;二是Multiple spells问题②。它涉及到进口贸易关系中断后又再产生的问题。为了简化问题,同时又与Besedes & Prusa(2006),Nitsch(2009)的处理方法保持一致,将中断后再产生的贸易关系视为新的贸易关系。
表1描述了进口贸易关系数量及比例。我们发现在所观测到的1 967 613对进口贸易关系中,有1 191 671(60.56%)对贸易关系只持续了1年;有100 757(5.12%)对贸易关系持续了7年以上。删失数据(censor data)有209 523对贸易关系,占到整个贸易关系的10.65%。存在Multiple spells问题的贸易关系(即贸易开始年份不是2000年)306 064对,占整个贸易关系的15.56%。
四、结论
以上使用“公司-产品”层面数据考察了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中国公司与各贸易伙伴之间的进口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短,大部分(80%)贸易关系仅能持续1~2年,很少(5%)的贸易关系能持续超过7年。这表明从“公司-产品”层面看,中国进口贸易关系是动态调整的:大量贸易关系结束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贸易关系。进一步使用KM图形方法和COX比例风险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语言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正相关,当贸易双方语言相同时,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小,贸易关系持续时间长;初始交易额、产品交易额、GDP和人均GDP等四个因素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正相关,其数值越大,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越小,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长;距离因素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负相关,贸易伙伴距离越远,贸易关系结束可能性越大,贸易关系持续时间越短。
注释:
①
例如:从2001~2005年A公司都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但2006年A公司没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那么该贸易持续时间为5年。
②例如,从2001~2003年A公司都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2004年A公司没有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但在2005年A公司又开始从B国进口第C种产品。
参考文献:
[1]Besedes, T.Prusa, T.J.Ins, outs, and the duration of trade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39),2006,(3):266-295.
[2]Evenett,Simon J.,Venables, Anthony.Export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arket entry and bilateral trade flows[OL].http://.2002.
[3]Baldwin, R., & Krugman, P.Persistent trade effects of large exchange rate shock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LVIII (104), 1989,(3):635-654.
[4]Rauch J E.Business and social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LVIII(39),2001,(3)1177-1203.
篇3
作者简介:冯晓玲(1977-),女,吉林通化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大连海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关经贸关系:
赵放(1961-),北京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摘要:有关中关两国贸易数据的统计差异历来存在着很多争议,其中香港的作用被广泛提及。文章将中国途经香港到美国的商品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以东、西行贸易的“镜像数据”为基础.将其分为五种贸易流向进行了分析比较,得出了香港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中介地位仍然不容忽视,从中国途经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统计有一部分实际上是再出口,而不是转运的结论。
关键词:香港;再出口;转运;镜像数据;统计差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1-0015-06 收稿日期:2007-10-24
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之大有目共睹,对于两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彼此存在差异的原因,其中有关香港的作用,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结论:Fung and Lau(1998,2003)认为,中美两国统计的双边贸易差额数据都是不准确的,两国贸易统计差异归因于中美对经由香港转口、转口毛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处理;Chaodong Huang and Broadbent(1998)认为,中美在编纂双边数据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包括不同的计价基础和运输时滞,特别是中国经由香港的转口贸易,以及确认和正确的计价这些贸易流量的实际困难;Jialin Zhang(2000)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使用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产品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但是并不把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统计为美国对华出口,因而放大了美中贸易逆差;USCBC(2004)认为,美国的统计方法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因为美国按照f.a.s(装运港船边交货)计价,进口按照c.i.f(成本加保险加运费)计价,并且美国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商品都统计为美国自华进口,尽管香港的附加值高达25%。沈国兵(2005)将以上观点进行了综合,得出香港转口贸易和转口毛利是直接造成中美贸易数据失真和扭曲的原因之一的结论。本文主要引入Michael J.Ferrantino(2007)“镜像数据”的分析方法,将途经香港的货物分为“再出口”和“转运”两大类,探讨其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一、再出口与转运
在实际业务当中,再出口(re-export)和转运(transshipment)经常被混淆,前者是指当进口的商品以某一香港买家为收货人,该买家随即拥有对该进口品的法定所有权,并且可能在再出口之前时商品进行一些不从根本上改变商品特性的加工;而后者指的是在同一联运提单下的货物,由香港外某地运至香港,而目的地为另一地时,在香港水域内的同一艘船上装运或者由一艘船转运至另一艘船上。转运同为再出口而将货物进口至香港是不同的,它属于“过境中的商品”,通常并不通过香港海关的估价程序。
附表1和附表2提供了香港、中国、美国三者之间的贸易数据。附表1是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附表2是由中国和香港海关提供的与美国进行贸易的有关数据。香港调查统计局将一国运往另一国的货物分为四类,即进口、出口(包括本地出口和再出口)、向中国国内转运、向中国以外的国家转运。附表l中的A部分比较了香港和中国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的“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卸下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问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出口(但是香港不一定是最终目的地)和香港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对美国的出口数据和作为美国总货物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中国转运至美国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的A部分)。附表I中的B部分比较了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贸易数据和香港“在主要国家(国境)和装运港上装运的港口货物”的数据间的区别。它表明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的进口(但香港不一定为原产地)和香港报告的向中国的出口两者间的差异日益增大,类似的关系也可以在中国和香港自美进口和作为来自美国进口的总船货中的一部分的香港为美国向中国转运的数据中找到(见附表2中B部分)。
由此可见,香港在中美贸易中的中介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而在中国海关数据中,很有可能出现途经香港的出口中,一部分是通过香港再出口而另一部分是通过其转运的情况。然而,这种情况很难通过经验来确定,因为在香港的贸易和货物数据中再出口是以美元来衡量,而转运则是以公吨来计算,因此很难直接地比较两者。要想明确中国通过香港的再出口与转运及其同中国报告的直接出口和进口的关系,一个恰当的途径就是海关要完全理解双方在贸易数据上的显著分别,所以在这里引入“镜像数据”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镜像数据与东、西行贸易
理论上说,一国对其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应与其贸易国相应的进口数据相匹配,二者称为“镜像数据”。本文使用以“东行贸易”和“西行贸易”为基础编辑的镜像数据来估算中国、香港、美国三者之间贸易数据的差异。在编辑镜像数据时,一面用中国、香港所报告的数据,另一面则用美国报告的数据。镜像数据的一对恰当的匹配指的是通过该途径报告的贸易数据是可以互相印证的,然而很多原因导致了数据差异的存在。
(一)“镜像数据”的引入按照联合国指导方针,美国是按原产国来记录进口数据的。美国所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包括直接从中国的进口和通过香港及其他国家间接从中国的进口。而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的进口仅仅包括原产地为香港的进口。所以,在东行贸易(中国一美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当是中国报告的出口到美国的数据、香港本地出口数据和香港报告的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数据之和,而进口一面的数据应当等于美国报告的来自香港和中国的总进口值之和。
类似的,在西行贸易(美国一中国的出口)中,镜像数据中的出口一面应该等于美国报告的输到中国的出口加上美国报告的输到香港的总出口值之和,而进口一面应等于经过离岸价/到岸价调整后的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值减去美国途经香港再到中国的再出口值,这是因为美国通过香港间接对中国的出口将在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进口中被计算两次:一次是在货物进入香港海关时,紧接着当再出口到中国时又会被中国海关计算一次。这就意味着中国和香港均是根据联合国的指导方针,按照货物的原产国来记录数据的,这一点和美国做法相似。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通过避免调整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格,简化了实际数据差异的估算,即通过这
种方法计算的数据差异的实际大小将免去由于估算香港再出口的标高价而产生误差的难题,因此从统计上更加令人满意。报告的贸易数据的镜像联系见图1和图2。
(二)东行贸易附表3列出了中国和香港对美国出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问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自中国和香港的进口开始,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出口数据结束(该数据包括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商品向美国的再出口)。从附表3叫‘以看出:第一,在1995年和1996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要高于美国报告的同时期从两地输入的进口量,到了1997年,两者才大致相等。从1997年开始,双方数据差异迅速增大,并在2004年达到最大差异点,相差19.53%。自1998年到2006年间,中国报告的输至美国的出口量和美国报告的来自中国的进口量问的差距超过2倍。第二,在过去10年来,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中介人的地位迅速下降,从曾经超过60%的比例到目前大约14%的比例,而在香港再出口至美国的产品中,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占到了超过90%,该比例一直保持稳定。第三,香港本地对美国的出口量一直下降,并且随着香港的经济越来越以服务业为导向,这一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三)西行贸易附表4列出了中国和香港自美国进口的官方镜像数据,有关的调整以及对1995年至2006年间的统计差异的估计。它以美国官方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开始,经过了fob/eif的价格调整,另加上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再出口至中国的数据,最后以中国和香港官方报告的同时期的进口数据结束。
与东行贸易中的数据不同的是,1995-2006年间西行贸易总的统计差异似乎没有明显的模式。仅在其中的1999年和2004年,中国和香港报告的来自美国的进口额稍稍超出美国所报告的对其出口额,在余下的10年中,在镜像数据的出口一面,统计差异比进口一面要大得多。这就意味着出于逃税和其他动机,中国对来自美国的进口低报价的情况更为平常。该数据的其他显著特征就是香港作为方便美国对华出口的地位逐渐下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中,由香港再输出的比例已由1995年的超过30%下降到2005年的12.4%。同时,由美国参与的香港通过中国再出口至其他国家的比例也由1995年的10%下降到2005年的不到5%。
在贸易的双流向中,同贸易合作者所报告的贸易数据问的估算有一些统计差异很容易被解释,比如同荷兰(由此最终出口到其他欧盟国家)、巴拿马(中国出口至此地的商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要最终输至美国的)的贸易,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世界转口贸易的中心。但是中国和香港在同其他贸易者的贸易往来中由于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原因,如走私、低报价等因素,因此需要对所搜集的数据问的整体差异进行进一步的分解,才可能找出导致统计差异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三、通过贸易流的子部类来分解中美贸易间的统计差异
根据上文的以东西行贸易数据为基础的镜像数据显示出了中美两国与香港之间记录的贸易数据差异,要进一步研究差异的来源,有必要进行贸易流向的分解。
(一)对镜像数据进行的贸易子部类的分解在中国的出口数据中,中国海关要求贸易商说明启运国和消费国,其中前者是指在出口货物离开中国港口后下一个要到达的地点,它并不一定是货物的最终目的国,而后者是指消费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以这一信息为基础,可以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细分为三类。
a.美国既是启运国又是消费国,这指的是中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
h.香港是货物的启运地,但美国是消费国,这指的是出口货物要通过香港转运才能到达美国;
c.启运国是除香港外的第三国,消费国是美国。
如前所述,香港调查统计局将进口和再出口时两次不同的估价称作“香港调高价”,而在通过香港的转运中(通过香港港口的货物而没有通关),只报告货物的重量值而并非价值,所以香港的转运数据仅以总量报告且以公吨为单位,对商品不进行分类。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中国海关数据中h类型贸易能否反映出通过香港的再出口或转运。最明确的解释就是h类数据能够反映出转运的有关数据,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国与货物第一次通关的国家是同一个,所以在中国报告的数据中再出口数据会被记录为以香港作为消费地的出口,而不是对美国的出口。这类贸易就是传统上被归结为导致贸易统计差异的主要因素。因为货物通常被香港的中间商支配,所以中国的出口商可能事实上并不清楚货物的最终日的地。如果出口商知道货物的最终目的地是美国的话,而货物由于物流原因需要经过香港时,出口商很有可能会开立一张联运提单以避免在香港通关时产生的费用和麻烦。然而,这样理解并非总是可信的,如果一些中国出口商拒绝接受通过香港时的商品分类,那么有的再出口就要记录在b类统计中。
这样从中国和香港海关的数据中,就可以找出五种可能的贸易流,归纳如下:
C1.中国报告的对美国的直接出口;
C2.中国报告的通过香港对美国的出口;
c3.中国报告的通过第三国而非香港对美国的出口(C1-C3对应上文a-c);
C4.香港报告的对美国的本地出口;
c5.香港报告的对原产地为中国的产品向美国的再出口。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美国的官方贸易数据仅仅指出的是货物的原产地。但是,在美国商务部的详细记录的进口数据中,却含有货物是否在途中经过第三国到达美国的记录,这一进口数据覆盖了1995-2005年间美国从中国的所有进口数据。这里将这一数据作为美国报告的自香港进口的官方数据的一个补充,并将美国数据分为以下五类。
A1.从中国境内港口直接运至美国的货物;
A2.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货物在香港并未通关;
A3.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但最后一个启运港是在除香港外的第三国;
A4.美国对原产地为香港的货物的进口(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
A5.从中国输到美国的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在香港通关且最后一个启运港是香港,即通过香港的再出口。
如果采用对上述C2的最简单的理解,C1-C5同A1-A5之间依次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可以得出图3中列出的五种镜像关系。该图中有两个额外的盒子。右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上标注了在香港货物数据中报告的通过香港转运的数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因为这些数据不标明商品的名称也不以价值来记录而是采用以公吨为单位记录,所以不能把它们用作分析中。左侧标有问号的盒子代表了原产于中国的产品通过第三国的对外再输出。如果将c3理解为仅仅包括转运而A3既包括转运又包括再出口的话,就会潜在的遗漏一部分数据(即通过第一
国而不是香港的再出口),而它们正是此盒子中代表的数据。
(二)中、港、美三方贸易数据的差异在恰当地找出美中贸易中镜像数据的两方面后,就可以定义数据差异的两种衡量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在商品水平上衡量贸易双方的差异。
在这里M指的是贸易者r在第t年从s国进口商品i的贸易数据,E指的是s国在第t年报告的输到r方的商品i的出口值。这一指标总是用于衡量镜像贸易数据双方的差异。
第二个指标使用双方报告的数据总和作为标准,它的值在100(M=O,E≠0)到100(M≠0,E=0)间变化。当双方报告的数据差别不大时,两种方法得出的数值就会十分接近。
在东行贸易中,E等于中国报告的对贸易国的出口值、香港报告的对贸易国的本地出口值及其为中国的再出口值的和,M等于贸易国报告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进[1值之和。在西行贸易中,E等于贸易国报告的对中国和香港的出口值之和,而M等于中国与香港报告的来自贸易国的进口值减去香港报告的到中国的再出口值。
篇4
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统计差异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中美关于贸易额的统计方法差异。双边贸易统计方法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中美两国之间进出口计价方式不同。中国的出口数据是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惯例依据离岸价格,也就是通常所说的FOB价(freeonboard,简称FOB,包括本国生产成本、货物运输保险和在本国装载上船成本)统计的。与大多数国家出口计价不同,美国出口数据是按照船边交货价,也就是FAS价(freealongsideship,简称FAS,不包括本国生产成本、货物运输保险和在本国装载上船成本)统计的,这与国际惯例有别。由于未包含商品装上船的成本,故FAS价的数值小于FOB价。并且中、美两国都是依据到岸价格,也就是CIF价(包括货价成本、在途包装费、保险费和运输费)统计进口。这样,由于中美进出口计价基础不同,自然而然会造成双方贸易统计差异。因而就需要把双方的进出口数据转换成统一的离岸价(FOB价)计算,这样才能比较中美双边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情况,进而推算出中美贸易顺差规模计算上的失衡程度。为此,按照国际通行的转换方法,以FOB价为基础,把美国的以FAS计价的出口值加上1%的成本转换成FOB值。并且,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转换做法,把中美两国的以CIF价计算的进口值扣除10%来得到FOB值。为什么要用同一种方法计算进出口数据呢?原因是当贸易数值庞大时,FOB价与CIF价的差异会造成显著的由计价方式不同带来的差异。比如,如果以FOB价计算,中国、美国每一年对另一方的商品出口为500亿美元,双边贸易本应刚好平衡。但现在美国会认为,本国对中国出口是500亿美元,但从中国进口是550亿美元,原因就是后者以CIF价格计算。这使得美国以为自己有50亿美元的逆差。反过来,中国对美国出口以FOB价计算是500亿美元,但进口以CIF价计算是550亿美元,以至中国也认为自己有50亿美元的逆差。一项本来平衡的贸易,现在变得双方都认为自己有了“逆差”。因此,用不同的基准价格计算进出口会造成一定数额的误差。当我们按照国际通行的转换方法,以FOB价为基础,把美国的以FAS计价的出口值加上1%的成本转换成FOB值,并且,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转换做法,把美中两国的以CIF价计算的进口值扣除10%来得到FOB值,双方在统计计价方法完全一致情况下计算出的经过修订的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数值增加了,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数值减少了,同样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额也减少了。这样,经修订后,双边贸易顺差规模的差异有了一定量的减小。而且从计价方法上明显看出,美方的统计数据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
二、经由香港转口贸易的影响
所谓转口(reexport)亦即香港买家依法取得某批进口商品的所有权后随即售出,运送给第三国家或地区的另一个买家。香港买家将进口商品再出口前,或会略微加工,但不影响商品性质,故不会把香港变成原产地。这种转口使中美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出现差异。美国方面在计算进口时,由于美国海关追查所有进口商品,包括转口商品的产地来源,美国的进口数据应该已经包括了直接进口和间接进口,无需另加转口。现实中,中国使用的是目的地原则,往往不统计部分经由香港对美国转口商品,如果这部分转口在中美贸易中微不足道,或可忽略,但现实中刚好相反。香港经济研究中心学者FungandLau(<中美双边贸易差额1990-2000>2001)根据香港贸发局提供的数据研究后发现,以2000年为例,美国有61亿美元的制成品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内地,占美国对中国出口官方数据的37%。同期中国内地有365亿美元的制成品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占中国对美国出口官方数字的70%。如此高的比例,原因在于中国以目的地为原则的统计方法没有统计经港转口商品的数额。美方资料显示,中国的货物只有20%直接运往美国,其余80%是通过第三方转口到美国的,中方对转口贸易不计入贸易额的统计方法,导致中国统计的对美出口普遍低估,而美国由于在进口贸易中统计转口部分,使得美方统计的自华进口普遍高估,这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根据FungandLau的研究,中国在加上对转口的统计后,中美双边关于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会大大减小。
三、转口加成利润的影响
分析时,我们还应考虑香港转口毛利带来的标价上升问题。中国出口商品经由香港转口赴美时,香港中介人附加了利润,即加成利润。这部分被视为香港的附加值,理应在中美贸易数据中剔除。根据FungandLau(<中美双边贸易差额1990-2000>2001)的研究,中国货物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平均增值率高达40%。货物离开中国后在第三方增加的价值显然不应计入自中国进口中,而美国按照原产地原则和CIF价统计进口的方法,导致美国的统计数据中包含了该增加值部分,从而夸大了美自华进口数量。在美方所计算的自华进口数据中剔除香港转口加成利润后,中美贸易顺差规模的统计差异也会进一步缩小。
四、美方统计中忽略了服务贸易
篇5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1-0010-05 收稿日期:2010-06-10
产品是技术的载体,产品进口会使得所体现的技术在进口国发生外溢,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一国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在当前全球贸易迅猛发展的条件下,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开始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研究了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对相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然后简单地加以评述,并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理论基础及作用机制
(一)理论基础
新贸易理论、内生增长理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发展为动态贸易利益的量化研究提供了可能,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以Krugman(1979)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学家放松了传统贸易理论完全竞争、产品同质、收益不变等强假设条件,将规模经济、产品种类、技术转移等因素引入到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将贸易理论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构成了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点。Romer(1990)、Grossman and Helpman(1991)、Yong(199I)、Aghion and Howitt(1992)等学者将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加以拓展,在开放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投入品种类、产品质量等变量,考察贸易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了国际贸易在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中的作用,为增长理论与贸易理论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成为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Melitz(2003)、Meliiz andOttaviano(2005)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表明,开放条件下生产率异质企业对于外部竞争压力的不同反应对行业生产率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这为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框架。
(二)作用机制
为了实证分析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许多学者对上述基础理论模型从不同层面进行了拓展,具体地解释了进口贸易影响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
Coe与Helpman(1995)在Grossman、Helpman(1991)研究的基础上,利川进口份额作为权数衡量了国外研发对于本国TFP增长的贡献,为衡量和测度国外技术溢出对进口国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Connolly(1997)发展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证明进口贸易对模仿进而是技术扩散产生的正向影响,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获得静态和动态贸易利益。贸易通过降低南方国家的模仿成本,产生重要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南方模仿国的增长,因为贸易可使南方模仿者廉价地获得关于北方创新者新产品的知识,而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成功模仿的概率,会对南方模仿产生正的影响。南方国家销售进口产品,提供售后服务,会增加对于进口产品技术知识的了解,降低对这些产品逆向工程(reverse-engineering)的成本。同时,贸易开放还会通过对国内企业带来的竞争效应,影响企业的模仿行为和国内企业数目,进口贸易降低了模仿者了解国内市场需求的成本,保证了有效率模仿的实现。Connolly(1999)在一个南北贸易的质量模型中,在创新和模仿过程融入了学中学(learning-to-learn)的概念。他认为,学中学(learning-to-learn)不同于干中学(learning-by-doing),因为学中学获得的技术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研究,而不是仅仅限于特定所学任务。当一个企业成功模仿了质量越来越高的特定种类产品时,他将获得产品工程中的知识,并且改善它,因此模仿不仅使得企业在未来的模仿中更有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独自成功发明更高质量水平产品的可能性。
Keller(2001)认为通过与国内外企业相互作用的学习是促进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方式。国内发明的效率随一国知识存量的递增而递增,它与国内所知的产品设计的数量是成比例的,通过增加国内知识存量,国际溢出提高了国内发明活动的效率。Chen、Imbs、Scott(2009)扩展了Melitz(2003)和Melilz、Ottaviano(2005)的企业异质性国际贸易模型,把理论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有机结合在了一起,认为贸易的开放导致了竞争效应,在更大的国外竞争和更多的进口产品的压力下,国内企业的利润会下降,异质性企业中生产率水平较低的企业会退出市场,只有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才可以适应市场竞争,并且会在竞争中增加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这样产业的平均生产率水平也会上升。
理论模型的构建为实证研究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基础理论模型的拓展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揭示了进口贸易影响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进口贸易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总量、进口贸易模式和进口产品的竞争效应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进口贸易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国家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Coe、Helpmanfl995,以下简称“CH”)利用21个OECD国家和以色列1971~1990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通过进口贸易的传导机制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发现国内外研发资本存量都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一国进口占GDP比重越大,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国内生产率的影响越强,开放度高的经济比开放度低的经济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要大。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使用CH的方法计算了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发现通过进口的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许多学者以CH模型中的数据为基础,利用新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研究,得出了与CH相似的结论。Liehtenberg、Potterie(1998,LP)认为CH(1995)模型中计算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赋权方法存在汇总上的偏误,因而提供了一个理论上产生更少偏误和更好实证结果的赋权方法,在修正了指数偏差的基础上,分析了国外研发的产出弹性对于一国贸易开放度的依赖,研究证明一国贸易越开放,该国从国外研发中获益越大。喻美辞、喻春娇(2006)利用LP方法计算了相对于中国的国外R&D资本存量,并将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计量模型,证明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Keller(1997)也质疑CH
(1995)的赋权方法,而采用随机赋权方法计算了国外知识资本存量,同样得出了与CH模型相似的结论。但是Coe、Hoffmaister(1999)认为Keller(1997)的随机赋权实际上是带有随机误差的简单加权平均,这种随机赋权只会得到一个随机变量,它和生产率之间是不存在联系,他们利用替代的赋权方法作为双边进口份额回归证明,随机创造的贸易模式并不能产生国际研发溢出的估测。
鉴于上述学者研究中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中可能出现的伪回归,有学者根据CH研究的数据,利用面板协整方法重新考察了进口的技术溢出对进口国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通过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要么是微弱的(Kao、Chiang和Chen,1999),要么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Funk,2001),因此,他们认为之前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高估了进口的作用,但是忽略了其它传播机制的作用。
Altair and Cieeone(2004)测度了贸易的实际开放度对国家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出口加总的贸易开放度是一国全要素增长的重要因素。Falvey、Foster、Greenaway(2004)区分了知识的性质,认为通过发达国家的研发生产的知识能够通过贸易溢出到其他国家,利用21个OECD国家1975~1990年的面板数据集中考察了进口作为技术传播途径的作用,发现无论国外的知识是公共还是私人的,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都非常显著。Lumenga-Neso、Olarreaga、Sehiff(2005)通过引人间接与贸易相关的研发溢出的概念扩展了CH的分析,认为与贸易间接相关的研发溢出也会在国家之间发生,他们利用114个国家的向量矩阵实证研究发现,国外研发的间接流量要远高于直接流量,间接流量对于TFP的贡献要远高于直接流量的贡献,并且全部(直接加间接)国外研发流量明显地要比国外直接研发流量要稳定。由于间接效应的存在,双边贸易相对来说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重要决定因素,这调和了CH(1995)与Keller(1997)的结论,但也提供了贸易作为国际知识传播机制重要性的支持。
Madsen(2007)使用16个OECD国家1870~2004年间技术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数据库,验证了知识是否通过贸易渠道发生了转移。实证估计表明,在过去135年中通过贸易发生的知识转移始终非常重要,TFP与知识进口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在过去一个世纪中93%的TFP增长要归于知识的进口,知识的外溢是1870~2004年间OECD国家TFP收敛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贸易的国际技术外溢是OECD国家TFP增长的重要贡献因素,有助于OECD国家TFP的收敛。
(二)企业和产业层面进口总量的技术进步效应
企业和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证明,进口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Blalock、Veloso(2003)利用印度尼西亚制造业的详细面板数据,证明供给进口密集部门的企业比其它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进口是国际技术转移的推动因素,与国外厂商的垂直供应联系是进口推动技术转移发生的渠道,这从企业层面证明进口是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Aeharya、Keller(2007)把技术转移和进口联系起来,利用17个工业化国家1973~2002年的详细数据实证分析发现,进口是技术转移的一个主要渠道,国际技术转移对于生产率的贡献常常超过了国内研发的贡献。
李小平、朱钟棣(2006)总结了国外学者计算R&D存量的六种方法,并用这些方法分别计算了同外R&D存量通过进口贸易对中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虽然不同的实证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不近相同,但基本上肯定了产业层面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为正的结果。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利用DEA方法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发现进口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出口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进口贸易模式的技术进步效应
(一)资本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与CH(1995)研究方法相一致,Coe、Helpman、Hoffmaister(1997)采用77个发展中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研究了这些国家通过机械设备进口从工业化国家的研发中获益的程度,结果显示,国外研发资本存量的知识通过机械设备进口能够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越大,对于来自工业化国家机器和设备进口越开放,本国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越高,该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越高,而总进口中许多消费品和服务的进口对于生产率并没有影响,国外知识存量只是通过机器设备的进口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
Connolly(1999)考察了国内外创新对于实际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发现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产品的进口在国际技术扩散中作用的证据,国内模仿和创新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进口存在持续的正依赖性,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对于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要高于国内创新的贡献。Xu、Wang(1999)认为资本品比非资本品拥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因资本品贸易是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他们考察了资本品贸易作为国际研发溢出渠道的重要性,估测结果表明,在G7国家中,研发投资大约一半的收益溢出到了其它OECD国家,其中大约一半的溢出是通过资本品外溢渠道发生的,资本品衡量的研发溢出变量统计上是显著的,比总进口衡量的溢“{变量更多解释了国家间生产率的差异。Eaton、Korlum(2001)也认为国际贸易可以把技术进步的好处传递过国界,他们通过研究世界生产和资本品的贸易,评估了这一机制的重要性,证实一国的生产牢取决于该国对国外资本品的可获得性以及该国使用资本品的意愿和能力。
(二)中间品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
Keller(1997)引入一个研发驱动的增长模型,技术通过体现在不同中间产品的贸易传递到国内其它部门和国外部门,他使用来自8个OECDI业国1970~1991年13个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在同一行业中,国际贸易是国外技术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随后使用相同的数据,Keller(1999;2000)量化分析了贸易模式在决定技术流量中的重要性,发现一国的进口模式会影响到一国的生产率,如果一国主要从技术领先国进口,该国获得的体现在中间产品上的技术将高于主要从技术跟随者进口的所得,与进口模式相关的技术进口的差异解释了这些国家生产率增长上20%的差异。Hakura、Jaumotte(1999)利用87个国家1970~1993年的数据,在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对于技术转移影响的基础上,考察了贸易在技术从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溢出中的作用,证明产业内贸易能够比产业间贸易更多地促进技术转移。
Amiti和Konings(2007)利用印尼1991~2001年间制造业的普查数据,估测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们区分了源自最终产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与源自中间投入品关税降低的生产率增长,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投入品关税的降低。Topalova(2007)利用制造业部门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印度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贸易改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导致的生产率增长远高于最终品关税下降产生的影响。Kasahara、Rodrigue(2008)利用智利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估测了国外中间品的进口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国外中间产品的进口提高了生产率。Halpern、Koren、Szeidl(2005)利用1992~2001年问匈牙利制造业企业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估测了一个生产者结构模型,研究显示,进口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统计上与经济上都是显著的,进口解释了匈牙利90年代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30%。
(三)对贸易模式技术进步效应的质疑
对于贸易模式与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的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Funk(2001)使用面板协整技术考察了贸易模式与国际研发投入溢出间的关系,没有发现支持进口模式与研发溢出之间关系的证据,因此认为,先前的研究可能高估了进口投入品在国际研发溢出中的作用,却低估了其它传播途径的作用。Lumenga-Neso、Olarreaga、Schiff(2005)对与贸易相关的间接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似乎也证明双边贸易模式并非国外研发通过贸易溢出的决定因素,一国外部研发溢出流量对于贸易模式的依赖可能是很低的。
四、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
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但是受传统贸易理论严格假设的束缚和统计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这方面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进展相对缓慢。随着企业层面统计数据可得性的提高和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开创性进展,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引起学者们极大的研究兴趣。
Bertschek(1995)利用德国80年代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口和内向型FDI对于国内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进口和内向型FDI增加了国内竞争,降低了国内企业的盈利,对产品和过程创新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Lawrence、Weinstein(1999)通过对日本1964~1973年间进口贸易的研究发现,进口竞争是促进日本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并且进口竞争的作用要大于中间产品进口对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竞争性产品的进口刺激了创新,向国外竞争对手潜在的学习是效率增长的主要渠道。
Pavcnik(2002)利用企业水平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智利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内生产率的进步要归于进口竞争部门中的贸易自南化,总的生产率进步源自资源从低效率生产者向高效率生产者的重新分配。Schor(2004)利用巴西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于企业生产率演进的影响,发现进口产品和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动与生产率的变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贸易自由化后,竞争的增加和可获得的体现更高技术的中间品进口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Topalova(2007)的研究表明,进口关税的下降增加了国内竞争,导致了产业生产率的提高。
Gorodniehenko、Svejnar、TerrelI(2008)利用27个新兴市场经济的数据,估测了来自国外的竞争、与国外企业的垂直联系以及国际贸易对国内企业几种创新的影响,发现有很强的证据表明国外竞争和创新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Chen、Imbs、Scott(2006)利用欧盟1989~1999年间制造业的详细数据研究发现,进口竞争的技术进步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短期内贸易开放具有促进竞争的效应,由于进口竞争的增加,无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产业中产品平均成本降低、生产率出现上升。但是长期来看,当竞争力更弱的经济体也开始出口时,这些效应会逐渐减弱甚至会逆转,虽然增加的贸易对欧盟的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小的。Acharya、Keller(2008)使用1973~2002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长期内进口自由化通过选择效应降低了本国产业内的生产率。
对于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以上我们按照进口总量、进口模式和进口竞争几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梳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三种机制并非各自独立地发挥对进口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它们分别都是从进口贸易的一个侧面反映出进口贸易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对于一国整体进口来说,三种机制都在共同发挥着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
五、结语
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研究隶属于动态贸易利益研究的范畴,是对贸易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证实了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内生关系,进口是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深化并丰富了我们对于进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和认识,有力证明了自由贸易所蕴藏的巨大动态利益,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目前,对于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相对来说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主要还是停留在进口产品总量上的研究,缺少对进口贸易模式、进口竞争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因而对进口与我国技术进步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我们认为未来对于进口与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应当考虑一些忽略的变量可能产生的影响,深化对于新的机制的研究,同时对于我国进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应当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方希桦,包群,赖明勇2004,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l中国软科学(7)
李小平,卢现祥,朱钟棣,2008,国际贸易、技术进步和中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增长[J],经济学(季刊)(2)
